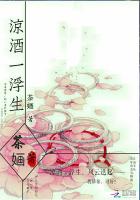楚河、张鹏、王嘉怡三个人是雷厉风行的行动派代表人物,李可可一向对楚河言听计从,最终以四比一的压倒性优势否定了我坚决但势单力薄的反对声。下午的课四点十分就放学了,他们四个随着学生一起走出校门。我犹豫再三,终是追上他们,一行五人浩浩荡荡地奔向东山。
到了山脚下的祠堂,说说笑笑的四人不约而同地噤了声,生怕惹到那个古怪的老婆婆又出现阻拦我们。不过今天老婆婆好像不在,那个破败的泥土房里没有一丝声音。我们几个人趁着这个好时机溜上山去。
昨天上山下山都很急,我根本没有闲情逸趣欣赏这山上的花草树木,此时悠游而上,的确是个令人神舒气爽的好景致,如果忽略那越来越近的浓重怨气,一切都显得很完美。
来到山顶,楚河带领我们转了两转,眼前便出现了那座高大的牌坊,几个人的目光凝在那牌坊上,齐齐屏住呼吸。原来“百闻不如一见”这句话说得是真的,虽然我们都在楚河的手机里看到过这场景,但真正见到它,我们仍是感到震撼。
青石铺就的圆形广场中间矗立着一座三门二楼制式的牌坊,飞檐翘角,纹饰繁美,一望便感受到人世间熙熙攘攘的喧嚣和蓬勃美好的愿景。四根敦厚高大的石柱与门楼上喜庆繁华的吉祥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简朴厚重,显示出对抗风雨,穿越岁月,不屈不挠的决心。门楼上正中间隐约留下四个字的痕迹,已模糊得看不清是什么,使人心生出虚无的缥缈感。广场上从青石缝中钻出的荒草沉默静立,鲜绿簇拥着枯黄,记录下生命轮转的痕迹。一时间这座跨越时间长河,穿越历史风霜的牌坊,令我们生出无数感慨。
“芳草凄凄,重门深锁。”李可可叹。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楚河叹。
“一世浮华,过眼云烟。”王嘉怡叹。
“对酒当歌,人生苦短。”张鹏叹。
“······”
他们几个迟迟没等到我的感慨,丝毫不觉意外,这段时间他们早已习惯了我的沉默,但还是很客气地为我留下一段发表感慨的空白时间。
我盯着那个站在牌坊下蓬头散发面露狰狞的白衣女子,果然不出所料,李可可的确遇到过她,她很生气,气我们打扰到她。
静立片刻,大伙敛下肃穆而沉重的心情,欢悦的情绪如雨季里的喷泉般源源不断地涌出,一时间同时动了起来。
楚河心中早已取好角度,大步迈向自己心宜的位置,李可可拎着一堆画具跟在他后面一路小跑。张鹏手中的相机卡卡响起,对着牌坊或趴或跪摆出各种姿势寻找理想的角度。王嘉怡从背包中掏出一套汉服打算去树林中换上,她招呼我,“扶笙,过来帮我一下。”
我过去,帮她拿着衣服首饰,俩人走到一丛灌木后面,那个白衣女子跟随我们身后,静静地看着王嘉怡换衣服,眼神中透着赞赏、羡慕、渴望和妒忌。王嘉怡做梦也没想到这里有个第三者,而我,虽然看着这个白衣女鬼在我面前流连,可是我早已养成面无表情若无其事的本领,所以暂时我们三个相安无事。
“好了,扶笙,我得快点,咱们得在天黑前回去。”
那白衣女鬼听到“回去”两个字,面目狰狞起来,伸出双手掐向王嘉怡的脖子,我跟在王嘉怡的后面,出手如电般捉住女鬼的领子,把她揪回来甩在一边,用眼神警告她不要再轻举妄动。许是刮到了树枝,闹出了点动静,王嘉怡回头关心地问道:“扶笙,怎么了?”看着我的诡异动作,愣了下。
“蜘蛛。”我面不改色道。
王嘉怡面色一紧,她最怕虫子,拉着我快步走出树林。正在拍照的张鹏转身看到王嘉怡,满脸惊艳,灵魂出窍,呆立在那里,我识相地站住。一阵微风起,掀起王嘉怡的裙角,恍若仙子一步一步走向张鹏。我想,他的这一生都会因这一刻拜倒在王嘉怡的石榴裙下。
李可可举着手机录下这一幕,眼神梦幻迷离,这个小可爱被这一瞬间感动得一塌糊涂。沉醉在绘画世界中的楚河似乎感觉到流淌在这处荒凉之地的别样情愫,也抬起头看着这一幕。
一阵凄厉的尖叫在我耳边响起,痛苦、绝望、疯狂。沉浸在美好中的几人同时一愣,李可可跳到楚河身旁,有点惊慌地向我道:“扶笙,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我摇头。楚河拍拍李可可的手,安慰道:“我好像听到山下谁家驴在叫,这么远,听不太清。”说罢拉着李可可偎在他身边继续作画。
张鹏灵魂归窍,一把抱起王嘉怡转上了圈圈,信誓旦旦要为王嘉怡拍出一套绝美的大片来。
我安静地走到牌坊下,看那个白衣女鬼疯狂地抓挠着那根稳如泰山般的柱子泄愤。
“恨?”我问。
女鬼转头狠狠地盯着我,刻骨的恨意从女鬼眼中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