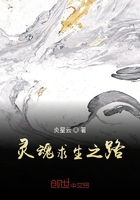且说专家组众人与坦赞施工队一起,经过几个月的奋力抢修,两座被炸毁的铁路大桥顺利恢复通车。“瓜爷”与“东方红”牵引着列车顺利抵达了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希车站。
经过短暂的整备,随着“瓜爷”的一声长鸣,列车又运满载着旅客返回坦桑尼亚。
刚开车不久,卡萨车长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卧铺车厢一名非洲男性旅客满头大汗,却盖着毯子颤抖不止……
“肖总工,好像有一名旅客生病了!”卡萨车长道。
“情况严重吗?”正在餐车吃饭的肖总工放下碗筷问道。
“我刚才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烧了,非常烫,出了很多的汗,但一会儿又喊冷,盖了两床毯子都不行。”卡萨车长道。
“哎呦!可别是疟疾啊!”肖总工道。
非洲大地历来炎热多雨,蚊虫肆虐。而疟疾这种古老的疾病,正是在热带地区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广为蔓延。患者多有发烧寒颤、时冷时热、呕吐腹泻的症状,迁延难愈,在非洲各地高发常见。我国对疟疾俗称“打摆子”,非洲当地人民叫疟疾为“蚊子病”。
此时天色已暗,列车正停靠在位于东非大裂谷腹地的一个小站进行待避作业。
“际涯和三胖看看去。”肖总工道。
我和王三胖来到患病旅客所在的车厢,见一名二十多岁的非洲青年男子满头大汗躺在卧铺上,盖着两床毛毯却瑟瑟发抖,从症状上初步判断,正是疟疾!
此时,一名非洲中年妇女拿来一束药草,在那男子头顶和身上摇晃,口中唱念有词,但说得是当地语言,我和三胖却听不懂了。
“这非洲大姐说得是什么啊?”王三胖问卡萨车长道。
“她说得是‘通加语’,我也只能听懂部分,大概意思是:‘蚊子表姐啊!你吸食了我弟弟的血,但请你把那可恶的蚊子病不要留在他的身上,否则我会让古老的神族断掉你的大腿……’”卡萨车长翻译道。
“干嘛管蚊子叫表姐啊?再说蚊子大腿能有几两肉啊!”三胖奇道。
“具体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可能是当地人的一种习俗吧,也可以翻译成蚊子妹妹的。”卡萨车长道。
“蚊子表姐就表姐吧,蚊子大腿也算二两肉,但这是疟疾,需要赶快治疗!”我道。
车上并无治疗疟疾的药物,我招呼三胖先到车长办公席拿退烧药给那非洲小伙儿服下。
正在这时,旁边一名包着“花卷儿”棕红状头巾的男人用英语道:“这是疟疾,我这里有英国产的最先进的治疗疟疾药物--‘奎宁’,吃上就会好!”
卡萨车长给我和三胖翻译了那“花卷儿”说的话。
我们朝那“花卷儿”打量,只见他约么四十多岁,棕色皮肤,像个印度乘客,卡萨车长道:“请你快把奎宁给他吃上吧!”
岂知那“花卷儿”却道:“这是‘日不落帝国’专门为我们印度生产的,本来是不能给黑色皮肤人使用的,但考虑他发病急,用也可以,需要100英镑!”
卡萨车长翻译了这“花卷儿”说的话,三胖听了就要发作,挥拳想揍那“花卷儿”。
三胖被我一把拉住,愤愤骂道:“我去你大爷的!瞧你丫‘红配棕,塞狗熊’的揍性!狗奴才!”
我忙告诉卡萨车长:“这段儿掐了,别翻译!”
卡萨车长笑而不语。
我心想,这“花卷儿阿三”原来不是给非洲兄弟送药治病的,丫是‘刷存在感’,并且来找事儿的!
“这儿距离达累斯萨拉姆站还有多远?”我问卡萨车长道。
“大概还有13个小时的距离。”卡萨车长道。
“先拿退烧药给那小伙子服用,然后车到站后,回中方铁路大院儿治疗。”我向三胖道……
非洲蚊虫肆虐,人们常患疟疾,同时非洲医疗水平堪忧,加上西方国家生产的抗疟药物非常昂贵,很少有人承受得起,非洲当地人民多用土著巫术进行祈祷,导致病死率非常高。
当时我国在援建坦赞铁路时,与达累斯萨拉姆的铁路大院设有医院。中方各援外机构工作人员患了疾病,在当地医院无法治疗,往往驱车几百里,也要迅速赶到铁路大院诊疗。我国驻达累斯萨拉姆铁路大院医院(以下简称铁路医院),能进行内、外、儿、妇等诊疗,同时还能开展外科手术,当时已经相当于我国县级人民医院的技术水平。
列车缓缓开动,肖总工正与技术人员研究列车参数,只听耳边嗡嗡作响,忍不住挥手扇了几下。
王三胖道:“孙际涯同志,‘嗡嗡’的是你二姑吧?”
“不对!刚才我仔细看了,‘嗡嗡’穿的是连衣裙,我二姑哪有这么年轻,肯定是你表姐!”我摇头一本正经道。
众人听罢“噗嗤!”一声哈哈大笑,又见孟翻译穿得是连衣裙,更是笑得直不起腰来,孟琳琳和王三胖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我本没想往孟翻译那儿说,但和三胖斗嘴,他说嗡嗡飞的蚊子是我二姑,我为了证明那蚊子“年轻”,就说那蚊子穿得是连衣裙,是他表姐。哪知忘了孟琳琳穿得正是连衣裙。
见王三胖和孟琳琳都有些尴尬,我便转移话题道:“哎,我说三胖同志,你岁数大啊?还是孟翻译大啊?”
“明知故问,我二十三!”三胖白了我一眼道。
“叫姐姐!”我比你大,孟琳琳急忙揪住话题,化解尴尬。
“什么呀,我23岁,6月的生日,肯定我大啊!”三胖道。
“嘿嘿!我1月的生日!”孟琳琳笑道。
“好吧,蚊子表姐!”三胖道。
众人听罢又是一阵大笑……
列车在大伙儿的说笑声中飞速行驶,期间,我和三胖又去看了几次那出现疟疾症状的非洲小伙子。他吃了退烧药睡着了,暂时没有什么大事。
但列车快到达终点达累斯萨拉姆终点站时,还是出现了状况……
却见那非洲小伙儿开始出现恶心呕吐,神昏谵语等症状,“花卷儿阿三”也开始寒战发冷,唇甲发绀,更为头疼的是孟翻译和其他几名中方专家组同志,还有几名坦赞列车工作人员,也相继出现了乏力低烧,四肢酸痛等情况。
其中,“花卷儿阿三”虽吃了自带的奎宁,症状却不见好转,不一会儿又出现了高热发烧的状况。只见他一会儿盖被子,一会儿扇扇子,甚是痛苦难当。几次想要出言向列车工作人员相助,又碍于之前的言出不逊不敢张嘴。直到后来实在忍耐不住,竟用半生不熟地中文向三胖哀求道:“大爷爷!嗯,大爷!大爷爷!给我一块退烧药!”
三胖见这花卷儿阿三竟也懂得些中文,恨道:“你叫祖宗我都不想管你,我们可以提供列车运输服务,看病找你的‘日不落’去吧!”
那“花卷儿阿三”高烧难耐,声音断续道:“我的奎宁……不要……英镑,给黑……皮肤吃,向你们买……一块退烧药!”
“行啊!一百块钱人民币买一块退烧药!”三胖道。
“我给一百英镑,这比人民币值钱。”花卷儿阿三道。
“我们车上退烧药对非洲兄弟姐妹不要钱,对日不落和他的奴才只能收人民币,不要英镑。”
那花卷儿阿三几近绝望……
我见三胖把这小子收拾得差不多了,为非洲兄弟姐妹争了一口气,也就不再难为他,让三胖给了他服一片退烧药。
三胖嘟着大嘴一百一十个不乐意,气囔囔地扔给“花卷儿阿三”一片中国产的“扑热息痛”道:“吃吧!”
那“花卷儿阿三”想是难受得紧了,抓起药片直接吞了下去,竟连水也不喝。吃罢拿出一张100元的英镑,颤颤巍巍地递给三胖。
王三胖接过看了一眼,甩在他面前,头也不回,大步走向餐车了……
一个小时后,列车驶入达累斯萨拉姆站,铁路医院的何院长接到通知,带领医护人员早已在站台等候。
列车停稳后,众人七手八脚将疟疾发病的非洲小伙儿和孟琳琳等工作人员,连同那“花卷儿阿三”,或搀或抬,一齐送上汽车驶向铁路大院。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