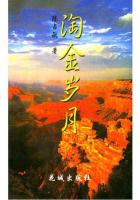金四九在市里一连开了一周会,说是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培训性质的研讨会。会议一结束,他连学校都没回便直接杀回到了直周县城。
见到孙一水的时候已经黑天了,孙一水正在警队大院里往篮板上扔篮球。他心不在焉,球篮上连个铁圈都没有,他就那样往篮板上投一下,噗通一声弹射回来,再投……
听到车的声音,他突然来了精神,球在手里有了灵性,又是穿裆又是转身来了一个三步上篮之后才站住,把软趴趴的篮球远远地扔到了自行车棚后面,叉腰站在原地等金四九下车。
“案子怎样了?”金四九扔给他一条小苏,“案子结了?”
“宋修礼和刘无敌的事已经没啥事了,事实清楚,嫌疑人认罪。”孙一水看了看手里的烟,知道金四九不差钱,也不谢,摆了一下手往办公室走,“江有沱的事不好处理,死犟死犟的,不认罪。”
“凭啥让他认罪?”
“凭他身上背了二十条人命!”孙一水停住脚扭头看了一眼又继续走,“沙河桥上杀了七个,没罪!在他家屋里杀了三个,没罪!可是他约宋修礼来他家,一下杀了八个,有罪!”
进了办公室,开了风扇,孙一水抡了膀子换了一条短袖,一屁股蹲在椅子上,急不可耐地想把那条烟拆了,突然犹豫了一下又扔桌子上,从裤袋里掏出半盒石家庄抽了一根。
“防卫挑拨?”金四九拧开一瓶纯净水,喝了一口才发现已经过期俩月了,凑合吧,喝不死人。所谓“防卫挑拨”,指的是故意挑衅激怒或采用其他方式引诱对方用暴力攻击自己,再借“正当防卫”之名趁机打击对方,以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防卫挑拨”一旦认定成立,跟故意伤人、杀人没什么两样。
孙一水有点不高兴,“金教授,你是不是在替一个严重的暴力犯罪分子说话呀?我跟你说,在大街上我随便看一张陌生的脸,我就知道他身上有没有事,更别说江有沱这个老熟人了。他身上不干净!绝对的!”
金四九说,“你没有证据,是不是?你管侦查,你说他有罪,说他是防卫挑拨,你就得负责举证责任,这没问题吧?”
“然后哩?”
“然后你死活找不到证据,是不是?”
“八条人命啊,那不是证据?”孙一水说这句话的时候底气严重不足。他知道,那不是证据,那仅仅是一个结果,无法证明那些人死于防卫挑拨。一大群暴徒入户去杀一个人却被反杀,然后你说这是防卫挑拨,暴徒成了受害人。谁信?除非有证据支撑,否则对这群入户行凶的暴徒之死不需要任何人负责。
金四九摇头,懒得解释,孙一水心知肚明。对江有沱来说,当晚的事件严重和紧迫程度赋予了他无限制防卫权。刑法规定,对迫切而紧急的暴力犯罪,可以采取一切方式进行自救和阻止,包括杀死暴徒。换言之,杀人无责。
金四九看着正在泄气的孙一水,“刚才还在兴致勃勃地玩篮球呢,一转眼就丧气成这样。”
“什么玩篮球,我是愁的。”孙一水掐了烟,一本正经地说,“江有沱还算老实,问什么说什么,就是咬死不承认那天晚上他砍死的那几个人是出于防卫挑拨。”
“一个庄稼人[205],他哪懂什么叫正当防卫,什么叫防卫挑拨?”
“他懂!”孙一水哼了一声,“你别被他的表象蒙骗了。不管我怎么圈,怎么绕,这家伙死活都不上当。”
金四九本来计划要去调查一下他的家事,因为宋修礼被抓,江有沱自首,市里又说巧不巧地有个研讨会便耽搁了,他这几天一直惦记着这事。
讯问的情况他已经知道,虽然大部分涉案人都已死亡,即便宋修礼供认不讳,这案子依然疑点重重。当然,警方完全可以结案,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对死无对证的事,有没有异议都不会再有任何意义。宋氏家族死的死进号子的进号子,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宋修义。按现在掌握的信息,这个家族的内讧的原因是争夺财产,就是那两片林地。双方互不相让,拼了个同归于尽。这个解释看起来很符合逻辑,也合情合理。
“江有沱要见你,有话跟你说。”孙一水扭着脖子,颈椎发出一阵轻响,“见不到你,就不说崔仁明那几个人埋在哪里。”
见金四九盯着墙壁,“他是关心他的马,我已经跟他朋友说了。”转头看着孙一水,“他关在哪儿?没受苦吧?”
“他没受苦,号子里的人受苦了。”
直周城只有一个看守所。江有沱被关进去的时候,在一个挺大的房间,地上全是地铺,里面有二十几号等待受审的嫌疑人,多数是这里的常客,大罪不犯,小罪不断的那种人。这里的规矩是欺生,并且按犯的罪排大小,大概是罪行越严重,人就越恶。最受人鄙视的是贪污和对儿童进行的犯罪。不知道多少年前,有个死刑犯在墙上刻了一行字保留至今:贪污的进来先喝尿,欺负孩子的,进来先割鸡巴。
房间很大,门口放着两个尿筲和一个屎筲。平时地铺距离屎尿筲的距离和受鄙视程度成反比。如果来了新人,新人在头几天睡门口。
江有沱进来的时候,那些人都坐在地上抠脚丫子搓脖子掏裤裆。江有沱见里面有个空位,不知道是个圈套,便过去坐了。然后旁边俩人用被单一下蒙住他的头,七八个人一拥而上,全程像哑剧一样没人吭声。江有沱护住头脸和要害,任他们打了一顿。没动静了,他才扯下满是尿骚和屎臭的被单。环顾众人,他们仍旧像先前一样抠脚丫搓脖子掏裤裆,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江有沱心里装着事,没计较。旁边一个人说,“伙计,哪个当儿的?因为啥?”
“八风镇,杀人。”
一说杀人,众人抠脚的穿上了鞋,掏裤裆的系上了裤子,都看向他。
“杀了几个?”
“二十。”
人群大笑起来,有人说,“这个傻咯子操哩[206]是个神经病,咱揍他一顿?不揍白不揍。”
左侧那人又像先前一样往他脸上蒙尿臊被单,江有沱当时坐在地铺上,一扬胳膊连被单带那人的手一把扯住,就势一拉,那人便扑倒在他大腿上,被江有沱右手一把抓住右耳,略一使劲,那人便觉耳朵要齐根断了似的大叫,“放开我,放开我,不放就弄死你……”
其他人停了手,围着看热闹。那人开始骂爹骂娘骂祖宗,江有沱松开他耳朵抬手给了他一耳光,鼻口窜血,那人还骂,接着又一巴掌,这回不骂了。
“兄弟,别打了,跟你闹着玩儿哩……”
既然认怂,江有沱一脚把他从身上蹬地上去。
那人站起来,左看右看找不到能用的武器,不知道谁往脚下扔了一截木棍,一端削得挺尖,像个小攮子。那人一把抓在手里,擦了一把鼻子上的血,狠狠吐了一口,人急失智,便嗷一声冲江有沱扑来。其他人见状马上过来帮忙。这种事,闹出人命也是处分领头的,谁拿了武器,谁带了头,谁就是领头。所以马上成了群殴。
江有沱早就站起了身,一把抓住刺来的手腕,另一只手托住对方胳膊肘,往里顺势一带,接着迅速往回一推往下猛力一拽,嘎巴一声,那人胳膊便脱了臼,武器自然脱手。江有沱抬腿一膝盖顶在对方小腹,那人嚎了一声倒地。
江有沱抡开巴掌,围攻的众人脸上像放鞭炮似的,声响处,必有口鼻见红。
一分钟不到,房间里清净了,全部捂着口鼻,指缝里冒着血,连嚎叫声都没有,只听一片痛苦的呻吟声。
江有沱在大房间里两天打了七回架,众人联名要开除他,请求看守给江有沱调房间,被告知没有空房。然后,江有沱的睡铺被安排到最里面的角落,那原本是“老大”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