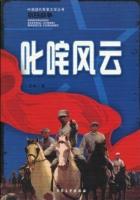宋修仁要去按摩,杨翠花说,“司机不在,你最好别自己开车,开车像个慌张三似的,又不把式,让宋修礼来,开车带你去。”
宋修仁给宋修礼打电话,宋修礼在电话里直哼哼,哎哟哎哟地说,“大哥,我跑茅子挺厉害,都提不上裤子,现在还在茅子里蹲着哩。”
宋修仁骂了句,“穷咯子[115]操哩,咋就跑茅子了?”
宋修礼有气无力地说,“哥,我喝扎啤喝的,那扎啤可能变质了,喝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对,又不舍得浪费,就喝了。严严喝了三大杯,稀屎马上就下来了,清汤,还挺臭……”
“好了好了,在家待着吧。”宋修仁挂了电话,冲杨翠花嘟囔,“怂包,说跑茅子哩,喝扎啤喝的。”
“我不用猜他就得这么说,他这是嫌天太热,肯定在掏空儿[116],指不定心里想干点啥哩。”
宋修仁没吱声,拿了车钥匙出去了。
杨翠花咬着嘴唇扭着腰跟着他出去,看他从车库里开出车,冲他摆了摆手,“回来前打电话,我好把水给你烧上泡一壶好茶晾着。”
宋修仁抬了一下胳膊算是听见了。
杨翠花看着汽车在并不平整的地面上张张歪歪晃晃悠悠越去越远,感觉幸福越来越近,心跳越来越剧烈,那种扑扑通通的声响,就像有人拿了一对鼓槌在使劲地捶打自己的胸腔。她哆嗦着手给宋修礼打电话,由于紧张而气喘吁吁,以至于不能连贯地说完一句完整的话,“他走了……快点来……蛛蛛网都要从房顶掉到床上把我糊住了……我浑身都是,快来袅一袅……”
她刚进街门还没关上,就听见小摩托的声音,是宋修礼。他刚才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是看着宋修仁离开的。
杨翠花吓了一跳,脸色潮红,胸脯起伏着,喜极而泣似的带着哭腔说,“你咋这么快?赶紧来。”宋修礼把摩托往门口一歪,闪身进来把门关上,想插门,被杨翠花拦住,“插门就出事了,这个家外人也不会来。他要是突然回来见门插着你又在这,就得死人了。”说着拉着他的手,在前面走的飞快,拉得宋修礼直趔趄,“你咋比我还急?”
杨翠花说,“废话,我熬了多少年了,就是一条大江也都快熬干了。”
还没进屋,杨翠花把拖拉板踢飞,死命拽着宋修礼往里屋的床上拖。她的眼睛红红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样子,像是一个复仇者把敌人拽向了断头台。她知道,宋修礼不是她的仇敌,也许宋修仁才是。
两人从下午三点开始袅蛛蛛网,直到下午六点还没袅完。宋修礼受不住了,说,“我得走了。”杨翠花抱住他,说,“来的时候那么急,走的时候也这么急,你是不是怕他知道?”
“当然了。你不怕?要是被撞见,我怎么说?袅蛛蛛网?”
杨翠花咯咯笑起来,往前一拱把宋修礼拱倒,骑住他来回蹭,像是在搓衣板上洗袜子,“他还没打电话来,再说,他开了车,能听到动静的,狗也会叫唤。听到动静再下地就赶趟儿。他要是问,随便掏个空儿不就糊弄过去?”
宋修礼使劲挺起上半身想坐起来,被杨翠花双手按住肩膀扑通一声摁了回去,娇笑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再来一回就放你走。”
宋修礼精疲力竭,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他不明白这女人怎么精力这么旺盛,床都快鼓捣塌了,咋还有这么大的劲?难道是吃了牛鞭?就是吃了牛蛋也不会这么神奇啊。他带着哭腔说,“你别摩了,再摩也起不来了,都三回了,你看,它是不是快死了?一点反应都没了,像是昏死过去似的。要是再弄,反醒不过来就是真死了。”
杨翠花打了个激灵,自上而下瞪着他,“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宋修仁的屌也是这么死的。”翻身下来,用手指戳了戳,把那黑不溜秋的东西从那一丛毛里翻出来,果然无精打采,跟一个藏在草丛里快死的降粘虫[117]似的。”她抓住宋修礼的胳膊,一使劲把他弄了起来,宋修礼赶紧把衣服穿上,嘟囔说,“快回来了,快回来了,趁他来前我赶紧回去,还得回去跑茅子哩。”
宋修礼走的时候,腰有点直不起来,像是饿死鬼似的肚子也瘪了。女人穿上衣服送他出去,关门的时候,“下回再来袅蛛蛛网。”
摩托车的声音去远了,女人背靠着门,掏出手机给宋修仁打电话,问问他按摩完了没有,这么晚还不回家,是不是死外面了。手机没人接。
杨翠花以为在开车,心里还想着这兄弟俩千万别在路上碰上。过了一会,眼看黑影子都下来了,宋修仁还没动静,难道去了公司?好几个公司,今天跑这明年跑那的也保不准。杨翠花又打了一次电话,电话无法接通。她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一个人出去,身边也没个可以联系的人,要是有事咋办?
杨翠花沉不住气,给宋修礼打电话,“你在哪儿呢?”
宋修礼吓一跳,刚到家还没歇过来呢就来电话,这女人是不是疯了?“我在家啊。”
“忙不忙?”
宋修礼听着有点不对劲,心里犯嘀咕,可能是宋修仁回来了,让杨翠花来试探他,看看是不是真的在家跑茅子,便吭哧着声音说,“我在茅子里蹲坑呢,跑茅子。”
“怎么跑茅子了?将一将不是还好好的?”
“我喝扎啤喝的。”宋修礼刚说完,就又觉得有点不对,杨翠花要是当着宋修仁的面,绝对不会说“将一将”袅蛛蛛网的事,马上改口一本正经地说,“什么事?我哥还没回来?”
“手机好像关机了,人找不到。你找个人去直周那家私人按摩诊所去看看吧。要不你去也行,你离那里也没多远。”
宋修礼觉得这事有点不同寻常,马上给大哥打电话,确实无法接通,看来是自动关机了。那家诊所他知道在哪,马上动身。从宋修礼家到那家诊所,不过半个小时车程。到了地方,诊所门口并没有看到宋修仁的奔驰车,按摩师傅说,“一个半钟头以前就走了呀。”
“他说要去哪没有?”
“没说,不是回家吗?”按摩师拉着宋修礼从诊所出来,指着诊所左边十来米远的一棵一搂粗的大杨树,“他来时开了奔驰,车就停在树下。”按摩师说不清楚宋修仁开车之后去了左边还是右边了。诊所在路南,往右是回家的路。从大杨树地面上的轮胎痕迹判断,宋修仁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往家的方向走,是往西边去了。往西能去哪儿呢?他出来的时候没带任何人,那就是说他没打算去其他地方,所以按摩完之后应该立马回来才对。如果有其他事,他一般不会一个人去,起码也得给宋修礼打个电话告诉他往什么地方去找他。
这个诊所虽然临路,但是地方很偏僻,再加上政府正搞一项美化工程,要清除违建,诊所对面及周围的房子都已搬空,不大可能会恰巧遇到什么熟人请他去吃饭之类。就算遇到熟人拐了弯儿,起码也得跟家人说一声吧?都没有。
宋修礼掐着腰看着灰不溜秋的柏油路,风从远处吹来,热一下凉一下的。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大哥从来不会这样一个人单独偷偷摸摸地出去,特别是晚上一个人去某个生疏的地方的情况几乎没有。宋修仁很清楚,整个直周城,恨他的人他都记不清有多少,他不认识人家,可人家认识他,他以为某人是个陌生人,没准却是一个恨不得他死的仇敌。所以如果要是真跟一个恨不得他死的陌生人狭路相逢,那人突然脑子抽风想要他命,那真是防不胜防啊。就算是揍他一顿跑了,他都找不到人。基于这样的判断,宋修礼猜,宋修仁遇到麻烦了。
他又给杨翠花打电话,问大哥有没有回来。杨翠花懒洋洋地说,“没有。”反问,“这么说,你没找到他?能去哪里呢?”
“别急,我联系公司里的保安,四处找找看。”
宋修礼没动地方,靠着大杨树给保安队长曹景凯打电话,这人对外还兼职着办公室主任一职,宋修仁平时要去哪里,也多半会跟他说。曹景凯正在跟人喝酒,房间里乱糟糟的,从房间出来,一听老板找不到了,连饭桌都没回,没跟谁打招呼就直接走了,他得召集公司里的保安去找人。
二十多个保安找了一晚上,把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所有能问的人也都问过了,一无所获。
当天过了夜里十点的时候,宋修礼去了宋修仁家,抱着最后一点希望,看看大哥是不是已经回来了,没准是躲在家里某个房间睡觉,杨翠花却不知道呢。
杨翠花已经睡下了。宋修礼给她打电话,她才开的们,张嘴就问,“还没找到?不会出事吧?”
“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没准是有什么危险,他树敌太多,大晚上,又是一个人,怕是凶多吉少。”
杨翠花听他这么说,感到十分害怕,“那可怎么办?会不会被人害死了?报警吧?”
“先不急,明儿个清早要是还没找到,就让警察找,他们手段多。”
杨翠花说,“晚上别走了,我挺害怕。”杨翠花舔着嘴,像是刚吃了烧鸡后舔去唇上的油,就那么来回舔,舔了上面舔下面。
宋修礼向外瞅了瞅,那条大狗正从院里看着他,两只眼睛反着蓝莹莹的光,像是两盏夜鬼提的灯笼。他往里侧挪了挪,不想跟狗眼对视。他盯着杨翠花的胸,这东西比以前大了一圈,以前就像是没充足气的洋茄子,经过下午反复地充气,感觉又圆又大了。宋修礼忍不住一把揽住杨翠花,发出一串嘿嘿的笑,“你身上又有蛛蛛网了,我来给你袅一袅?”
“你哥失踪了,还有心袅蛛蛛网?”女人说着,一把扯住他的裤衩,话锋一转,“你把我这熬干的大河续上了水,你可得送佛送到西,定期排洪清淤,不然会决堤的。”说着连推带搡把宋修礼弄到了里屋的床上。
房间里的钟表在黑暗中嗒嗒嗒地走动,远处传来潮水一般的鸡鸣和悠长深远的狗叫。呼呼的夜风在某个树洞中钻进钻出,发出鬼哭一般的呻吟声。宋修仁现在在哪?他们都不知道,也许并不会有人真的关心。在宋修礼和杨翠花眼里,他也许还不如一张蛛蛛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