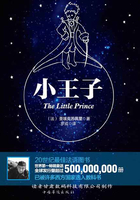一周后。
孙一水告诉金四九,警方有柳媚的线索了,可能在大黄庄,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看看。线索是柳庄的支书柳小峰提供的,他说,这是柳三狗告诉他的。
“差不离,应该就是了。”孙一水拐到派出所拉上金四九,掐头去尾地说了经过,“大黄庄有两个光棍儿,是兄弟俩,大的叫黄金,小的叫黄银。每年秋天都会开着三轮到地里偷棉花,进过好几次派出所了,拘也拘了,罚也罚了,就是没改。”
金四九回头看了一眼后窗,还有一辆警车跟在后面,孙一水带了两名队员,这是要准备抓人的架势。
“这么说,那柳媚没死?被这俩光棍给拐卖了?”金四九说。
“柳小峰说,可能是盗尸……”孙一水声音不大,看了一眼金四九,想看看他惊讶或者疑惑的样子,可金四九并没什么反应,托着下巴壳做沉思状。孙一水便有些失望地说,“不惊讶?”
金四九不吭声,看着窗外发呆,若有所思。
今天天气不错,窗外视野一马平川,随处可见犁地的拖拉机,把麦茬翻到地下,耙平之后随便种上些什么,秋后就会有些收成。
有连成一片的棉花地,阳光下绿得发黑,土地虽然贫瘠,这些植物却长得敦实。棉花已有了花蕾,藏在叶子下面的阴凉里,闪着浅黄或粉红的花。金四九以前没见过这种花瓣,他喜欢这种花的样子,像女人的裙子。
到大黄庄以后,他们先去了生产大队,大院里只有一个管事的在。孙一水表明来意,管事的给支书打电话,关机,给会计打电话,没人接。孙一水指着大院中央的一根大杆子说,“喊!”那杆子有十多米高,顶部对把儿装着四个大喇叭。“让支书抓紧来,有急事!”
管事的没见过这阵势,好几个警察,开着警车,领头的似乎脾气还不好,没准是来抓支书的。他小跑着进了值班小屋,大喇叭里传来“呼——呼——”两声吹气声,“喂,喂,黄龙飞,黄龙飞,听到广播,请抓紧到生产大队,公安局的找你哩……”大喇叭的声音够大,就算支书在邻村都能听见。
孙一水气得跺脚,等管事的从值班室出来,吼着说,“谁让你说公安局的来找他?”
管事的眨巴着眼,“你们不是公安局的?”
孙一水看他不是很机灵,再说能在支部当这差事的,不是老光棍就是身有残疾的五保户,便摆摆手,没吭声,到屋里找了个板凳坐下来。
金四九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地面上铺着红砖,西南角是茅房。他见管事儿的笑呵呵地看着警车的后视镜,还伸出手擦了擦镜面,金四九这才注意到他的手只有两根半手指,另一只手——根本就没有另一只手,手腕处是一个红色的球状物,像个肉疙瘩。
“你这手怎么弄的?”金四九指了一下。
他抬起胳膊,冲金四九展示着自己的手,“小时候从西地挖出个铁疙瘩玩,炸了,是颗手榴弹……”
正说着,支书骑着自行车来了,肩膀上扛着一把趟地用的铁耙子。还没下车就喊,“三坏,三坏,喊什么?!”
黄龙飞支住自行车,顺手把铁耙子搠[82]在墙上,扫了一眼院里的警车,“三坏,找我就找我,喊得那么详细干啥?我又没犯事!怎么像是犯事一样?”说着话,看到金四九,打量了两眼,不认识,小心地说,“警察同志,我是支书黄龙飞。”
“去屋里说,几句话的事。”金四九指了一下大屋,孙一水正在板凳上坐着。
到了会议室坐下来,黄龙飞结实说,“别跟喊喇叭的一般见识,他叫李三坏,你们也可以叫他三坏,这是他官名儿。他人不坏,小时候玩手榴弹炸坏了手,俩手加起来只剩下三根手指,所以叫三坏,脑子也炸坏了……”
“行了,黄书记。”孙一水赶时间,“黄金和黄银是不是你们村的?”
黄龙飞拍一下大腿,“果然又是这两个三眼架子!他们犯什么事了?我就知道,我们生产大队要是如果有社员犯事,肯定是出不了他俩。”
“带我们去!”孙一水站起来,面无表情。
黄龙飞点了点头,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那个什么……还没喝碗水呢……”
黄龙飞上车的时候,跺了跺脚,又拍了几下屁股,怕把车弄脏了。他的鞋上沾了泥巴,一跺脚,哗哗啦啦掉一地。
黄龙飞在副驾驶领路,“好近的,两个光棍在一个家住,临街,房后有一棵大椿树。”
一会儿就到了。黄氏兄弟没在家,街门紧锁,一条狗卧在门下的水口上避暑。远处的土路和墙头在阳光下白亮亮地散着热气,开起来像是泡在水里一样有些轻微的抖动变形。这有门下的水口处不但是个阴凉,还有点潮乎气儿。
黄龙飞用手拽了拽门上铁锁,转脸看着孙一水,一副“人没在,你看怎么办”的表情。
“弄开,我们进去。”
黄龙飞下腰抓住乘凉的黑狗的脖子上的皮,把狗拉了出去。那狗倒老实,开始还四脚摩着地,拧巴了几下,不情愿地站起来扑棱了几下毛,身上的土像烟一样散开,然后掉头钻进了院子。
黄龙飞双手把住右边的一扇门扇,往上一端,门扇从门墩上错开,往下一放,便把门扇摘了下来。他把门扇往地上一放,一侧勉强能挤过人。
大院里静悄悄的,有扫帚扫过的痕迹,落了一层细密的沙尘,一群在院子里觅食的麻雀被惊起来,哄一声飞到房顶和树梢上去。不知道为什么,叽叽喳喳的麻雀叫声以及知了断续嘶哑的嗓音却让这庭院显得异常寂静,是那种没有人气儿的死寂。晒衣服的铁丝上搭着被单子和几件衣服,在风里悠荡着,能看到落满了黑白掺杂的麻雀屎。有风,风进了庭院就分不清是东风还是南风,反正是热风,烘得人脸疼。
这个院落,院墙门朝东,有三间堂屋,两间东屋,都是平房。南边有个猪圈,但是没猪。院落东南角,也就是在街门正南侧有一眼井,看来已经废弃不用了,井口上并排压着两个打场[83]用的石磙。井旁有几棵榆树,树干上挂满了去年的玉黍。院子西侧的墙根处有一个露天的土灶,土灶前面散乱地放着一堆玉黍轴和麦秸。一根黑黢黢的烧火棍插在炉膛子里。
东屋的门开着,里面有一股潮气,是那种由于很久没有人气导致的什么东西发霉的气味儿,阴嗖嗖的。地上到处是沾了草沫子的棉花穗子和谷粒。一个盛着黄豆的搓斗随意扔在里侧的墙根处。窗台上有一只蜘蛛在结网,看来结了很长时间了,右上角的玻璃已被蛛网罩住,一只苍蝇说巧不巧地在此时鸣着喇叭撞到蛛网上,大概想着能冲个窟窿飞出去,却被粘住了。大灰的蜘蛛灵巧地跑酷一样地冲了过来,到跟前又突然停住,左右徘徊着,盯着挣扎中的苍蝇,大概在想等对方耗尽体力再饱餐一顿呢,还是现在下手比较好。
东屋门对面的东墙上有一个神龛,供奉着不知道什么神位,香炉里盛着半香炉高粱籽,几根燃过的香参差不齐地插在里面,歪歪扭扭。
孙一水和金四九穿过院子来到堂屋,黑漆木门涂着青颜色的边框,没锁,门扇错关着。
室内冲门一张大方桌,桌上方是窗户,钉着着一层塑料布。桌子上有几只碗和一只秫莛[84]筐子,筐子里有几个馍馍,皮干裂了,打着卷,像旱裂的地皮。干裂的皮下和馍馍的底部已长了醭。
三只碗,其中一只里还有没吃完的食物,长满了白中带绿的长毛。一双筷子在碗上,两双放在桌子上。看来主人还没吃完就走了,很匆忙的样子。
黄龙飞的在院子里带着哭腔喊,“都来看看,快点来……”他嗓音不洪亮,但是用的力气挺大,都破音了,像是被什么骇人的事吓破了嗓子。
黄龙飞背靠着井旁的一棵弯榆树,树干上长了虫,淌着褐色的黏糊糊的液体,他使劲往后靠,压烂了虫子屎,靠得树干直摇晃。他指着面前的井口,浑身筛糠一样地抖动,树枝上的干榆钱纷纷扬扬像雪片一样落下。“在里面,里面有人……”
这口井不是抽水井,是储水井。这个村没有甜水,村民用水要从邻村买,各家都有一眼这样的井,里面拿水泥抹了,把买来的水倒进去,吃完再买。自从通上自来水,这些井便废置了。
这眼井有两米深,大概是为了往外打水方便,所以井口很大。井台上的两个石磙紧挨着靠在一处,正好堵住井口。透过边沿的缝隙,能看到里面歪着两个人,一个趴在另一个身上,下面的人露着屁股和腿,明显是死了。一大片苍蝇附在两人身上,在上的那人的脸让苍蝇盖严实了,眼窝、鼻孔和嘴巴像是糊上一块黑泥巴,这些苍蝇趁着尸体还没移走,拼命地吸食着人体的汁液。
金四九看了一眼就感到反胃,闪到一边看着孙一水安排封锁现场,然后打电话叫人支援。
“他娘的个腿!刚才看到没来及收拾的碗筷我就有点不好的预感……”孙一水抽出一根烟,想递给金四九一根,刚拿出来想起来他不抽烟,又塞回到烟盒里。
“金教授你咋回事?没见过死人似的。”孙一水冲金四九笑了一下,不是嘲笑就是苦笑,绝对不是乐。
“是苍蝇。我现在每天都在跟苍蝇搏斗,哄哄的,吃饭、睡觉,特别是上厕所,闭着眼睛抡一下胳膊就能抓一把。”金四九仰头看着榆树翠绿的纸条,很难相信在这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树冠下,竟然有两具尸体被扔在井下。远处某个胡同深处传来悠长的号角声,“嘟——嘟嘟——”,好大的肺活量,是卖馒头的。那号角是个巨大的田螺,音色低沉,在这宁静的中午能瞬间穿透整个村落。这个卖馒头的小贩也许在别的村呢,不过谁说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