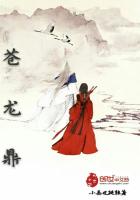陆晋知道阮北会离开,但是没想到她会这么快便瞒着所有人逃走。他这次做过了,既是有意为之,也是中人诡计。本以为阮北会闹,会不吃饭,会往他的药汤里放盐,同每一次闹别扭一样,至少她的离开会来的比现实晚一些。这样的想法钻进脑子里,陆晋自己也暗暗好笑,毕竟此次不同往常,阮北长大了。
江拾雨好像看不到一屋子大气不敢出的人战战兢兢的表情,满屋子弹松子用嘴接着吃,两片嘴皮子生怕松子呛不死正主,忙着上下翻飞讨人嫌:“兔子急了不仅会咬人,还能捅了窝跑了,哎呀,你说人一回来看到空兔子窝多沮丧啊,是不是?”
陆晋没理他,闲闲地翻了翻衣柜,随意扫了眼屋里的陈设,好像一点不着急。
江拾雨自己玩得不亦乐乎,但还是好心提醒:“还不去找?走一天了,出了凉州城你知道她去了哪?外面不太平,她就算有玉灵护着,时灵时不灵的,你能放心?”
“啰嗦。”
“哦哟,嫌弃起来我了哈?这两天要不是我给你输真气……”嘴碎的江拾雨获得一记白眼,忙改口:“你的伤寒能好得这么快吗?”说完心虚地观察周遭人的神情,生怕看出谁听明白了什么。
陆晋收回目光,知道江拾雨担心自己杀所有人灭口——管家成渠是自己用惯了的,其他人嘛,无关紧要。“渠老……”
陆晋手刚抬起来就被江拾雨按下了:“别别别,浪费浪费!”这根手指头一划不知道要取多少人性命。
陆晋斜睨着江拾雨,手终归是没再抬起来。——江拾雨知道怕也算是长脑子了!
日前陆晋特地将延期半月有余的同卢夏马商洽谈合作事宜重拾了起来,谁知人还没过卢夏国界,便听到兔子跑了的消息,赶回来就见到这样的场景。呵,想不到纪夫人还留了这一手诛心的好招。“走得聪明,这几天吃不了太大的苦。——坡上的血衣是女子军服?虞将军不在府上?”
管事答是,陆晋道:“我书房造通关文牒是落笔而就的事,她有点小聪明,北城门的阮北文牒很可能是计,跟着文牒追是不可能了。撒人出去问虞娘将军下落,跟着照应点。”
江拾雨听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好奇:“你怎知阮北同她在一起?”
陆晋无意识地敲了敲茶杯盖,不紧不慢的样子看着悠闲,唬得过满屋子下人,瞒不了从小穿一条裤子的江拾雨——陆晋是多压得住心思的人,杯盖子都叮哐敲起来了,心里不知怎么山崩地裂呢。
惯会装大尾巴狼的陆晋没在意到身边江拾雨的嘲讽脸,压着性子扶贫江拾雨的智商:“女兵中能力战一十三狼的有几人?知道山南道的有几人?”见他一脸痴呆实在恨铁不成钢:“求你长长脑子吧。”
江拾雨明显没能体会他的良苦用心,不着调地兴高采烈起来,蹦了一地松子壳:“你求我?!哈哈!你求我!!我以为你这辈子会求我的就是我家铸剑秘诀呢,没想到美梦今天居然实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陆晋习惯江拾雨间歇性发个疯,吩咐管事:“继续追查定魂佩,一旦发现,不计代价夺回,万不能让北北接近!动用宫中和军中势力查询靳方圆下落,化成白骨也给我挖出来。”抿了一口茶,欣赏了两眼江拾雨的痴呆样,想到虚则实之,还是吩咐管事:“北边关碟派崔长卿带着赤眼鹰去找,他手上漕运的事先交给李丰年。……注灵丹药准备个十颗,我要送礼……虞娘是宣城人,此去宣城半个月路程……去宣城开家首饰铺子,和最老的那家临近。”
管事一一应了,提醒主子:“布图那批勃利马东家还要吗,您走得急,小的怕他面子上过不去,您看是不是抬……”
“不用,让许珝去谈,价钱再压一成。今年雨水少,他手上的牧场多数受灾。卢夏市面上粮草都炒出稻米价了,十三盟更不可能帮他,五千匹马在他手里存不久。除了我,谁也要不起这么大一批。如今贺嘉氏正在抓布图的错处,买完放个消息出去,私通马市的罪名便能钉死他,李丰年的仇便报了。”贺嘉氏是卢夏王姓,近年卢夏十三盟已不如初建国之时团结,贺嘉王急需集中权力,如今送个把柄到贺嘉格多手上,既是卖个人情,也是展现一下实力。
李丰年原本是卢夏贵族姜奇氏后人,专为帝王训练骑兵,布图有意夺此一族权势,设计君臣离心,姜奇一族近乎全灭,李丰年逃到文道,改名换姓,誓要报得此仇,如今眼见贺嘉格多与布图齐齐二虎相争,应当宽慰。
似乎觉得和管家说得太多,陆晋呷了一口手里半温不凉的茶,越看江拾雨越糟心,那小子拨弄阮北的胭脂,在妆镜上画了匹海棠红小马,自己玩得不亦乐乎。“江拾雨,你跟我去关中。”
江拾雨一指胭脂戳出镜面,在花梨桌面上划出香气四溢的不解风情,惊道:“关中?你去宣城?那不是何晏君的地界吗,十五年之期未满……”
陆晋习惯性地打断他:“去不去?”
“……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