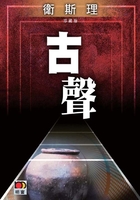吴奕说:“红粉佳人?你这也太矫情了,换个纯爷们的。”
我说:“我是一小姑娘,你看不出来吗? ”
吴奕冲着调酒师打了个响指,说:“再来一杯……”
不会是要对饮血腥玛丽吧?我赶紧抢着说:“我要玛格丽特。”
吴奕对我竖起大拇指,看来这款酒得到了他的认同,他说:“基酒是龙舌兰吧?我喜欢龙舌兰。这种热带的烈酒,喝起来很江湖,”他呷了一口猩红的血腥玛丽,接着说,“看过《生于七月四日》吗?墨西哥有一款龙舌兰酒,每杯里都泡了一条虫子,他们把酒一口吞下,再狠狠地将虫子吐出来,真给劲。”
我头皮又一阵麻,突然觉得血腥玛丽是多么温和的饮料啊。吴奕曾经是一个装腔作势的精品男人,不知这些日怎么突然变糙了?
喜欢同一款酒的人,口味竟然可以差别这么大,我和他欣赏的玛格丽特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说:“我并不在乎基酒是什么,哪怕是料酒兑的,我也照样喜欢,只要这酒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它还叫玛格丽特,我就中意它。”
“玛格丽特?”吴奕一挑眉,揣测其中的奥秘。
我爱这款酒,因为它是有故事的酒。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人在枕边讲:“很久很久以前……”所以长大后特别爱听故事,经过几年的恶补,我储备的故事总算在数量上和同龄人打成平手,只是他们知道的都是童话,而我的故事都很冷门,譬如手上这杯酒的来历。我不紧不慢地讲起来:“简·杜雷萨和玛格丽特是一对恋人,有一天他们外出打猎,玛格丽特不幸中流弹身亡。简·杜雷萨从此郁郁寡欢,1949年他把思念调制成一款鸡尾酒,这款酒获得全美鸡尾酒大赛的冠军,他将它命名为玛格丽特,纪念爱人。”
吴奕听得出神,拿过杯子去,轻啄一口,失望地摇摇头说:“徒有虚名。”
“这酒要一口闷。” 我纠正了他的品酒方式。
玛格丽特是短饮,需要一饮而尽。来自古巴的龙舌兰入口时有一种火辣的灼烧感,但这股热力又瞬间被青柠的温柔冲淡,末了,口腔里回转着一股淡淡的酸橙味,就好像体味到简·杜雷萨和玛格丽特的爱情,热烈中带着一抹哀思。我一直相信,好的调酒师既会调酒又会调情。
吴奕将信将疑地把一整杯酒一口灌了下去,表情顿时复杂起来,丰富的味觉刺激他展开丰富的联想。
我说:“鸡尾酒,喝的不是酒精,是故事。”
吴奕低头摆弄手中的空杯子,轻声说:“我有一个好故事,要听吗?”
他缓缓道来,语气平静,但这真不是一个平静的故事,连我这个旁听者都难以淡定,他怎么可以讲得风轻云淡?故事的梗概是:他父亲被举报,全家逃到俄罗斯,他现在毕业了,学生签证即将到期,马上要变成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但他却不能回到中国,他只能隐形在俄罗斯……
吴奕讲完,不等我有任何反应,自我解嘲地笑了两声,他想表现得洒脱,可是没演好,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幽幽地说:“知道我为什么要点血腥玛丽吗?”
“因为它残忍?”我想他是想点一杯应景的饮料烘托悲壮的气氛吧。
“不。”他摇摇头说,“因为它的基酒是伏特加——俄罗斯的土产。我现在已经无法离开俄罗斯了,我要学会喜欢俄罗斯,这样能够好过一点。”
他这么做,算是一个仪式吧?我想了想,反过来问他:“那你知道为什么用伏特加做基酒吗?”
吴奕摇头。
我说:“因为伏特加无色无味,有宽广的胸怀,容得下任何香料和色素,它能把番茄、胡椒、酱油、芥末这么多突兀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做成一杯还算可口的饮料,如此包容,也一定容得下你。”
吴奕会心一笑,大大地喝了一口酒。杯口的胡椒莳萝粉末融掉一半,这真是一杯疗伤的好酒,胡椒可以驱寒取暖,莳萝可以抚平忧郁。
我忍不住为他惋惜,他热爱的新闻事业是无以为继了,谁会雇佣一个身份不明的记者呢?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要怎样向读者起誓,保证他报道的都是真实的?我想起来上次我们谈到毕业考试时,他落魄地说还有两个月了,像一个被宣告了死期的癌症患者。原来,他热爱的事业,真的被宣告死期了。
我想安慰他几句,却真不知该说什么,我为自己的低EQ感到懊恼。
吴奕反倒安慰我:“别难过,我都不难过。我本来就不是做新闻的料,把你爸错看成贪官,又把我爸错看成清官。身边的事情都搞不清楚,怎么弄得清别的新闻事实呢?”
我问:“那你有什么打算?”现在已经不只是做不成记者的问题,没有合法身份,他找什么工作都是问题。
吴奕苦笑:“打算,有用吗?我曾经为自己认真地规划未来,结果呢?认命吧。今天,我决定拿所有的钱出来喝酒,我就是这么想的,花光了这些钱,我们再努力去挣钱,如果不能自食其力,那就证明自己是个草包,既然是草包,就不要奢望太多,回家当一张乖乖牌,不要总幻想自己是大英雄,卓尔不群。”
这一天,他很不开心,却在说每一句话时都辛苦地挤出一个笑容。后半夜,吴奕醉了,无力地摊在吧台上,我忍不住从后面抱住他,想要给他温暖。
“万紫,你不能喜欢我。”他突然说,我以为他醉了,没想到如此清醒。可他一动不动,任由我抱着。
我伏在他背上说:“凭什么呀?”
“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
“我也没前途啊,正好一对儿。”
“你不是有个很好的对象吗?”
“谁说的?”
“你啊,那晚在别墅,你说有个成熟男人,很帅,强壮,睿智,坚韧,专注。还是选择他比较正确。”
“哦,他呀。”我笑起来,吴奕的记性还真好,看来他一直对这个人耿耿于怀。我说,“我想选你。”
“走开,别过来。”他用的词汇很残忍,但语气却很温柔,并且他还是一动不动,纵容我伏在他的背上。
新闻系毕业典礼那天,我在礼堂寻寻觅觅,却不见吴奕身影,到处都是穿着学位服的毕业生,整齐划一的造型很难辨认,我绕着礼堂做地毯式搜索,挨个排查每一张脸,仍然找不到他。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到底去哪了?我匆匆赶回宿舍,他的房门虚掩着,从门缝里,我看到他忙忙碌碌的背影。我长长地松了口气,还好,他在这里。我走进去,却发现他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搬离主楼,顿时一种莫名的恐慌袭上心头,如果他悄悄地溜走了,我再也找不到他,该怎么办?
看到我,吴奕诧异地问:“你怎么来了?”
我生气地说:“还好我来了,你想要玩消失啊?”
吴奕笑笑:“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怎么没想到。”
他没什么东西要带走,就一箱相机,一箱照片,一箱衣服。还有一口纸箱子,里面全是书。他说:“来得正好,送你一箱礼物。”他指了指那个纸箱,我扒开箱子瞄了一眼,赶紧推到一边:“有没搞错,又是安娜攻击普京的书?你不知道普京是我的心头好吗?”
吴奕耸耸肩表示遗憾,说:“那就扔了吧。”
“扔了?安娜不是你的精神导师吗?”我知道吴奕是多么崇拜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怎么会扔掉她的著作呢?
他苦涩地笑起来:“是精神病导师吧?现在她只能将我导向精神分裂。”
明知不能做新闻,再看这些进步书籍插上理想的翅膀,只能徒增烦恼。对吴奕来说,哀莫大于心不死,心死了反倒轻松了。
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号码,接起来说:“马上就回来了,你看着办吧,随便吃什么都行。”
手机就在他的裤兜里,他是一直故意不接我电话的,我更加确信他准备甩掉我,然后人间蒸发。他现在是要搬去和父母住在一起吗?
我连忙说:“我送你回去。”我心里盘算着:我去认个门,你小子甭想随意消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吴奕冷冷地说:“不行。”
我一把拎起他装相机的箱子,紧紧抱住,挟持了这个宝贝箱子,他就不敢撇下我。
吴奕扑上来,想夺回“人质”。我恨恨地说:“别过来,小心我撕票。”我非常投入地恐吓他,因为他的不辞而别确实把我惹恼了。他被吓退半步,无奈地看着我,生怕我失手摔坏了这些精密仪器。
我们拖着箱子走出宿舍,坐在主楼正门的长台阶上,等预约的出租车。
校园里,很多学生在拍毕业照,穿着学位服,手里卷着学位证。穿上这种僧侣似的黑色长袍,硬着脖子顶着四方形的礼帽,一个个都不自觉地肃穆起来,只有帽檐垂下不安分的流苏暴露了他们驿动的青春。
我说:“你都没有拍毕业纪念照吧。”
吴奕指指我怀里的箱子,说:“那帮我拍一个吧。”
我打开箱子,挑选了一台相对比较傻瓜的相机。一边琢磨着怎么使用,一边说:“这哪算毕业照?长袍、证书、老师、同学,这些必备要素你全没有。”我都替他觉得凄凉。
吴奕笑:“毕业纪念照就是要记录毕业时的真实状态啊,我的真实状态就是这样。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说着他一手举起相机,伸长胳膊,把镜头对准自己,另一只手一把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拉进镜头里,利落地按下快门。镜头里,我们脸贴着脸,他嘴角一个浅笑,浅得肉眼难辨,我惊恐地瞪大眼睛,在他的相机里,我永远都是扭曲的,不是愤怒地竖着中指,就是哭成大花脸。
我说:“你拉着我干什么?”。
“留个证据。”说完,他指着远处台阶上正在拍集体照的一群人让我看,那群人站在台阶上排成高低有序的队伍,以便露出每个人的脸,摄影师数一二三,所有人齐刷刷地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吴奕说:“你觉得他们在干什么?集体制造一个证据而已,相片里有我有你有他,物证里面装着人证。这哪叫纪念照啊?时间里的真实片段才值得纪念,而这个整齐的方阵本来是不该存在于时间中的,是他们为了照相而故意制造的,照片也不过是为了纪念的纪念。”说到这里,他举起相机,远远地拍下那个方阵,接着说,“而我这一张才是纪念照,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镜头的存在,我记录的是他们毕业时的事实——他们在拍集体照的事实。”
同样是排列成方阵的集体照,人家自己相机拍的就是证据,你躲边上偷拍的就是纪念?吴奕这些怪道理搞得我消化不良,痛苦使人哲学,果然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