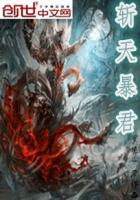我站在又陡又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沉入地下,觉得自己被巨大的黑洞吞噬,忍不住要转身逃跑,可是沿着下行电梯向上攀登,几时才能逃脱?
我开始惧怕出门,总觉得别人看我的眼光暗藏玄机,似乎听见背后有窸窸窣窣的议论。谁知躲在宿舍也不得安宁,大清早便听到一阵急促有力的敲门声,我感觉来者不善,战战兢兢地打开门,竟是万紫。唉,我早该想到是她,除了她还有谁这样敲门?
万紫拖着我一起庆祝男人节,我本要逃避,转念一想:“生活很无厘头,但还得继续,不如忙碌起来做好自己的事吧,我的人生又不是父亲的续集。”于是那一天,我在阿尔巴特街拍摄了一组雪人群像,格外认真地测光、取景、调焦,像一个认真作业的小三好。我挑选出五张照片发给《魅力神州》,让他们刊登在我的专栏里,这是继谢肉节之后,我最满意的一组作品。
谁知第二天我竟收到杂志社的退稿信,寥寥几句话,官方措辞:“你的大作已阅,虽然感到题材珍贵,摄影技术高超,并达到了发表的要求,但因我刊版面有限,安排不下,请另投他处。”这封信让我很意外,我是签约摄影师啊,怎么会收到这种火星邮件?
尽管我现在不得不计较国际长途的昂贵话费,我还是马上拨通了编辑的电话。
编辑说:“对不起,没来得及通知你,‘异域采风’的栏目从这期开始撤了。”他的语气中没有丝毫抱歉的味道。
我又惊又恼,问:“为什么?”
编辑说:“我也不太清楚,社长突然通知的,其实这个栏目本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咱们这边的读者对俄罗斯并不是很感兴趣。”
我刚要说点什么。编辑接着说:“你是签约摄影师,我们单方面解约,会按照合同赔偿你违约金的,明天到账。”
他们的财务处工作热情很高,从前给我支付稿费积极,现在结算分手费更是积极,巴不得立刻断绝关系。我说:“不用了。”
我想起韦铭以前说过的话:“你照片好卖,因为你爸是上级领导。”我当时傲慢地认为他嫉贤妒能,然而,竟被他说中。难怪在其他杂志我的照片都卖不起价钱,而在家乡却奇货可居,被几家小报社小杂志哄抢。一直以为是我的才华,结果……我出卖的是贞操。
不能刊登也好,我送出这样的照片,真是大逆不道。我拖动鼠标,翻看着我发给《魅力神州》的这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雪人的特写,我蹲在地上仰拍它,它显得高大伟岸,太阳在他的头顶,光芒万丈。
男人节那天,在堆满雪人的阿尔巴特街上,我给万紫讲了一个“雪大人”的故事:“有一个大人,完美无瑕,是孩子的偶像,可是一见阳光就化了,原来他是雪做的。”万紫听完撅着嘴说乏味,可是这故事对于我来说却五味杂陈。我拍摄了这张“雪大人”的照片,把它发给《魅力神州》,想告诉家乡的读者:“看,你们失踪的市长大人,他在这里。”
可是,雪大人见光死,他融化了,他的儿子也失去了发表照片的资格。
韦铭突然从msn上蹦出来。语气很兴奋:加拿大已经把稿子发过来了,太精彩了,我正在编。可惜他摄影水平不如你,没有一张像样的图片,干巴巴的。他要是像你跟拍“中指姑娘”那样,来一堆狂欢,打架,挥霍,痛哭……那多精彩。
我说:能不能不发?
韦铭:为什么?
我:总之我有苦衷,请你帮帮我。
韦铭:你没事吧?这么客气,吓着我。
我:兄弟,帮个忙吧。
韦铭:你说,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一起解决。
我:你别问了。
韦铭:你又被威胁了?
我:让你别问。
韦铭:怎么搞的?你那边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万紫的父亲没理由再威胁你了吧。
我:不是他,我们都搞错了,另有其人。他知道我们还在搞这个报道,怒了。
韦铭: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开车了。
不开车是事实。但接下来的理由,我打进对话框,又忍不住删掉了,再打上,反反复复,最后还是发送出去:前几天发现刹车被人搞坏了,我出了车祸,现在在医院里。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是今天又收到信,上面写着你的单位、电话、住址,还有你家人的名字。我害怕了……
韦铭:怎么会这样。你伤得严重吗?
我:医生来查房了,我先下了。你小心,稿子最好别发了。
不等他回答,我匆匆地把msn改为脱机状态,在暗处观察他的反应。
作为一个记者,以说真话为天职,我却撒谎了。为了我的家庭,我背叛了我的职业。
我的人生必须改变轨迹了。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层层递进,我的记者之路从理论上断绝了。因为要在记者这个行当中自我实现,必须要说真话。可这句真话又和其他更基础的需要水火不容。只有撒谎才能满足我的安全需要;为了归属与爱,我要用谎言保护我的家庭;为了不被扔臭鸡蛋,我还要用谎言来维护体面。满口谎言的人,还怎么在新闻行业中自我实现呢?
我为自己的谎言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持后,开始坦然地撰写一封恐吓信——在网上找了一张血腥的照片,在上面写道“下一个是你”,然后注册了一个新账户,发到韦铭的邮箱里。当我点击发送键时,我觉得我的灵魂已经被撕裂,支离破碎,它此时的模样一定比这张照片更血腥。
夜里一直做噩梦,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追赶着我,在无处可逃,濒临崩溃时,我被手机铃声唤醒,终于获救。黑暗中,手机发出煞白的光,显示出韦铭的名字,我料到是他,我一直在等待他的电话,但是电话来了,我又不敢接。我颤巍巍地按下接听键,韦铭焦急地对着电话喊:“吴奕,我也收到恐吓信了,看来他们这回要来真的。夜长梦多,我们不能再等了,看来必须提前发稿,以免他们阴谋得逞。”
我那封血淋淋的信多么逼真,他真的信了,可我本来是为了吓退他,谁知适得其反。我说:“你考虑清楚了,不要冲动,这事不简单,你要注意全家的安全啊。”
“我知道,你不要担心,”韦铭语气很沉着,他是大哥,要给小弟一颗定心丸,他接着说,“大半夜找你,就是想提醒你这几天也要注意安全。”
“谢谢你。”这句感谢哽在喉头,很艰难地吐出来,它明明是一句五讲四美的礼貌用语,可出口之时,真觉得它像呕吐物一样污秽。
韦铭,谢谢你关心我,可是你我的安全系数是成反比的。
挂断韦铭的电话,我继续举着手机,马上从通讯录里找到家里的电话号码。可是转念一想,这些事似乎不便在电话里讨论,看来必须回家一趟。这么晚,独自出门很危险,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光天化日下都敢明目张胆地袭击外国人,何况现在有风高月黑的好气氛。可是要等到明天吗?情况紧急,耽误一分钟,风险也增加一分,这漫长的夜会把我逼疯。
我找出一件外出拍摄时常穿的大风衣,有很多口袋,我喜欢在里面塞满胶卷,伸手即得。现在,我在衣兜里揣上了匕首和防狼喷雾剂。拿起喷雾剂,我心里一阵火辣辣的刺痛,就像被喷上了这灼热的辣椒水。这喷雾剂是韦铭送给我的,当年我们不知死活地跟拍光头党,他准备了这个辣椒水,以便在行迹败露时顺利脱逃。
我一路小跑到了地铁站,地铁到站停稳时,我正好站在两节车厢中间,前面的车厢空无一人,后面的车厢里面有一个中年壮汉。我犹豫着该上哪一个——空车厢,我自己上去自然安全,但有很多未知的风险,如果下一站上来了流氓,我将独自面对;而有壮汉的车厢,如果他是好人,我们可以互相照应,但他若是个坏人,我现在上去等于羊落虎口。地铁靠站时间有限,我不能犹豫太久,在关门的那一刹那,我奔进了空车厢。我最近很容易怀疑,自从得知自己的父亲都戴着面具,我还怎么去相信素昧平生的路人是善良的?
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暂时安全,满脑子都是韦铭,我想要思考出阻止他的策略,眼前却都是与他并肩作战的画面,无序地播放。过了两站,一个醉汉踉踉跄跄地挤进地铁门,手里提着酒瓶子,眉毛揪成一团,死死地盯住我。我心里一紧,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防狼喷雾,捏在手心。他看了我几眼,然后走到车厢的另一头,横躺在长椅上睡了过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怎么杯弓蛇影了?我患了被害妄想症吗?
快到了,看到在黑暗里漠然矗立的大楼中央还有一扇亮灯的窗户,我辨别不清那是几楼,却恍惚觉得那是为我留的一盏灯,为我亮着一线希望。我小跑起来。
总算平安到家,我开门进去,只见书房的灯还亮着,就是刚才看到的那道光吗?
我走近书房,看到我爸弓腰坐在桌前,光影中,他的面颊如雕刻一般,神色冷峻,好似那尊思想者。我敲敲门,他抬眼看我,很惊讶,可能因为太疲惫,他的表情肌并没有如实表现他惊讶的程度。他问:“怎么这会儿回来?”
我也问:“还没睡?”
他低声说:“学会儿俄语,老了记忆力不好,只能打疲劳战。”
我知道他是失眠了,发生这些事让他心力交瘁,我可怜他,只怕接下来告诉他的事会成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说:“我给你说点事。”
他微微紧张起来,我半夜跑来,他已经料到事情棘手。我把经过硬邦邦地讲了一遍,毫无修饰,或许我应该用委婉的措辞,照顾他虚弱的心脏。可是我恶向胆边生,一边讲一边冷酷地在心里默念:“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我说:“韦铭那边要提前发稿。我无能为力了,如果你在国内还有信得过的人,你就去最后一搏吧。”
“知道了。”我爸异常平静,我探测不到他的内心深处,不知道他在酝酿些什么。他的情绪就像是深海地震,你觉得他纹丝不动,可他却会引发一场毁灭性的海啸,将你吞噬。他就是这么不动声色地吞噬了不明来路的巨款,吞噬了我家的安宁,吞噬了我们所有人的灵魂。
又过了几天,一切都异常平静,可我却总觉得这平静之下暗流汹涌。直到有一天,韦铭发短信给我:战友,我也在医院里了。
我倒抽一口凉气,赶紧打电话给他。
韦铭丧气地说:“被人袭击了,电脑被黑了,那稿不能发了。”
“你没有备份?这不应该啊。”我了解他,做什么事都周到稳妥。
“有。”韦铭说。
我心一紧,这事还没完,都已经到了打手与黑客出场的地步,为什么还不能结束?到底要怎么样?我在心里暴躁地嘶吼,而说出口的话又虚弱无力:“那怎么不发呢?”
“他们扬言下一步会对付我的家人,我怕了,对不起,我没能坚持。”韦铭很自责。
“我理解。”我说。
“电脑被黑,是应付领导的一个托辞罢了。”韦铭自嘲地干笑一声,“我竟然说谎了。”
“我也理解。”我说。
“谢谢你。”韦铭充满感激地说,庆幸海内存知己。
一句感谢深深地刺痛了我,这电话我聊不下去了,我没法无耻到这个地步,我叮嘱他好好养伤,然后匆匆挂线。
一切都圆满结束,我不知是悲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