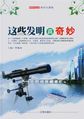派对还在火热地进行,大家沉浸在简单快乐中,不知道在这个大房子的某个角落里发生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这个热闹的生日派对,对于它的主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剩下的一切欢笑都显得那么傻气。
“伊凡雷帝”是魏何请来的贵宾,压轴表演。听“伊凡雷帝”的名字,像是会骂政府骂社会骂时代的愤青团伙。按理说魏何是不欣赏这种风格的,他很少责怪社会怎样怎样,他喜欢思考社会为什么要这样这样。
“伊凡雷帝”上场了,音乐一起,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干净明快,我们都跟着轻松的舞动,主唱鲁斯兰的表演颇有英伦摇滚的味道,唱我们最真实的生活,唱我们最简单的追求。演出把气氛带至最高潮,大家围在一起把鲁斯兰举过头顶,克拉拉看我孤零零地站在旁边,过来拉我加入。我俩走进人群,旁边站着几个彪形大汉,把鲁斯兰稳稳地举在半空,我和克拉拉伸手想要托一把,却够不着,克拉拉举着手频频跳起,非要碰到不可,跳着跳着突然停下扭头窃笑:“我刚才好像摸到不该摸的地方了。”
演出之后,大家到院子里烤肉,姑娘们切了一脸盆水果,一个满胳膊刺青的吉他手往里面挤了两袋沙拉酱,扣上另一个脸盆,癫痫一样猛摇。
鲁斯兰和魏何坐在树下喝酒聊天,鲁斯兰说:“租这房子,准备这些,不少花钱吧?我们乐队可以分担一些。”
魏何很豪迈地拒绝了。
鲁斯兰说:“千万收下,我们都是穷人,坚持做音乐不容易。”
魏何指着我说:“房子是她的。不花钱。”
鲁斯兰看看我,很惊讶。刺青男也听见了,捧着一盆子沙拉也不癫痫了,盯着我上下打量。我很害羞,慌忙逃开。
这一夜,大家都喝懵了,配合田园风景,我家小院成了农场,有装马让人骑的,有装蛇伏地蠕动的,有说自己会中国功夫,然后作鹰状作猴状的。克拉拉向来有坐在树上唱歌的恶习,她唱着唱着幻想自己是飞鼠,甩开胳膊往下跳,大周冲过去将她稳稳接住。不然就仙女下凡脸着地了。
我一个人在角落里呆着,有些怨恨自己。现在爸爸一定很伤心,还好有吴奕送他,他能在我最悲伤的时候逗我开心,应该也能安慰我爸吧。那我妈呢?
我和他们是命中注定的冤家吧?她在塔斯社做记者被派去北京,爱上了我爸。我姥姥极力反对,一为当时中苏关系不稳定,二为我爸有妻女。我妈热情勇敢执着地和我爸好,竟然怀孕了,她对我的到来恐惧莫名,想去医院把我还给上帝。姥姥却又反对了,她是虔诚的教徒,不允许人工流产,老太太对生命的重视胜过了政治上的利益权衡,于是我爸我妈偷偷地生下了我。
我天生不是低调的孩子,不久我爸的正室就知道了我的存在,她哭哭啼啼地跑去找我爸的领导主持公道,这个愚蠢的维权方式让我爸身陷纪委调查,调查项目齐全,细致入微,调查人员兴奋极了,经验告诉他们桃色新闻背后往往暗藏着内幕重重的经济大案,而我爸的故事更为生动,甚至兼有间谍嫌疑,不久我爸便下岗了。消息传回莫斯科,我妈虽未下岗,胜似下岗,从此后再未接到过像样的任务。他俩一定很恨我,我害他们失去一切。但更让他们无奈的是,在那段百无聊赖的岁月里,我又成了他们的全部事业,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精力都花在我身上,琴棋书画天文地理,像培养女特务一样管教我。我很乐意被他们管教,我很爱他们,我想他们也爱我。后来我妈复出了,她疯狂工作,像在报复岁月;我爸在陪我学习绘画的过程中,竟然像抛弃了过往秽浊的岁月,自己修炼成了一个画家(当然,有很多官员都有做艺术家书法家的潜质)。他们都有了真正的事业,就忘记我了,他们突然变得这么陌生……
我不能独自呆着,满脑子坏情绪,混浊不堪。当你被浑水装满,却找不到阀门释放时,那就注入些清水将它稀释吧。我走到魏何旁边,想要听听他们聊天。魏何和鲁斯兰没完没了地聊,鲁斯兰成熟而真诚,魅力十足。魏何认真得像个孩子,可爱极了,他不会爱上鲁斯兰吧?鲁斯兰看到我,跟我打了招呼,感谢我的邀请,他对我说:“开场的那首歌是你自己创作的?很棒,青春无敌。”
这个评价让我很沮丧,“青春”是代表浅薄和浮躁吗?可是我想要的是深刻而沉静。我苦笑,我天真地想要唱一首歌给父母,告诉他们我有多么爱他们,可是我刚刚唱完,又忍不住说了恶毒的话。
我说:“我的音乐很幼稚吧?连我自己都觉得幼稚,为什么会这样?”
刺青男路过,没头没脑地搭了一句:“因为你他妈的是有钱人!”
他喝多了,醉得像坨烂泥巴,我没搭理他。
他凑近我,喷着刺鼻的酒气说:“有钱人最肤浅,懂个屁的音乐!”
魏何拉开他,说:“朋友,话不是这样讲的。”
刺青男来劲了:“他娘的没吃过苦,懂什么叫生活?懂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渴望?操他妈的二世祖,我们不欢迎你,摇滚不是给你装B的。”
我觉得不可理喻,饿肚子才是痛苦?睡马路才叫痛苦?这些痛苦是表层的, skin deep。如果内心充满快乐,饥饿可以是修行,幕天席地可以是浪漫。真正的苦是心灵的痛苦,因为不快乐,才觉得难以承受。这个肤浅的男人哪懂得寂寞、孤独、无助?只要给他钱,他的那些所谓的苦就统统都甜了,他懂得什么叫痛苦?
我噌地站起来扯嗓子喊:“你懂个屁!”最后一个爆破音夹带了无数发璀璨的散弹喷了他一脸。他咬牙切齿要打我,我不知哪根筋短路,多半是被自己的肾上腺素呛晕了,很英勇地冲上去想要跟他对殴,眼看着短兵相接,被魏何和鲁斯兰把我俩隔离了。我熊熊燃烧的斗志哪能就此扑灭,魏何环腰把我往后拉,我却借着他的支撑跳起来,凌空一脚,可惜腿短,也没踢上。刺青男自己一晃神,摔了个大屁墩儿,看客大笑,我得意起来,“中国功夫——无影脚。See?”他羞愤交加,顺手捡了个酒瓶乱捶,酒瓶砸在树上,碎了一半,变成了一把利刃,他疯了般扑过来,我们慌忙跑开,他扑了空,气急败坏地把瓶子扔向我,我来不及闪躲,觉得自己快被刺瞎的刹那,大周飞过来将我扑倒,酒瓶戳进了他的额头,血流不止。刺青男自己也吓坏了,顿时酒醒了。我抱住大周,满手是血,不知所措。克拉拉大喊:“送医院,快送医院!”
魏何给大周简单包扎后,我们把大周送去医院,缝了八针,黑色的线头从伤口上伸出来,像极了蜘蛛舒展开细长的腿,张牙舞爪地趴在他的额头。我惊恐地打了一个寒颤,想起别墅里的那张蛛网,我真的触犯神灵了?我拉着大周嚎啕大哭,大周笑着说:“哭什么?傻丫头。”
神啊,我不是有意冒犯,请不要用鲜血来考验我们的友谊。
(吴奕)
我开车载万紫的父亲回市区。点火发动之后,我灭掉了车厢里的照明灯,他摸索着检查了一下安全带,露出一丝不安。汽车开出小院时,他回头看了看他家的小楼,那里仍然灯火通明、欢歌笑语,一派欢愉的节日气氛。我迅速开上公路,将那小楼抛到视线之外,我们这个狭小而昏暗的盒子,一头扎进无边的黑夜里。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嫌疑人关进了我的审讯室,接下来的两小时将由我掌控,但我却没有做好升堂的心理准备,犹犹豫豫开不了口。难怪衙门里升堂时都要聚集精壮衙役喊一声“威武”,原来是要给县太爷壮胆啊。
沉默了很久,黑暗里跳出一个声音:“不好意思,本来你可以多玩一会儿。”这声音来得突然,虽然很低沉,还是让我惊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是他先打破沉默,我定了定神,赶紧说:“没关系,我也不是很懂摇滚乐。”
这是实话,我今天跑来参加聚会的动机本来就与摇滚无关,甚至与万紫的生日无关。她们第一次邀请我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因为我不想面对大周。昨天我单独约了克拉拉见面,想要从她嘴里打听些线索。我们绕着公园散步时,她哼了一首很温暖的歌,我由衷赞叹,她说:“是万紫写的,她要在生日派对上演唱。”克拉拉是乐队主唱,为何万紫要喧宾夺主?加之这个词是写给至亲至爱的,直觉告诉我,这场聚会定有特别嘉宾。我决定前往现场一探究竟,谁知真的遇到万紫父亲。我开始相信自己是个天才记者,嗅觉这般灵敏。调查这些日子,核心人物终于出现了,我简直欣喜若狂。万紫和她父亲闹得不愉快,我反倒得了好处,争取来与核心人物单独相处的机会。有些乘人之危,我为我的机灵感到抱歉。
“您家住哪?”我问他地址。
“哪有家呀?在市区随便找个宾馆吧。”
“不跟万紫她们住一起?”
“不住在一起,对大家都好。”
我在网上看到,外逃贪官都是不和家人住在一起的,这样即便落网也不会牵连全家。而他尤其谨慎,平时独居彼得堡,连回莫斯科也不与家人团聚。我偷偷瞟了一眼他的侧脸,竟觉得有一抹孤胆英雄的悲壮色彩。
我说:“一家人还是应该生活在一起,会消除很多隔阂。”
他笑了:“我们不是一家人。”
我诧异。
他解释道:“我和她母亲不是夫妻。”
我糊涂了:“不好意思,我不太懂。”
他说:“我和万紫母亲,没有结婚证的。”
这可真是赤条条的裸官啊,连结婚证都没有。一旦东窗事发,牺牲他就够了,执法人员想顺藤摸瓜,都找不到藤。难怪万紫富得流油,她父亲却穷得连个车都没有。定是财产都在万紫和她母亲名下吧。
“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问。
“说来复杂,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不能与她结婚。等我可以与她结婚时,我们已经被生活折磨得互相怨恨了。不过这样也好。”
“为什么相爱的时候不能结婚?”
“我偷渡来的,怎么与她登记?”
偷渡?我兴奋了,却不敢问得太露骨,一时想不到安全的提问方式,只能先绕过这个问题,留出时间设计一个高明的计策。我另问一题:“那后来怎么又能结婚了呢?”
“在俄罗斯住了十几年了,人家也懒得把你遣送回去了,索性给你个身份,方便管理。”他答道,然后转过头看看我,笑着说,“你真像个记者。你是万紫的同学?学新闻的?”
被他察觉了,我不得不承认:“是,学新闻的,职业病。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些。”我傻笑一个,以显示自己天真无邪。
“没关系,可能好久没有跟中国人聊天了,才会和你聊这些。”
“您是想念中国了,应该回去看看。”
“回去看什么呢?快二十年了,城市面目全非。至于那些人呢,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愿见他们。”
“为什么?”
“我欠了一笔债,还不清的,所以我和债主们不如不见。”他落寞地说。
他家那么有钱,还能有还不清的债?定是欠了国家、欠了人民。
市区很快到了,我还想与他多聊一会儿,至少搞清楚好好的国家公务员,为什么要偷渡来俄罗斯啊。我看到街边有个小酒吧,于是对他说:“您一个人,去宾馆也是寂寞,不如我们去喝到天亮。”
万父还没来得及回答,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我爸。我打发他说:“不方便接电话,晚点再打给你。”说完快速挂掉电话。
万父听了,体贴地说:“你有事就快回吧。今天辛苦你了,谢谢。”
我连忙说:“没事,我们去喝酒。”
万父摆摆手,自己下了车。我有点气恼,好一个酒后吐真言的机会,就这么溜走了。我锁好车门,窝进座椅,长长地出了口气,把刚才绷紧的弦放松下来,然后拿起手机,拨电话回家。
我爸略带责备地问:“你忙什么呢?连电话都不方便讲?”
我有些小抱怨:“那个新闻调查,我刚才接触到核心人物。眼看着要揭晓谜底了,被你搅黄了。”
我爸提高分贝:“你还在为这事浪费时间? ”
我辩解道:“我没有浪费时间,这个调查马上就胜利完成了。我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了,就差当事人亲口证实了。”
我爸说:“你曝光这个对社会有何帮助?他们已经胜利逃亡了,你追不回人,也追不回钱。这样的报道仅仅满足一下小市民的偷窥欲罢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新闻价值。”
我反问:“那我们就沉默吗?看着这些蛀虫逍遥法外?虽然已经出逃的追不回来,但曝光之后,总可以让后来者无路可逃。”
我爸劝慰说:“你可以有一万种声张公平正义的办法,但显然做这个报道不是聪明的举动。你先停下调查,我帮你想想别的计策,既能达到目的,又能保证你的安全。”
世上哪有万全之策?我不怕危险,二十几岁的年纪不去冒险,恐怕这一生也只能庸庸碌碌了。我安慰他说:“下次我一定听你的,与你好好谋划。但是这一次只差一步了,我不会放弃。”
我爸急了:“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做这件事对你没有好处的!跟你说过多少次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