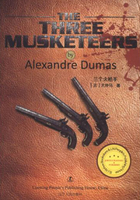接下来却无话可说,我想到刘小姗很可能是冲着我才应聘到公司,来了却看到我还和从前跟阮姐一样,和她表姐还有老板太太云姐扯不清,她一定伤心失望极了,我就有些无地自容。刘小姗随便买了几样日用品,于是去付款。款台前很热闹,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抱着玩具排队做游戏,又像生产车间的流水线,我提着货篮跟在刘小姗后面,——本来我们一直是并着肩的,但是刘小姗这时却昂首挺胸地走在前面,走在她神气的头颅和高雅的步态后面,我更加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永远摆脱不了款姐跟班的角色,永远也不过是人家养的小白脸。在阮姐那里是这样,在云姐那里是这样,在过去的李美和现在的刘小姗那里也是这样,这难道也是我的宿命?
快到我们时,刘小姗扭回脸朝我笑了一下,心照不宣地向上弯了弯嘴角。这善良的笑容把我拉回到现实,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缺少点什么,同时视线似乎自己落到了篮子里,我叫道,刘小姗,拖鞋!
什么拖鞋?刘小姗扭着脖子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有点惊异。
擦地拖鞋!
怎么啦?她转过身来,用手去翻篮子里的东西。
我们忘记买擦地拖鞋了。我对她的迟钝感到费解。
算了吧,下次再买。
下次?我忍不住笑了:你不是专门来买擦地拖鞋的吗?
刘小姗望着我,稍许,她也笑了,拉着我侧身挤过排队的人,重新进入货架的丛林。
有两个女孩推着小车和我们擦肩而过,我只匆匆一瞥就发现是我们公司某个部门的。她们含笑望着我,想给我打招呼,我冲她们笑笑,没有说话。这一切刘小姗浑然不觉,她在想什么呢?
擦地拖鞋们躺在一只巨大的箱子里,那只箱子像个小游泳池,而那些拖鞋像满当当一池子翻肚子的蛤蟆,准确点形容,那些长满毛线头的拖鞋更像绿毛乌龟。刘小姗拿起一双来,拆开包装,把手伸进鞋里去做了个擦地的动作,像在认真琢磨它能产生的效果。我望着她,笑而不语。
你觉得这东西管用吗?她歪过脑袋看着我。
我想伸出手去摸摸那些密匝匝的毛线头——它们像极了我们家乡用中间镶着满是小眼儿的铁皮的木制工具挤压下来的玉米面条,当面条密麻麻挂在铁皮下时,需要用刀子把它们切下来下到锅里;我想擦地拖鞋的发明者一定吃过这种面条,说不定跟我还是同乡——,但我忍住了:买不买是刘小姗的事情,我只是应邀来陪伴她,别人家的事情我最好还是少插嘴。这时有个别着胸卡的走过来冲刘小姗嚷:不要拆包装!
这双我要了。刘小姗不示弱。
但别胸卡的并不因此客气:那也不能拆,付款之前不能拆。
什么态度,我不要了!刘小姗把那双拖鞋重新塞进包装袋,把它们扔回了池子里。——那拖鞋翻着跟头跌进池子里,真像一只绿毛龟。刘小姗没再朝别胸卡的看,拉上我就走。
绕过几排货架,刘小姗脸上愠怒未褪。我指给她看头顶上的一块牌子,上面不太客气地写道:
请不要拆包装!
如果说这块牌子也有表情的话,那一定跟刚才那个别胸卡的一个德行。我若有所思地轻声说。
刘小姗收回目光,斜睨着我,扑哧笑了。分别多年后的重逢以来,少有的轻松和谐的气氛笼罩了我们,我暗忖:以前不了解跟刘小姗,跟她在一起时能享有饮食男女那样随心所欲的快乐的时光真是太鲜见了。她跟李美有些相象,不愧是表姐妹。
我们重新开始在货架的丛林里徐徐漫步。
你真不买拖鞋了?我忍不住问刘小姗。
不买了,家里有好几双都还能穿呢。刘小姗的目光在货架上滑行,对我的问题回答得漫不经心。
刘小姗的回答暗合了我潜意识里的某种猜测,其实这一切很简单,也就是那么回事吧。况且,从第一次在我电脑上留下“ILOVEYOU!—liuxiaoshan”,刘小姗的心思从未瞒过我,我敢说她从没想过要瞒我。——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不够含蓄的地方。她把对我的欣赏坦露无遗,我反而不能从中找到满足和快感了。
一个年轻女人推着购物车迎面走来,她的孩子很调皮,舒服地躺在货物上面。我和刘小姗的目光都被购物车上的孩子吸引过去,我低声在刘小姗的耳边幽了一默:嘿,这超市里还卖孩子?
我以为刘小姗要笑,她却有点愣神,像没听到我的妙语。我正想重复一遍,刘小姗猛地扭过脸来,面无表情地对我说,咱们也卖吧。
卖什么?轮到我愣神了,呆了一刻才弄明白她什么意思,机械地问,卖孩子?你有孩子了吗?哪里来的孩子可卖?
咱们俩可以生呀,生下来就卖掉。刘小姗盯着我,眼神热切而空洞。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有点傻眼地望着刘小姗。好在她突然酒醒一般摇了摇脑袋,仿佛被摄去的灵魂又回到了体内,她不好意思地笑了,柔声道,开玩笑呢,看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我这才发现自己也失了态,用手掌摸了一下额头,擦下一把冷汗来。——我在阮姐、云姐包括李美面前从来没有这样过,我在她们面前和在刘小姗面前仿佛不是同一个人。这一次的确被刘小姗吓了个够呛。我干笑一声,想来个自我解嘲,刘小姗却大步向前走去,我只好亦步亦趋地跟上。一阵浓烈而清新的蔬菜味道直灌鼻子,我们几乎同时止步了:嗨,怎么走进了蔬菜市场,——两个人的魂儿都丢了?
我们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地笑笑,绕着菜市场兜了个圈子。蔬菜味渐淡而烤面包的香甜气息渐浓。刘小姗扭头问我:饿了吗?先买个面包垫垫?
我说饿是饿了,不过超市里好像不让吃没付过钱的商品。
刘小姗笑得弯下了腰,挺起来的同时涨红着脸说,没事,吃了省下付钱了。她依次拿起几袋面包捏了捏,又都放下了,回头说,算了,还是去买热包子吧,也许包子直接可以付钱,别把你老人家饿坏了。
结果包子也打包封袋,刘小姗无可奈何地把那袋包子抱在胸前说,走吧,车上吃。
我们又一次向款台走去,刘小姗走在前面,我提着购物篮跟在后面,里面还是没有任何样式的拖鞋。
超市外面人的浓度跟里面差不多,而且流动速度明显得快,另一种乱。
从出门时刘小姗就走在我前面,像一只高贵的天鹅,我心里有点别扭,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样子的她,但我没吭气。刘小姗把买的东西都装进她大衣的那两只同样大的口袋里,还把两只手也插进去。朝存包处走的过程中她回头调皮地冲我笑了笑,我看了她一眼,还没吭气。拿上包,她又把那个帽子似的东西也塞进了口袋里,大衣前面鼓囊囊的,仿佛她是个准备出场的魔术师。看到我打量她,刘小姗索性抽出一只手来,扶在后腰那里,挺着被许多东西撑起来的肚子扭了几步。我哈哈大笑,刚才的不快已经溶化到被各种光线弄得支离破碎的夜空中。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刘小姗亲切起来,想去挽她的胳膊。但她似乎并没有跟我展示柔情的意思,只是挨着我缓缓地向街上走去。
公交车站牌插在雪堆里,不知哪个糊涂的家伙把它当一棵树来浇灌。站在刘小姗对面,我瑟瑟发抖。刘小姗看了看我问,冷吗?
我说你觉得呢?
那咱们打的回吧,别玩了。
没事,再等等,把游戏进行到底。
刘小姗认真地看了看我,她有点近视,看人的眼神很陌生。我这句话可能有点伤着了她,她脸上的笑容都掉进了积雪里。
我可能是有点饿了。我发着抖说。
那你要不先吃个包子?刘小姗的语气也开始生分起来。
我说车上再吃吧,拿出来就成冰球了。
刘小姗笑了,抬头看看车牌,眉头皱了起来。我跟着她的目光看去:
末班车——晚8∶30
老天,现在都快九点了。哈哈,我们开心起来。刘小姗一手拉着我往马路上跑,另一只手扬起来招呼出租车。
从出租车里望出去,街两边被各色的霓虹灯装扮着的店铺和高楼宛如异国风情,流动的光影在刘小姗脸上幻化出喜悦的表情,使她的面孔分外迷人。我一时不知今昔何昔、此地何地,迷路般茫然地问刘小姗,这是朝哪个方向走?是去我们公司吗?
刘小姗柔媚地白我一眼,把装包子的塑料袋解开举在我面前说,哥,先吃个包子吧。
我依然陷在浑然忘我的境界里,望过去,正碰上她亮亮的眼神,那眼神里含意丰富,包括对我此时如陷梦境的理解。刘小姗一直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她偶尔流露的那点女人的善解人意的可爱神情,仿佛也从那聪明而来。但如此聪明的一个女人,在我面前却甘于把自己置于一个崇拜者的角色,她是真心喜欢我,还是从我这里满足她作为一个女人需要的精神依托?——无论那聪明还是傻气,都不是我所喜欢的,而我却愿意与她相处,是因为我也需要有人欣赏吗?——还是,我们在一起的理由是彼此可以满足对方的心理需求?
到底你拿哪个呀,肉的还是素的?刘小姗审视着我问。我悠悠转醒,发现手还插在那塑料袋里,刚才因为思考而失神了。吃个素的吧,我说。刘小姗用纤细而温凉的手指握住我的腕子,把我的手拔出来,把她自己的手伸进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包子递给我。我一把拿过来,做出一副很食人间烟火的样子,狠狠地咬了一口。汁水溅了半脸,——原来是个肉包子!
我咬着那包子,扭过头去瞪着刘小姗,她开心地大笑起来,在我大腿上拍了一巴掌。然而那手却贴在那里不动了,我甚至感到它在微微用力。刘小姗若无其事地吃着包子,探身问司机:师傅,在您车上吃东西,不介意吧?
没事,别脏了车座就行,这是冬天,夏天在我车上吃雪糕的有的是呢。司机很爽快:能坐到我的车上,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我们都大笑起来,这年头这样有情调的人实在不多了。我低声对刘小姗说,无论如何,能坐在一辆车上,说明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
刘小姗不语,举着包子望着我。我接着说,《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唱道,“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并不完全是佛家的说教,你想想,众生芸芸,能在舟车中共渡,冒着撞车沉船的危险,也算是经历了一回生死考验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算是共同经历和见证了一段生命吧。你想想,两个陌生人,如果没有这种机缘,在彼此的生活里,岂不是跟死人没有分别?
在昏暗的车里,刘小姗那只手慢慢从我大腿上抽去,同时眼神里聚集起专注的光芒,似乎不接触我,才更能体会到我的高深,——在我面前她又恢复了一个实习生的角色。但我却渐渐感到一种悲哀,与把作为漂亮女人的刘小姗拥在怀里相比,得到作为聪明女人的刘小姗的欣赏突然间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没有意义。
像你这样诗意的人,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和你坐在一起。刘小姗带着自炫的神情说,同时在等待着我肯定的答复。我笑一笑,胸中充塞着悲哀和苍凉,——我突然想到:一个女人毫无保留地欣赏你,或许不是爱你,而是想通过对你无条件的推崇来印证她自己与你的接近和与别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