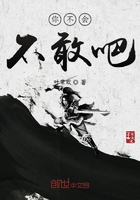最后一句话他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尾音上扬,带着怒和痛,暗沉的目光紧紧盯住白倾念的脸,“怎么不说话了?你默认了吗?”
白倾念被突然发怒的池北辙惊得脸色一白,再加上她确实被顾景年感动,在知道顾景年的真实身世后,她更加同情顾景年,决定放弃爱池北辙,试图去爱顾景年。
被池北辙一番质问,她有些心虚,躲闪着池北辙犀利的目光,她仰着下巴反击回去,“那是我的丈夫,我为什么不可以爱他?”
她这一抬下巴间,白日里顾景年在她下巴至脖颈处留下的吻痕就落在了池北辙的眼底。
他的目光陡然一暗,错以为是灯光照射的缘故,出其不意地推高她的下巴,逼她仰起脖颈,仔细看清楚那些痕迹后,他眼眸里的火苗慢慢地燃烧起来,直至火光充盈他整双眼睛,他掐住她的下巴,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真的让他碰了你?”
疼痛感从下巴上传来,白倾念恼得要拍掉池北辙的手,但她看到池北辙发怒的眼中慢慢浮起的一条一条血丝,她的心像是被狠狠划了一刀一样,冰冷的神色渐渐露出痛苦,“昨晚我喝醉了……”
“喝醉?你明知道顾景年一直都想要你,你这个喝醉究竟是无意,还是借此顺水推舟?”池北辙抽出垫在白倾念腰后的手,移到前面扯着她的衣服,随着渐渐露出的皮肤,他看到上面更多、更清晰的吻痕。
他的手指像是被重物击中一样,突然跌落下来,高大的身形也是一晃,险些倒下去,出于本能地扣住黑色的柳树干。
心口熟悉的剧痛传来,他只觉得连呼吸都开始困难起来,眼前一阵阵晕眩,视线模糊地看着胸膛前自己深爱的女人,他的喉咙如被火烧,声音沙哑,字字艰难,“你给他了?林音,你忘记了你答应过我,只把你的身体给我一个男人吗?”
耳边有寒风呼啸而过,刮得白倾念的脸一片生疼,在这样冰冷的夜晚和一池湖水前,她却蓦地想起以往无数个夏日的深夜里,他平躺在她家荷花池前的木质长椅上,伸出长臂拉她入怀。
林家住处偏僻,四周几乎没有其他建筑物,母亲喜爱池北辙,每次看到他们去了荷花池,总会打发所有四处走动的人,连景观灯都命人全部关掉。
有母亲的支持,他们之间的欢爱从未被人打扰过,耳边有蛙声和蝉鸣,他粗重的喘息,她娇媚的呻吟,月华如水从头顶照下来,整个天地间似乎只有他们两人。
他一面冲撞着她的身体,一面咬着她的耳朵要她说爱他,要她承诺以后只能有他一个男人,只有他才能这样对她。
记忆如潮水将她淹没,曾经那么刻骨,那么用力地爱过,她穷尽毕生漫长时光也无法忘记,他整个人早已被熬成了她身体的毒,生命还没有耗完,她如何才能不再爱他?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将白倾念包围,她只觉得自己整个人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心底升起淡淡的绝望,埋藏在心底的爱恋被他逼得爆发出来,她红着眼睛冲他用力地吼,“对!我承诺过今生只有你一个男人,今生非你不嫁,但我最终还是嫁给了顾景年,我最终还是和他发生了关系。”
“你呢?你也给过我同样的承诺,我现在问你,我不在的这五年里,你就没有过其他女人吗?你说过非我不娶,再过几天不还是要和景曦结婚了吗?为什么你自己也违背誓言的同时,还能理直气壮地问我这种话?池北辙,既然我们都无法信守承诺,为什么还要折磨彼此?试着放手不好吗?”
“我不放!我死也不放!”池北辙突然用力抱住白倾念颤抖的肩膀,“你失忆的那段时间,我也以为你和顾景年上床了,但我从来没有在乎过,我所恨的是你那时的遗忘。后来我知道了这五年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虽然庆幸你的身体仍旧只属于我一个人,但就算你真的和顾景年上床了,这也不是我放开你的借口。”
他低哑的声音里夹杂着酸楚和苦痛,“林音,我没有背叛你,你离开的这五年,我不仅没有和任何女人发生过关系,我甚至连亲吻都没有给过任何女人。”
“我的伪装和谎言那么拙劣,柯雅韵知道我爱你,顾景曦知道我爱你,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爱你,为什么只有你还是不懂?你是不是要我把心掏出来,捧在你眼下,你才能看到里面全部都是你?”
“我懂你什么?”白倾念没有推开池北辙,从他胸膛间低头看着地上的积雪,心里凉了一片,“你不再戴送给你的手表,不再把你的拥抱和柔情只给我一个女人,我能看到的只有你搂着顾景曦说着曾对我说过的情话,能想到的只有晚上你和她做着曾对我做过的事,你还要我怎么懂?我不想懂。”
她抬起眼睛,想看清他的脸,眼中却好像起了一场大雾,白茫茫一片,“池北辙,既然我们彼此都背叛了彼此,那么我们两人之间两清,谁也不再欠谁,从此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
“好一句互不相欠,老死不再往来。”池北辙眼眸深处涌出一团猩红的光,咬牙说完后,他松开白倾念,大手扣着她的后脑勺,低头用力地吻上去。
白倾念一瞬间被池北辙堵住了唇,惊恼让她脑中一片空白,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离她几厘米远的眼睫毛,她的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白倾念被吻得失去了反抗的能力,细若无骨的腰被池北辙一手握着,往上推了几分,浓密乌黑的眼睫毛颤抖如雨中墨蝶,她感到片刻的窒息,本能地低叫出声。
“音音……”池北辙抵在她唇间,粗喘着低声说:“音音,我好想你……”
难耐的欲望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尾音绵长低沉,眼眸里的怒火慢慢散去,变成渴望和情欲,灯光洒进去,竟然带着平日里看不到的迷离和潮湿。
白倾念盯着他温情柔软的表情,想起这些日子里他伪装的漠然和冰冷,她心底顿时升起莫大的委屈来,眼睛里酸痛难忍,恼得去推他的脸。
谁知他突然捉住她的手腕,高大的身体再度向她压来,不给她反应的时间,已经再次吻了上来。
池北辙狂猛的吻激得白倾念呼吸困难、腿脚发软,她意识恍惚地伸手去搂池北辙的脖颈之际,也不知道池北辙何时把她外衣的扣子解开,冰冷的空气随之钻了进去,只是下一秒,寒意就被他滚烫的大手驱散。
忽冷忽热的交替,让白倾念的脑子好不容易清醒了一些,耳边传来皮带扣的声响,白倾念陡然睁大的眼睛。
他难道真想在冰天雪地里要了她?
她浑身一个激灵,脸色由白转红,再由红转白。
她处于半混沌半清明的脑子里想到刚刚她还下定决心放弃池北辙,昨天晚上她还和顾景年做过,此刻又被池北辙碰,她感到屈辱的同时,再次觉得自己的肮脏。
她早已是和顾景年领过证的合法妻子,而池北辙和顾景曦也即将结婚,她却还是和池北辙纠缠不清,先不说传到外界别人会痛骂她,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下贱。
尊严和道德让白倾念心底的痛苦一点点叠加起来,在眼泪夺眶而出之前,她狠狠闭上眼睛,伸手用力在池北辙脸上狠狠一抓。
她的指甲不算长,但在人的皮肤上一划,就是几条血痕,池北辙拧眉“唔”了一声。
白倾念趁他分神之际,屈起膝盖往他的下身顶上去。
但池北辙身形高大,即便此刻他俯低了大半的身子,白倾念那一顶也用尽了力气,不仅没有推动他丝毫,他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把她反压到柳树干上,被激怒的男人声音阴沉地说:“林音,你这一辈子都是我的,只要我还活着的一天,你就休想让我放开你。还有……”
他低头咬着她的耳朵说:“趁早打消和顾景年在一起的念头,我不允许你爱上他。”,另一只手顺利钻入她的衣裙内。
白倾念仰起修长的脖颈羞恼地说:“爱不爱谁是我自己的事,你管不住我。”
池北辙看到她脖颈上密密麻麻的暗色痕迹,眸色再次暗沉了几分,他的视线紧锁着白倾念痛苦却仍旧不屈服的表情,声音阴沉中透着巨大的胁迫,“你且试试看林音,反正我强占你已经不止一次了,只要你敢再让顾景年碰你,我会理解为你愿意继续让我强占。”
“你……”白倾念无措地伸手抱住池北辙的肩膀,浑身瘫软。
她眼中的泪水倏忽溅落,泪眼朦胧地看着池北辙那张俊魅绝伦的脸,只感到陌生,心底生出深深的悲凉和绝望来。
她在这一刻突然想起顾景年来,想起顾景年从来不会强迫她做这种事,想起顾景年在欲望之下隐忍的脸,更想起他在半夜把她拥入怀里的那一瞬间,轻柔得像是把她当做心尖上的宝。
她心中装的满满的都是顾景年,他微笑时上挑的漆黑凤眸,他抱住她时修长有力的手臂,他在白雪中向她走近,问她那株水晶桃花树是否好看时,眼中盛满比桃花还要妖娆的笑。
白倾念猛地闭上眼睛,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她和池北辙这段长达十年的爱情,或许就会在此刻走到了尽头。
白倾念无力地靠在柳树干上,目光落在前方的池水里,池水在灯光和白雪的映衬下潋滟生辉,她的眼中却是一片空洞迷惘。
顾景年也说过爱她,而她面对两个深爱她的男人,不想伤害任何一方,两方却都在用爱逼迫她,她又该怎么选择?
池北辙闭着眼睛趴在白倾念的肩膀上,嗅着她头发间的香气,低声说:“音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把证据交给警方,顾家就完了。那时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开顾景年了。”
池北辙就是只喂不饱的狼,白倾念觉察到他再次起了反应,她用力一咬唇,咽下了反击的话语,心底生出一种无望之感来,走到这种地步,她再逃避也没有用。
她相信池北辙爱她,但她和池北辙的感情早已在时光和现实中变质,即便曾经她和他相恋,一直受到父亲和池北辙母亲的阻拦,她也没有像此刻觉得这么疲倦过,也或者她早就觉得累了,只是从来没有发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