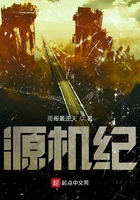乔瓦尼刚认识西蒙娜时,她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学生,胸不大,眼神犀利,她的父亲在患病之前,曾是外交部的一名高官。他们在乔瓦尼的毕业派对上相识,那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不勒斯最热闹的一场毕业派对,空气中都弥漫着酒精味。乔瓦尼在学院里结交的所有朋友都来了,还有些朋友的朋友也来凑热闹。再加上一大堆表亲,光是他妈妈就有兄弟姐妹六个。更别提那些老朋友以及不算很老但又许久没联系的朋友。对于乔瓦尼这种从不赶时髦的人来说,那次派对着实显得有些过于盛大了,一两百人挤在他家的天台上,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此前都素未谋面。
那天晚上他吻了三个女孩儿,西蒙娜是最后一个。派对结束之后,凌晨四点,他们俩和另外几个朋友拿着些酒出去继续玩儿,直至拂晓时分,朋友们的身影随着逐渐泛白的天空遗失在视线里,于是他们把车开到附近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车后座上发生了性关系。
再后来他点燃了一支烟,问她是跟谁一起来参加派对的。
“和里卡多。”她回答道。
几年前乔瓦尼在大学里认识了里卡多,他既是同校的校友,也是来自同一个省份的老乡。不过,里卡多受虐般的学习热情让每一个想要了解他的同学望而却步。为了能准时上课,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先坐火车然后换乘公共汽车,之后还要再徒步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学校。晚上回家之后,仍会孜孜不倦地学习到凌晨两点。在校园里,里卡多无处不在,每场研讨会都有他的身影,要是你不知道哪里能复印,或者不清楚教授们的接待日,找他准没错。但是在校外他就像不存在一样,大家对他的印象就只剩下他身上特有的气味,那是种火车车厢、背包和奶酪三明治混杂的气味。然后就是他那双粗糙的手,如农民般的大手磨得有些发亮,但是没有人知道上哪儿去找他。
“你怎么会问这个?”西蒙娜问道。
“随便问问,就想知道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西蒙娜沉默了,一时间有些琢磨不透他的用意。
“你真的就是随便问问吗?”
“那当然。”
她突然大笑起来,说:“你是想说,结果我和举办派对的人发生关系了吗?”
“这难道不是事实?”乔瓦尼回答道。
“哈哈,那你是不是得好好奖励我?”
没承想奖励即是婚姻。两个家庭都觉得这有些仓促、草率(虽然双方家长见面的那天,没有人敢在那个昏暗的、墙上还贴着神父画像的餐厅里公开表露出来)。
当乔瓦尼差不多挣到四千万里拉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感到出乎意料。他没有大手大脚花钱的恶习,于是他决定将积蓄用于投资房产,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大街上买了一套房。西蒙娜越来越频繁地去那里,两人差不多算是同居了,即使不是正式的,也并非永久性的同居。
直到有一天,他从办公室回到家,想起几个月前,他答应给她一个奖励,而当时西蒙娜面带微笑的回答已经预示了接下来将发生的一切。他向她求婚,她点头应允。
婚姻让二人彻底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但是乔瓦尼的前任——臭名昭著的卡拉,时不时地还给他打电话,她是一家日式按摩中心的老板娘。每次打电话,卡拉都在重复着那几个单调的话题,“我们得找机会见见,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等等。乔瓦尼感觉很为难,一方面,他不想伤害一个他曾经爱过的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表明自己不会重回过去的立场。他总是尽量礼貌地回答,但始终没有答应和她见面,毕竟他都是已经结婚的人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西蒙娜接了电话,电话那头卡拉沙哑又深沉的声音,正如她所期望的那般伤心。可没过两个月,卡拉就再次出现,在挂掉电话之后又消失几个月,如此反复了好几次,直到乔瓦尼告诉她西蒙娜怀孕了。
与卡拉不同,西蒙娜最重要的一位前任从未现身过,所以乔瓦尼没有机会认识他,只知道他是一位身家上亿的建筑师,据说比她大十岁,晚上睡觉的时候偶尔会梦游,一生中就只在他父亲去世时哭了一次。有一次醋坛子打翻了,妒火中烧的他一时没把握好分寸,在西蒙娜脸上给了她一拳。西蒙娜向来都不是度量小的人,但那次他太过分了,彻底逾越了她的底线,他们就此分手。那一拳在西蒙娜的鼻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即使到了今天,如果你对着光仔细观察,仍能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卡拉的来电之外,婚姻的头几个月令人陶醉。他们几乎不怎么着家,整整一年,他们似乎忙到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派对、晚宴、鸡尾酒、假期……他们忙于社交,当然,还有周末长时间的性生活。
尽管异常困难,他们还是抽空把家里简单装修了一下,虽然仍旧没有一个像样的柜子,餐具的数量也不足以应付那些不请自来的朋友。
他们性生活频繁,西蒙娜开始频繁验孕。
社会保守主义的守护神和掌管人类不幸之神,他们疲于欣赏一对新婚夫妇愉快地辗转于各个城市之间,遂决定结束他们这种纵情享乐的生活,将乔瓦尼微醺的精子与西蒙娜亢奋的卵子相结合。
巴托一出生就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孩子,至少他的父母是这么觉得的。他们对抚养孩子一点概念都没有,在一个连像样的柜子都没有的家里抚养一只小怪物。巴托会在晚上用指甲划破脸,每隔几小时就会醒来一次,然后紧紧吸住母亲的乳头。
西蒙娜的妈妈以帮他们带孩子为由住了进来,同时也带走了他们不着调的生活方式和糟糕的卫生状况,终结了这个家里之前的无政府状态。家里逐渐变得井井有条,布置妥当,凌晨三点的时候,再也不会看到他们嘻嘻闹闹,从玄关跑到卧室里做爱,沿路还不时会撞倒一些竹子制的家具,或者被地毯绊倒。餐具的数量变得刚刚好,与朋友共进晚餐已经成为古老的记忆。
“二十六岁就放弃追逐梦想未免有点为时过早。”
那时的西蒙娜因为产后焦虑症迷茫不已,几乎要放弃了继续进修心理学的想法,乔瓦尼的这句话像一剂定心丸一样,让她觉得无比心安,又给予她力量和勇气。那一刻她心里认定身旁站着的是全世界最成熟的男人。
当西蒙娜忙于进修课程时,乔瓦尼决定暂时停下工作缓一缓,与此同时,巴托也逐渐长大,他的手势变得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家里开始显得空空荡荡,是一种他们两人渴望已久但又从未有过的空旷。就这样,西蒙娜和乔瓦尼开始对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乔瓦尼非常惊讶地发现,他的妻子每个月都要花一大笔钱来购置各种各样的护肤品,面霜、身体乳、护手霜,等等;她只用一个牌子的洗发水来护理她的鬈发(说起这款洗发水的发展历程,也算是历经重重险阻,终于达到了今天的知名度);经期的时候,她并不会用广告里的那些普通卫生巾,而是像鱼雷一样的卫生棉条,一个一个排列整齐地躺在严密的包装盒里;每周二、周四的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二十之间会去游泳池游泳;极其厌恶惊悚片和恐怖片;讨厌起泡的葡萄酒;在她所有害怕的事情里面,排名第一的是被强奸;她发自内心地厌恶任何大男子主义的行为;从来不吃超市里买来的熟食,因为一般都是高脂肪产品。另外,也不知怎的,她对雀巢这个牌子的敌意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
可有一点让乔瓦尼百思不得其解,凭他对西蒙娜的了解,她应该不是那种对这座城市充满敌意的人。许多人觉得那不勒斯这座城市像个传染病,只要身在其中就会被感染,但是她属于那种少数典型的——认为在那不勒斯这样的地方还能正常生活的人。她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嘈杂,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生活着。可是,看似与这座城相安无事的她,又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她愿意铲除这座城市。
西蒙娜也在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她的丈夫。他栗色的头发和胡子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变得有些偏红色;周末的时候会穿着破旧又过时的卫衣四处走走(他还特别喜欢穿成这样);腹泻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他那本就带有地方口音的意大利语在他生气的时候还会不自觉地爆出几句方言来,而她好像也受他影响,讲话的时候偶尔会冒出几句来;性格的话,在有些场合他会过于腼腆,总体来看缺乏斗志,也没有什么远大宏图;他有时发表的见解和看法,实际上是从某本书或者某本杂志上看到的,要么就是与别人聊天时谈到的,可他却不记得了,还以为是自己的看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婚姻里某个暗藏危机的开关仿佛被打开了。一周五个工作日,还要肩负抚养孩子的重任,无聊的种子开始发芽,他们开始对彼此有了更为苛刻的评判。西蒙娜在某些方面的自我封闭,比如拒绝看恐怖片和暴力电影,成了件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阳光下乔瓦尼微红的头发变得平淡无奇,性生活也不如从前和谐。
乔瓦尼开始渴望一个情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身体的某个部分想要一个情人。问题在于,这个部分没有将这种渴望传达给身体的其他部分,身体的各个部分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导致了整体行为无效。
他的眼神四处放电,但他从不与任何人搭讪,如果碰巧有女人和他的眼神对上了,那他很有可能会赶紧逃走。因为对于这种主动的回应,乔瓦尼身体里那个渴望情人的部分并不想表现出惊讶,这迫使他逃离到安全的地方,丝毫不在意这完全有悖于刚刚做的事情。
他唯一的半次悲催的“出轨”,发生在雪地上。
西蒙娜七岁时便在奥地利学会了滑雪,于是,她决定要让她的两个男人也学会滑雪。
“虎妈无犬子,”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西蒙娜关上行李箱说道,“所以巴托肯定轻轻松松就能学会滑雪。”
“但是俗话说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要真按这个理论,他估计是学不会了。”乔瓦尼否认道。
西蒙娜大笑起来,然后把行李箱从床上挪到地板上,走过去吻他。
第一堂滑雪课前夕,乔瓦尼整夜都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脑子里各种画面蜂拥而至,想着第二天可能会因为笨拙的动作而被一群小孩儿嘲笑,又或许当他摔跤了半天起不来的时候,孩子们会在一旁戏弄他。他无数次地告诫自己别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了,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可能是没睡好的缘故,他显得有些虚弱,加上整个人心事重重,一大早就起来了,比其他人都要早到滑雪场。
他穿着从岳父那里借来的滑雪套装,从停车场步行至滑雪赛道,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别扭。并不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穿的款式早已过时,也不是因为衣服不那么合身,而是因为这一路上人们看向他的眼神,似乎人人都知道这件衣服是借来的,这使得他感到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就好比一部以古罗马为背景的历史片里的群众演员,身上穿着古罗马时期的服装,腕上却戴着手表,对,他感觉自己就像是那些群众演员。
好在现实并没有他所想的那么糟糕。首先,他惊讶地发现滑雪世界里充满了初学者,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从未在脚底踩过滑雪板的成年人。其次,那些已经做过几小时练习的人与零基础的初学者分开了,而初学者们又按照年龄被划分为两组:一边是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其中就有巴托,陪他一起的还有满眼宠溺的西蒙娜),另一边是成年人,虽然大部分人都有对象,但基本上都是单独来这里的,大概大家都不愿意在自己的爱人面前丢脸。这种把同类分到一起的分组方式使一切变得更加简单。
乔瓦尼是在第一次跌倒的时候认识蒂娜的。那时他正在一个小斜坡上吃力地往上爬,教练只告诉他们滑雪板要保持水平,但没教会他们如何刹车,正当他一点一点地挪动时,仿佛有种神秘的力量推了他一把,他一下子便失去重心摔倒在地。幸好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嘲笑他,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脚下,努力保持平衡,避免像他那样摔倒。
蒂娜从教练队伍里走出来帮助他,教他怎么站起来,并陪伴在他左右,直到他掌握了滑雪的入门知识。大约一小时后,乔瓦尼终于能走上斜坡,不仅学会了刹车,并且在蒂娜的帮助下还能滑一小段路,从小斜坡的坡顶一直滑到扫雪机那里。
蒂娜戴着羊毛帽,紧身教练服下是傲人的曲线。就在乔瓦尼努力练习力求早点重新归队的这段时间里,巴托已经成了他那个滑雪赛道的冠军,用他教练的话来说,这是“真正的天赋异禀”。
第一堂课结束时,乔瓦尼发现初学者的人数已减少了许多,但他仍旧不能独自从坡顶滑下来。西蒙娜鼓励他试试,他说他还没有准备好,于是暂时归还了滑雪板和靴子等待上下一堂课。
他像避难似的逃到酒吧里,还要等很久才开始上第二堂课,为了打发时间,他决定喝点酒。外面的温度那么低,喝点烈酒应该也无妨,这么想着,他点了一杯格兰冠[1],没承想等酒上来的过程是个更为漫长的等待,真是个恶性循环。
大约一小时后,他看到一个金发女孩儿在向吧台靠近,脚上穿着双休闲靴,一身精致时尚的滑雪套装里面包裹着性感的身体。女孩儿走到吧台点了一杯咖啡,同他打了个招呼。乔瓦尼不敢相信自己竟能引起她的注意,带着略感意外的羞涩也向她问了声好。女孩儿有些尴尬地说:“你认不出我了吗?我是蒂娜。我们是刚刚在你的滑雪课上认识的。”
乔瓦尼道歉,说因为她把帽子摘下来了,所以一时没有认出来,打算请她喝杯东西以表歉意。
“谢谢,不过我已经点了咖啡了。”她说。
蒂娜小口啜饮着咖啡,和他聊起前段时间因为一直艳阳高照雪的质量特别差,滑雪道几乎都要融化了。然后,乔瓦尼问她是如何看待他这名滑雪初学者的。
“你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初学者,”她面带微笑地回答,“但等你上完一周的课程之后,你会发现情况有所好转。”
在那一瞬间,乔瓦尼脑海中同时冒出来两个问题。他先是问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大城市的人,为什么他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在八月来这个鬼地方度假?为什么要耗费精力和体力,去学习一项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缺乏平衡性的运动?第二个问题,抛开他的虚无主义情绪,想象力开始撩拨他的下体。他在想,在这一周的时间里,说不定能有机会去蒂娜家,在那覆盖满冰川的巨大屋顶之下做点什么。
“希望如此吧!你下周能继续做我的教练吗?”
蒂娜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钟。“恐怕不行,我已经有安排了,”她说,“有一对七岁的双胞胎需要我去辅导他们。”
乔瓦尼一定是喝醉了,才会试图去想象这对双胞胎的样子。“我不介意和他们一起。”
“我觉得不太妥,他们的水平可远远高于你。”
“你可真毒舌。”
“我这是客观。”她纠正说,“不过如果你还愿意的话,倒是可以请我喝点什么。”
他们彼此纠缠的唇舌间萦绕着格兰冠的味道,纵使舌头已经被酒精麻痹了,乔瓦尼仍能从鼻子里感受到她的香味。他们躲在山脊的一个小角落里,离厕所大概十米远,吻了大概有两三次,然后乔瓦尼的手机就响了。西蒙娜在电话里先是问他进展如何,是否感到无聊,接着便开始不停地讲巴托的进步。他边讲着电话边看着蒂娜,意识到自己身担丈夫和父亲双重角色,一时对他的家庭心生反感,包括他自己。中产阶层,是人们对他社会地位的肯定,这虽然赋予他形而上学的重量,但也为他去滑雪山庄度假提供了经济保障。艳遇,仿佛成了这为期一周的假期的赠品。挂掉电话,他看见蒂娜面带羞愧,应该是猜到了他是有妇之夫并决定逃跑。“我得走了。”她说。乔瓦尼用一只胳膊搂住她:“明天我们会见面吗?”
“也许吧。”
“我想再见到你。”
“也许明天吧。”
他们没有再见过面。第二天,他尝试着独自滑一小段,滑到扫雪机那里。他隔得老远都能看见蒂娜与那对七岁的双胞胎一起,他们的确滑得比他好得多。
几个月后的一天,乔瓦尼对西蒙娜坦白了在那个小角落里的吻。
那天西蒙娜回家比平时晚,乔瓦尼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男性是多么地没有效率。整个下午,一支青霉素注射器就把他忙得团团转,巴托怎么也不肯配合他,坚决不让他打针,别无他法,他只能等妻子回来。等西蒙娜终于到家的时候,两人不可避免地吵了一架。他埋怨她整天忙于照顾诊疗中心里的那些孩子,对自己的孩子却不管不顾。她矢口否认,还骂他是浑蛋。于是,被激怒的他决定略施惩罚,主动跟她摊牌那次半出轨的事情。虽说一个吻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但至少会让她心里难受,这样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和谁?”西蒙娜问,声调突然降了下来,“那个金发女孩儿吗?”
“对,就是她。”
“那个婊子!巴托滑雪的时候交了一对双胞胎朋友,那几天她就一直在和双胞胎的爸爸眉来眼去,暗送秋波。”
乔瓦尼惊讶于妻子的好记性:“好吧,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晚些时候,西蒙娜决定原谅他。“毕竟只是一个吻,”她说,“不过你仍然是一个浑蛋。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回家晚了是因为我去看了趟医生。我怀孕了。”
虽然与巴托小时候相比,迭戈不会惹那么多麻烦,但是家里的处境还是再次变得艰难起来。乔瓦尼正处于他职业生涯的特殊时期,忙得抽不开身,西蒙娜也才刚休完产假,重返工作岗位。他们犹豫着是否该请个保姆,所以在罗宾到来之前的两个月里,家里的氛围异常沉重。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的乔瓦尼早已精疲力竭,他不再有幽默感。当西蒙娜滔滔不绝地和他谈论着工作、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宜时,他实在听不进去。不过就像所有疲惫的丈夫一样,他自动地掌握了一项技能,就是在妻子喋喋不休的时候,能不动脑子地时不时搭上几句话。其实,西蒙娜经常能感觉出她的丈夫不在状态,有时候她会安慰他,让他不要有太大压力,鼓励他振作起来,有时她会生他的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假装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是瓦莱里奥的出现。
迭戈那会儿刚满六个月,她才重返工作岗位不久,对诊疗中心新来的那位心理学家还不是很熟悉,只知道所有人都对他赞不绝口。各种八卦中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传闻他特别讨孩子们喜欢,尤其是小女孩们。
他的外貌寥寥几句便可概括,凌乱的头发,短袖衬衫,异常自信的表情,深色的皮肤呈现出好看又不过度的古铜色。
第一次看到瓦莱里奥时,西蒙娜变得像个小女孩儿一样,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但又不想被他看穿,然而这一切都逃不过瓦莱里奥的眼睛。他轻易就能看穿西蒙娜:她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很讨厌政治家们,几乎是文学与电影的绝缘体,有时候她会主动帮忙去丢垃圾,理由则是单纯的不愿意待在家里。
还记得头几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曾疑惑不解,同事之间怎么可能发展成恋爱关系呢?这就好像在问,激情会在何时何地如弹簧般突然一下弹起来,打破冷漠、无形的同事关系呢?她从未对自己产生过怀疑,那些去她办公室看诊的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都是些状况不容乐观的患者。她的同事也大多是年长之辈,忙起来甚至都不怎么能打上照面。在诊疗中心,每天还有一大堆小病人需要照顾,每天都会来许多新的小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问题,有暴力倾向的、被遗弃的、受他人排斥的……她实在想不出,怎么可能从繁忙的工作中脱离出来,而只想着年少时关于性的幻想呢?
直到她遇到瓦莱里奥。
关于性的幻想,在身体真实的快感下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并没有做得很激烈,也不是非常注重前戏或姿势上的美学。在三十岁的年纪与同事发生性关系,西蒙娜感到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她将自己的经验、力气和冷静全都投入了进去,沉浸在拥抱和抚摸的小宇宙里,另一边的瓦莱里奥挥洒着汗水,也投入了他的经验、力气、冷静。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西蒙娜躺在他身边问。
“我该说些什么?”瓦莱里奥反问。
两人相对无言。
瓦莱里奥起身整理了下自己的头发,宛如多年前那个规规矩矩的少年。西蒙娜在一旁看着他,想到了那些总是用内疚、污秽和错误这些字眼来讲述他们婚外情的病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与瓦莱里奥上床其实相当于上了一门进修课程,毕竟只有更了解病情,才能对症下药。
当他离开房间时,她朝他慵懒地笑了笑,有点迷恋又有点邪恶。
注释:
[1]格兰冠,一种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