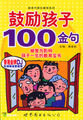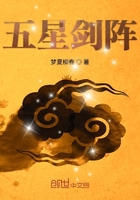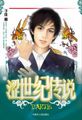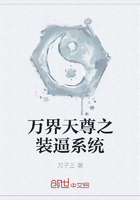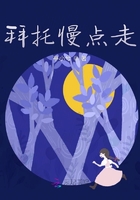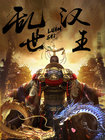而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课程或是这个活动或许并不适合自己孩子当下的成长需要,因为,它不是系统地为一个孩子的系统地发展而专门设置的课程或活动。它就像我们做的家常菜上的点缀一样,并不是主体菜必须要的,但它会影响主体菜的味道和效果。也许有人会认为,每周带着孩子到社会上的加强班或者各种特色班里去上几节课,就像孩子每周吃几次零食一样的道理,调节一下周一到周五的幼儿园生活。如果我们带孩子去的地方上的课,是真实能做到为孩子的整体发展做准备的,是适合当下孩子的年龄和他个体状态需要的,并且能以长期观察和研究这个孩子在课程中的反应为目标的,并且对孩子的困难能准确捕捉到并给予有效的帮助,也许我们可以带孩子去试一试。
所以,我们帮助孩子成长的人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对孩子有用,什么对孩子没用。我们不能把孩子的成长寄托在我们的感觉上,感觉到的东西只是我们身体中十几种感觉带给我们的礼物之一,并不是帮助我们做出真正思考工作的载体。要是我们对此进行过思考,我们会发现,虽然这种看似有用的东西会给我们一些暂时的满足和惊喜,但它一定会在日后影响孩子的整体状态。孩子的状态会真实地呈现出来给我们这些仆人看到,在一个了解和懂得孩子需要的教育机构里给孩子建构起来的良好状态是怎么一点一点地被家常菜上的点缀削弱掉的。
这是针对我们这些帮助孩子们的仆人的大的意识上的思考的建议。孩子的需要当然是我们真正要考虑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到孩子哪些课程可以上,哪些课程不该上,哪些课程我觉得对孩子好,我就是要让孩子上,哪些课程我觉得对孩子没有用我就不让他上,这是比较表面的一种思考。当我们在思考,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建立在一个一个不是同一系统下拼凑出来的课程上呢,还是建立在一个了解孩子本质发展的系统之下提供给孩子一个一个的课程呢,当然,其他层面暂且不说,这仅限于课程层面的比较,思考之后,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判断。
因为,作为仆人,可以是孩子的老师,可以是孩子的父母亲人。但是,不管我们大人扮演的是孩子的什么角色,我们对孩子所做的事情,孩子会用他的方式呈现出来,回赠给我们。如果我们随意地凭着感觉在对待孩子的成长,那么,孩子回赠给我们的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状态。
我们大人们之间,也会互相回赠礼物,就是为了自己和同事或者朋友成为对孩子有用的仆人,我们会给予对方关于帮助孩子、养育孩子成长的意见。
当有人给予我们意见时,我们不用立刻收下,也不用很快拒绝。我们可以想一想,这种想是让我们客观地思考这个意见,之后,我们再次做出决定。不管这个决定别人认为怎么样,是赞同还是反对,它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这个决定是经历了一个精神化的过程,这种思考过了的决定会是一种道德的做法,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这种做法是我们这些孩子的仆人们要时刻记住的。
仆人蜕变的过程
来“小农庄”工作的老师,不都是专门学习幼儿教育专业的人,大多数都是艺术、心理学、文学、金融等很多不是专门学习教育专业的人,却来到了这里当幼儿园老师。
有时候我会思考一个问题,我来到“小农庄”是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因为有人和我分享了一种现象,他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段旅程,你来到了一个地方,在这里学习、工作,为什么你就会来到这里?为什么是你来了而不是别人?
我想我曾经花了八年的时间学习美术教育,一心想当画家,但是没当成。现在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必须要时刻观察和感受他们。如果我没有之前的艺术层面的熏染,也许我就是通过了严格的教育培训也不会很到位地观察到孩子们的需要,也感受不到他们的细微变化。也许我学习美术,就是为了帮助我将来做幼儿园老师做的准备。
如果说我能成为一个对孩子有用的仆人,我很愿意做这个仆人,相信这也是我们这些帮助孩子成长的老师们共同的一种愿望。
当老师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为老师自己的成长而积累能量。与其说每天是老师在帮助孩子们渐渐地长大,还不如说是因为孩子的存在让老师有了成长的机会。老师在帮助孩子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是孩子给了老师解决问题的机会,让老师的能力得到了提升。所以,作为幼儿园老师,我们并不是在照顾别人,而是在修炼自己。
于是,没有经历过几年磨炼的老师,不会在一开始和孩子合作时,就做到自然地游刃有余地懂得孩子。因为,有一种力量使得人不能达到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和孩子合作,这种力量就是人的内心考虑的是自己不是他人。
如果我们内心装的全是我们自己,考虑的也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给别人呈现的状态是怎样的,不管这件事情对别人是不是有益的。那么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要展现自己想要展现的,而不管别人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不是真正做教育的人该做的事情。做教育不是做生意或者做交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做一个事情,那是爱自己的一种做法,并不是爱他人的做法。作为面对孩子的人,最忌讳的也是只爱自己不爱他人。
但人的本质中有善良的一面,我们可以通过对人的很多帮助,让人善的一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将人性中产生消极作用的东西降低到最低。
针对一个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人,他的成长经历而言,我有这样的一种体会。
当一个人对幼儿教育还没有多少认识,对幼儿教育还没有更深的理解的时候,要是和孩子在一起工作,或者帮助两个孩子解决一件冲突的事情,或者和孩子有一些交流等等时,都会有比较多的顾虑。会想我做的事情、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帮助到孩子,如果是没有帮助孩子的话,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做错了,对孩子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为了不让他人说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为了保全自己不要被他人指责而本能地思考自己怎么做事、怎么说话,才能不出错。这是因为,这个人内心还不够强大、不够自信,很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这种担心总是会让我们想象,怎么做和怎么说才是既不会让人说自己错了,也不会伤害到孩子;甚至为了更安全一些,也许都不去想这件事情,只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处在一种不高级的灰色系中。这种色系的颜色既不偏冷也不偏暖,既不属于偏冷的灰色,也不属于偏暖的灰色,不痛不痒,让人看不出自己明确的立场和观点,让人能看到的只是一塌糊涂的状态。
这也是很多刚来到“小农庄”工作的人容易出现的状态,因为在这里工作,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即使是经历了多次培训,在真正做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有不到位的情况。由于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人,生怕自己做的事情对他人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就格外地谨慎,越是谨慎越会不自然,越是不自然就越是表达不出自己真实的状态,也就不会被帮助自己的人发现自己的不足和需要帮助的地方在哪里,至少是对别人帮助自己有局限。
一个老师在成长中会经历到这样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蜕皮的阶段,就是在我们工作中会让我们发现由于自己的某些方面没有提升起来,而影响整个工作的质量。其实,不是有人有意识地不愿意把自己的不足呈现出来,而是,往往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什么。而做这种对人本质理解之后给予最大化帮助的教育工作,对教育者本人的要求更是很高,就逼得自己必须要挖掘不足,来完善那个不足,才能继续将教育做下去。
我曾经遇到一个同事,她很有才能,反应相当的快,对孩子也很热情,在工作中有很多新鲜的点子冒出来。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新鲜感一定会征服他们的好动,会让他们很快地安静下来听这位老师描述她的想法。渐渐地,这位老师也通过孩子们给予她的反馈认知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于是,在往后的工作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处于一种成功的幸福感中,这种幸福感是无意识的,她自己不知道。
接下来的事情,就会有问题出来。幼儿园的工作是需要很多人周密地合作才能完成的,对于我们做的这个教育来说,除了能合作,还要发挥大家的意志自然地合作。如果有一个人总是处在自己的世界中,只是做自己有把握的那一部分工作,没有听到和感受到整体的工作需要我们怎么配合的话,就会在某个环节中让与自己合作的同事很累、很没有头绪,孩子也会出现混乱的状况。
一个老师在成长的过程中,处在这个阶段时,就像孩子成长的头三年一样,他会做很多的事情,并且很专注地做自己当下的事情,却很少关注到和感受到他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于是,此时这个阶段的老师需要成熟的老师引领他们,让他们明确地知道做什么、如何做,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会将什么做得更好,这样对他们的成长会有帮助,让这个阶段的老师能建立起自信和探索教育的热情。
当一个老师在幼儿教育工作中,已经经历了好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以后,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和感受。这个时候,就像孩子成长阶段中的三岁到五岁这个阶段一样,开始注重感受身边的环境以及身边的人。也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充分地体现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并且很重视其他老师对孩子的感受,以及希望所有人都能将这种感受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也会比较深入地将感受和孩子的需要联系在一起,还会很有能力把握所带班级孩子的整体状态,对孩子的困难也能比较自然有效地知道怎么解决。
这个时候,这个老师对自己已经有足够的信心了,也会和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也有足够的勇气说出自己对教育理解之后的立场。对他人的意见也会比较客观地来看,不会因别人说自己的工作有哪些不足而担心不已,也不会很在乎别人是怎么说自己做得多么“糟糕”,并且会有力量将不足的地方让它有变化。
这个时候,对于一个老师的成长来说,是走到了一个初步成熟的阶段,也就是,他已经过了只做事情的阶段,来到了带有感受性地做事情的阶段。我们也会看到,这个阶段的老师,不会只为了做事情而做事情,会更关注在教育体验和教育观点上的认同感。于是体现在教师研讨会和教师主班会上,他们会有很多困惑和疑问,发言最积极的就是这个阶段的老师。
此时,这个阶段的老师,就像孩子一样,不再一个人做事情,会寻找玩伴,一起合作,愿意与人深入地交流,会创造出很多可能,并且验证它。此时对权威也会有很多的挑战,因为感受多了,体验多了,质疑也会多,他们不再说“某某老师说了,我们该怎么做”,他们会说“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我有一回就是那么做的,结果很好”。
此时,这样的阶段,延伸到一个幼儿园的成长和一个家长的成长也是一样的,在“小农庄”成长到第五年时,家长们对“小农庄”有很严重的质疑。因为,他们经历了几年的家长培训以后,像孩子一样成长了,他们和孩子一样不再停留在前三年的做事情上,不再感觉到大家伙儿一起劳动就是幸福的事情,而在三年前他们很享受那种幸福感。于是,他们对教育的体验和理解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中就会有对幼儿园做法上的质疑,这种质疑的来源不排除自己的感觉在内的一种判断。不过,我们要是靠感觉来思考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比较危险的做法,所以,不管老师还是幼儿园还是家长,在这个阶段中,还要有比较多的思考,不能只是有感受。
当然,不是说,人到一定的时候,都会跳出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树立自己的观点。而是说,有感受有观点是教育者在教育这个领域里有变化、有成长迹象的一种反馈。渐渐的,会从这个阶段慢慢地进入到一种对教育的思考阶段,而这个思考不仅仅是一种很简单的思考,不只是想想今天我上什么主课,怎么准备材料,哪个孩子比较调皮我要怎么来面对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如何将我们要做的事情更深入、持久地做下去。
对一个老师的成长而言,当经历了他自己认为的磨砺、指责、训斥、反驳意见甚至是很深的伤害以后,他应该是会有变化的。毕竟,从一个新老师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老师时一定经历了很多。
到了第三个阶段,除了拥有前两个阶段带给自己的礼物以外,还有另一个礼物,就是我们会进入到一种真正思考的阶段,这种思考是有意识地想要有积极变化的思考,与避免犯错而找到掩盖办法的无意识的本能的思考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