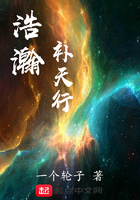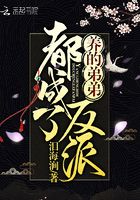到现在我依然感谢那位爸爸是那么快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足够的力量接受他人的意见,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孩子不能在室内做室外的活动一样。当一个孩子拿着一个纸飞机在飞时,我们会觉得孩子好可爱,特别是看到孩子因纸飞机飞起来而哈哈大笑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孩子做了世界上最美的游戏。而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是在室内跑来跑去地玩纸飞机的游戏所发出的噪音和丢弃的废纸时,我们就不这么认为了,就像我们不认为孩子在很高级的酒店里疯狂地追来逐去也是好事情一样。
在这里我想说的不只是纸飞机在哪里飞的问题,而是,成人要清楚孩子的活动不是随随便便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许我们所受“给予孩子自由”的影响太深,实际上我们又没有真正地掌握“给予孩子自由”的宗旨到底指的是什么,于是在和孩子们生活的时候,对于孩子的行为就不会管理,反而会让孩子做很多“自由的事情”。
我的班里来了一位新入园的孩子,妈妈陪园,在上午孩子们自由玩耍的时间里,新来的孩子在班里待了一段时间,就想要出去。因为他第一天入园,老师在孩子刚入园的时间不会对孩子有很多要求,所以也就同意妈妈带孩子到教室的门口外。但是,过了一会儿,我的助理老师告诉我,孩子的妈妈带孩子到我们楼上的班级里去了,因为孩子想去那里看看。
我让助理老师请孩子的妈妈带着孩子立刻回到我们自己的班级里。在孩子入园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状态来做一些调整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包括一个入园的孩子到其他班级里去逛逛。孩子的妈妈说:“我认为,孩子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环境中整体都有什么,再具体到自己的班里有什么。原来,大人和孩子了解环境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我对孩子的妈妈说:“孩子在自己的班里会比较安全,对他适应新环境有好处。孩子不像大人那样,会看到很多信息,他们也许只会关注到很小的东西。孩子随处走只能让他感到不安,在自己的班级中他会知道自己的老师和小朋友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便于他了解自己的班级。孩子要是想了解其他班级的情况,他们有机会到户外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孩子会知道很多关于其他班级的情况。”
孩子的妈妈很赞同我所说的,从那天以后,再也没有带孩子到处走动,后来孩子适应得很顺利。
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不想把事情做得不理想,特别是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的时候,更是想将和孩子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完美。但是,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人在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时,都会被一种东西所控制。也许是成人在养育孩子方面的一种不自信所致,大家会很在意他人对自己养育孩子时的做法怎么看,别人对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满意。
作为老师,我们也有这样的心理,当家长对孩子的状态提出疑问或者表露出担忧,或者园里领导对自己的教学提出要求,老师们就会思考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其实我们会把他人想给予我们建议的初衷误认为是在找自己的毛病,会首先想到的是对方不是在谈孩子的问题,而是在说自己工作的问题,这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水平不自信所产生的猜想。
同样的,当我的导师告诉我说:“当你在和某个家长谈到他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困难时,家长不会很快地接受你所提供的解决此困难的建议,是因为家长很担心你是在说他没有做好孩子的妈妈或者爸爸,才使孩子有这样的困难。”
之后,我就很能理解我在和一些家长朋友说起孩子的一些状态时,家长真的会很警惕。而当他们发现我只是在说一类现象,而不是在说他们自己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时,他们会很开放地接受我的观点。
这也许是我们这些大人的这种状态是因自己在受教育的时候被教育的结果。也许那个时候,我们被很严厉地训斥过,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自己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被他人认可和满意,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会担心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真的在帮助孩子。这么多对自己的否定让我们面对孩子的教育时,只要别人给我们提出一点点善意的建议,就有可能会兴师动众地紧张和误解别人。
我们成人在成长中有过被伤害的经历,再次面对孩子的成长时,对自己帮助孩子时所做的事情总会有所顾虑和不自信。不过,我认为,作为帮助孩子的成人,不管我们是孩子的什么人,要清楚孩子的活动范围,我们自己也要清楚一个孩子所做的正常活动最终的底线在哪里。之后,当孩子们在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做出怎样的反应是对孩子有益的。
有效行为的有效性
曾经在教师培训会和教师主班会议上,我们不止一次地探讨过一个议题,“老师在帮助孩子时的有效行为有多少?在工作中,这种有效性行为足够帮助到孩子了,还是远远不够,以及老师在观察和发现孩子的需要时,是否可以准确地觉察到并给予有效的帮助?”
这个议题,其实反映了新老师的培养问题,要是,每一个人的工作质量都很高,那么就不存在哪些行为是无效的,哪些行为是有效的。
我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也深深地体会到:帮助一个从来没和孩子打过交道的人,成为一个爱孩子和敬畏孩子,从根本上对儿童世界有所觉知,并且能遵循着某一种或者多种能够透析人类本质的理论,对儿童的成长以忠诚的态度及智慧而有力量地帮助孩子度过每一天的一个人,实在是很难很难。
其实,我还想用很多形容词来描述我对一个成熟老师的界定,当然,每一个人又都是很有个性的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没有更多的词语能准确地形容一个将教育理论和具体操作结合得很娴熟的老师。因为,这种娴熟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熟练,而是在一个成熟的老师身上几乎看不到他做的事情中,哪个行为是在体现哪个理论,所有的东西都似乎融合在这个老师的内在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老师会散发出无穷的力量给予他的班级,以及这个班级中所有的人,而所有的人又会将他们收到的力量以另外一种状态的力量反馈给这个老师。于是,这个班级就会以一种善良、友好的合作关系存在着。这种关系对于孩子而言极其重要。孩子们的世界中,他们崇尚所有和善有关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把握得很好,它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健康的营养,由此,孩子们可以健康地生活着。
当一个班级中来了新的老师以后,孩子们都会因此而做出一些不同的反应。有的孩子会一直看着新老师,有的孩子会躲得远远的,有的孩子会走到新老师跟前好奇地问一些问题,也许还会和新老师说一些他自己才清楚的事情。同时,每个新老师见到这些反映也都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状态。
有一天,我的班级中来了一个实习的新老师,她给人很无助的感觉,整个身体比较紧绷。虽然她已经参加过了我们的内训,但是,到了班里面,见到孩子时,我感觉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助理老师给她一些毛线让她绕成小线团,这样手里有点事情做,总比干巴巴地坐着要舒服一些。就在这位新老师稍稍镇定一点的时候,孩子们发现了她,有一个孩子走到她跟前看着她,那个孩子的眼睛盯着她的手看看,又看看她的脸,之后,孩子好奇地问:“你是谁啊?”
新老师比较紧张地回答:“我是新来的老师。”
孩子又好奇地问:“你是什么老师啊?”
新老师鼓足勇气,回答:“我是助理老师。”
孩子更好奇地又问:“你为什么是助理老师?”
新老师不知所措地回答:“我是新来的。”
问到这时,那个孩子的眼睛瞪得很大地看这个新老师,接着,那个孩子没再问,转身跑开了。
问问题的孩子是个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们这样的年龄的孩子,对人和物都比较关注,他们的生活中来了自己不认识的人,他们就很想探索和知道一些跟这个人有关的信息。我理解孩子们的问题是想了解这个新老师叫什么名字,是想了解新老师这个人是谁。谁知得到的回答是“我是新来的老师”,孩子听了会想,你怎么就是“新来的老师”?因为他们不认为你会是“新来的老师”,实际上他们不认为一个人的名字会叫“新来的老师”。于是,他们又换了问法,“你是什么老师?”例如,我叫马丽娟,我回答:“我是马丽娟老师。”这也许是孩子需要的答案,而孩子们听到的答案是“我是助理老师”,于是,孩子们就太好奇了,会想,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助理老师”呢?于是,孩子才问:“你为什么是助理老师?”孩子不明白,你明明是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助理老师。所以,孩子是想知道的是你这个人是谁,并不是你的职位或者头衔是什么。最后,当孩子们听到“我是新来的”之后,他们太无奈了,只好离开了。
这个新老师在我的班里还没有实习结束,就离开了“小农庄”。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班里来了一位德国的背包族,是来体验学习的。他个子很高,头发微黄。孩子们见到他时,很兴奋,在他的身边转来转去地看他,“背包族”会蹲下来,他知道他自己的个子实在是太高了,孩子们都仰望着他。有的孩子很害怕“背包族”的样子,不敢靠近他,只是在远远的地方看着他。我的助理老师请“背包族”坐下来帮助她撕羊毛,这样大家都能安静一些,因为,“背包族”的到来让孩子们很躁动,不过总会有孩子很想知道“背包族”怎么就会来到我们的班里。
有一个孩子警觉而又平和地问:“你是谁啊?”
“背包族”友好地笑了笑,说:“我的中文名字叫凯。”
另一个孩子接着又微笑地问:“你的眼睛怎么是蓝颜色的?”
凯平静地说:“因为,我的爸爸是德国人。”
孩子们又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会说汉语?”
凯自豪地耸了耸肩,说:“我的妈妈是中国人。”
孩子们听罢,哈哈哈地相视而笑说:“他叫凯,他的爸爸是德国人!他的妈妈是中国人!?”虽然还有点不敢相信,但是孩子们知道这是真的,只不过他们很少见到爸爸是德国人,妈妈是中国人的人罢了。
于是,孩子们对凯感兴趣极了,又问:“你有爷爷奶奶吗?”
凯稍稍停顿了一下,他说:“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了。”孩子们听了以后,没有再笑,他们看着凯,平静地说:“那你有姥姥姥爷吗?”
凯又笑了笑说:“什么?”
我想凯是不明白姥姥姥爷是指谁,就说:“你的外婆和外公。”凯立刻明白了,他打起精神来说:“哦,好的,我的外婆在北京,外公不在了。”
凯很快又说:“在北京我外婆的家,她也叫我凯。”其实,叫凯时,就像我们叫孩子的小名一样,凯的外婆在家里也叫凯的小名,这也许是中国人的习惯。孩子们和凯交流了很多,他们都挤到凯跟前,和他一起撕羊毛,给做好的布娃娃当填充物。他们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凯还教孩子们羊毛的英文怎么念,于是孩子们就“wool”来“wool ”去,念个不停,很开心。
后来,因为凯的个子太高,坐小孩子的椅凳很难受,孩子们给凯找了一个高一点的凳子,当做礼物送给他,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凯,礼物凳”。再后来,孩子们特别喜欢我们班的背包族凯,凯也在我们班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我就在想,两个新来的人和孩子们的交流,差别是那么的大,给孩子的影响是那么的不一样。我们在培养新老师时,总会看到当一个人内在的成长够了的时候,他才能做好外在的事情。而国外来的新老师,他们和小孩子交往时不需要再建构内在的部分,一上手就会做得很到位,因为他们内在已经拥有感受和体验他人感受的东西。
有人开玩笑说:“外国人是原装的,而我们不是原装的,外国的成人和孩子在他们祖辈那里就获得了自然的生活化的教育。而我们要靠后天发现我们哪里没有被教育好,而进行修正和再加工,才能相对地做一个适合现代教育理念的老师。”
这的确是问题所在,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的教育环境之下对人的影响,我们只能帮助来到这里的人,成为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的人。
把握“帮助”的度
老师们在交流孩子的状态时,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困惑,那就是到底怎么管孩子,要不要管,要管的话,怎么管?
我们也会看到,有些老师在帮助孩子时,很难把握和孩子在一起的度,大家在面对孩子的一些状态时,就比较困惑。就像,有的孩子他表现出非常强势、看起来无法无天的样子;有的孩子他表现出很需要人关注的样子,甚至是一种哭哭啼啼很需要人来抱抱的情形;有的孩子他会表现出像刺猬一样的状态,老师用什么方式都很难和他接近,也就是说很难让他和大家合作在一起……
当老师看到孩子这样的状态时,总想着怎么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看起来快乐一些、平和一些、友好一些、自然一些等等,总之是让孩子的状态看起来是顺畅的,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