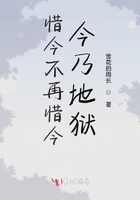次日中午,石克俭领着外孙贵生,走进沈家客房里,心正和好古招呼他们坐下吸烟,克俭先到厨房里把帼贞和惠珠叫到客房里。贵生对她婆媳二人说,昨天捻军到了终兴集,开运舅和大力哥在街上碰见俺娘了,他们托俺娘快给家里捎口信,说他爷俩一切都好,不要为他们担心,请张姥爷和姥姥搬到这里来住,土地不能种,就租出去,只要姥爷、姥姥在这里,有两个舅舅给撑腰,他们在外头就放心了。开运舅还说,张亲家离这里路远,来一趟不容易,这里有张姥爷和舅舅照料就可以了,叫张亲家举家尽可放心。大力哥说,叫舅妈和嫂子一百个放心,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他不用大刀砍,一根旗杆转一圈就能打倒一大片,清兵想靠近他,墙上挂帘子——没门,舅舅有他保护着,万无一失,他要跟着捻军走南闯北,逛一逛,溜达溜达,见见世面,学些治国安邦的本事,再回来。
张姥爷一家感动得潸然泪下,帼贞婆媳俩喜极而泣,他们说,他爷俩身在捻营,心在家,心事重得很呢。
帼贞说,我儿子只知道玩,拿打仗拼命当儿戏,真是不知死活。
惠珠高兴地对好古说:“爹,你女婿如果没真本事,敢说这样开心的话吗?这下你可相信了吧。”
张好古,放心地笑了。
贵生送来了希望和力量,帼贞从院子里刨出一坛老陈酒,往客桌上一放,揭开盖子,满屋飘香。娘俩将凉菜摆了一大桌子,让他们尽情地喝,她和惠珠将姥姥搀到另一张桌上坐下,三人随量喝。
一坛酒被他们喝干了,也尽兴了,婆媳俩将热馍热菜端上来。大家酒足饭饱,把桌子擦净,倒上茶,开始商量租地的事情。
克俭有四个儿子,儿子又生儿子,人口越来越多,总共才有四五亩薄田,日子穷困,是明摆着的事实。他租了寨主二十几亩地,每亩租粮两茬三百斤,丰年交过租粮,还能剩下一些。灾年交了租粮,就没有剩余了,等于白干了一年。有时减产严重了,连租粮也交不够,只好推到明年。两年的地租一次还清,更是无能为力。驴打滚的利息,越滚越多,逼得石家年年挨饿,日子比黄连还苦。他五十出头,头发胡子,都愁白了,一脸刀刻的老皱纹,一对无神的眼睛,诉说着他的辛酸和悲哀。他本来是高个子,现在成了弯腰驼背的矮个老头了,看上去足有七八十岁。
张好古告诉石克俭,亲家母和张大叔昨天商量好了,张大叔搬到这里来住,寨北的十八亩地,由大叔爷仨负责耕种,其余的土地都交给你种。考虑到你家人口多,生活艰难,每亩收你麦子六十斤,秋粮五十斤。灾年减租或免租,根据灾情商定。你如果同意,就立个契约,我和张大叔作中间人。
石克俭一听,大吃一惊,顿足道,昨天夜里,我一家人就商量好了,开运爷俩不在家,帼贞和惠珠婆媳俩年轻,不能抛头露面地去种地,耕种收打的事,我爷几个全包了,收多收少我们一粒不留,全给她们送到粮食囤里。恩人有难,我们若乘人之危,占人便宜,就猪狗不如了。
帼贞说,姑父一家人的心意我领了,我们把土地交给你耕种,目的就是照顾你们。要说不收地租,你老人家绝对不会接受,所以少收些。你老如果嫌多,还可以再减少,一年种春秋两茬,除去地租,若种好了,一亩地的收成还剩三四百斤左右。
石克俭说,寨南那十几亩洼地,种一茬麦子,一亩地收四五百斤没问题。割麦种豆,豆子一亩能收二百多斤。您寨西边那十几亩地,半沙半淤,土质肥沃,旱涝保收。我说侄媳妇,你光想着照顾我,我这个穷坑是填不满的,也于心不忍呀!不行,地租还得往上加。
加多少呢?大家都不好意思开口,还是帼贞说了算。她同意各加五斤,每亩收麦六十五斤,收秋五十五斤。
石克俭感动得潸然泪下,他说,只有帼贞一家人有这种菩萨心肠。老寨主脱胎换骨十次,也不会对穷人发一丁点善心的。他的沙碱地,不禁旱,不禁涝,产量上不去,他一亩收二三百斤地租,还亏得要命。从开运的父亲那时算起,到现在,我们到底吃了你家多少粮,穿了你家多少衣服,盖了你家多少床棉被,没法计算了。前几年,我病得骨瘦如柴,没钱治病,若不是开运花钱请先生,我早就上阎王殿上报到去了。陈国江一家四口,全靠你们救济。后来国江被老寨主逼死了,老婆领着一对儿女逃走了,至今没有消息。石匠老婆生孩子,寒冬腊月,一家人受冻挨饿。开运两口送吃的,送穿的,周济他们。老寨主却骂她玷污了他的宅基地,破了他家的风水,立逼着他们滚出去。一家人上门跟他磕头赔礼,求他高抬贵手,他仍然不依不饶。后来群众看不上了,纷纷找他说理,在群众的压力下,他才松手了。寨里的穷爷们,都非常感激您夫妇俩,大家一心向着你们。对寨主就不同了,都恨死他了,巴着他家失火,烧得寸草不剩,巴着他全家死绝,人芽也甭留。这一次清军进了寨,成百的清兵涌进寨主的大院里,在他家的阁楼上找着了他的两个儿媳妇。
石克俭恨透了老寨主,这一件轮奸案,是王妈传出来的,传得满寨沸沸扬扬,石克俭又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了哭笑不得,都骂清兵是衣冠禽兽。
张好古写了租地契约,帼贞、克俭、心正和好古都在上面签字画押,两家各执一份,租地的事情就办妥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