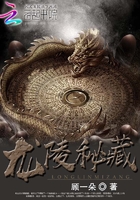“小伙子,我听你这口音却也并非像是北峵国的人啊?”范老汉坐在床榻上,一边为那已经几近痴呆的妻子喂食菜羹,一边与游让闲聊着。他的猫躺在床脚旁呼呼大睡。
“我在很久以前便离开了北峵。这么多年以来,口音也自然淡了些。”游让面无表情,不过这老汉倒并未带给他什么不好的感觉。
“这么多年以来?”
“有什么问题吗?”
“嘿嘿,我看你这模样邋遢是邋遢点,但岁数应该并不大吧?你说起话的语气怎么也像个离乡背井半辈子的人呢……”
“半辈子……只怕……”
“好吧,别说这些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关心一下你的身份问题了,你要知道,现在的情况可不比以前了,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你的处境可是相当危险的,而且你说了你想回到棱洲去,现在……”
“现在怎么了?”
“这你都不知道?各处的边关已经开始高度戒备了,来的人来不了,走的人走不掉。即使是那些位高权重的王公大臣们现在想要离开剑铜国,即使他们是公事在身,也要有那皇帝老子亲自写下的批文,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更何况你呢?由我们冽羊县要到棱洲,只有风却谷南边那一条路可以走,期间还要坐船行水路六七日,但就算你真正到了风却谷,你便会看见满山边野的堡垒和旗帜,在那些东西下面,听说可藏着无数全副武装的戍边甲士,兵丁和军械扩充到了往年的三四倍,就算是一只乌鸦、一只麻雀也别想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飞过去。前些日,听闻风却谷附近居住的一老太,上山采药因为大雾迷了路,不慎闯到了边境禁地,那些士兵真是连询问都懒得询问,警告也都未警告,用弓箭直接将其射杀。那么一个老人,唉……”
“这我倒是不大清楚,局势已经到如此地步了么?”
“剑铜和北峵两国之间,肯定迟早都会打一场的,即使是那些没啥见识的村妇和孩子也心知肚明,为这天,皇帝和军队们已经默默在暗地里筹备很久了……”
“我想的话,无论我是不是北峵来的密探,我始终是你们敌对国的人,你现在肯帮我,不,即使是肯让我到你家中聊上这么几句,你都已经算是死罪了吧。”
“这,确实是如此,我们的国君已经将北峵视为了大敌,只要那些卫兵抓着你并且知道你是北峵的人,他才不会管你是不是什么情报探子呢。而我,只要和你接触了,我便会被以通敌罪论处,抄满门。”
“多谢,你能把这么大的风险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不过我确实并非为了国家间的恩怨或目的而辗转于此,我只是为了回到故乡,只是如此。”
“你真是北峵人?”
“北峵,棱洲,猇夺人。”
“说实话,嘿嘿,我看你这小兄弟倒挺面善,所以才能这么放下心来和你闲聊。”
“很少有人说我面善。”
“哈哈……没事……没事……”
“嗯……倘若我必须路过风却谷又要避开守卫的士兵,应当如何?”
“没有办法,现在的戒备如此之森严,如果你硬闯风却谷的话,十有八九都……”
“就真的没办法了吗?”
“唉,是啊……不……等等……那样……嗯……”
“怎么了?”
“离……离风却谷不远处倒有一座大山,那里应该没什么卫兵,而且若能翻越过去的话,理论上绕一段路便可直接去到棱洲。”
“什么山?”
“就是那座招寒山。虽然这个提议并不明智,但从那里走的话,可以避开那些边境卫兵,不过……”
“招寒山?”
“正是。无论怎样,你还是……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为好。不过……恕我直言……我并不觉得你能……唉……好自为之吧……”
“多谢。”
————
空旷的山脚下,只有几栋已经破烂不堪的废弃茅屋,已不知被荒废了多少年月。
沿着茅屋旁的泥路走走停停,经过数日舟车劳顿的游让终于千辛万苦地找到了上山的方向。
招寒山之高,只是光从山下抬头往上看,已然是无法望见山顶的大概,只得若隐若现的云雾环绕飘浮在山巅之旁;而若关注眼前,便能勉强得见一条被齐人额头高的草丛拦住的石径隐藏在几根相当隐蔽的长满了菌菇的断木之间,它弯弯曲曲,游蛇一般延伸至不知何地。从那条窄小的石径上生满的一片片青苔倒可看出,这条路确实应该很多年没有人来过了,甚至人们可能连路过此处都会尽量避免。若目光顺着盘山的路径一路缓缓朝着更远处观瞧,仿佛会被其深邃无边的幽深之处摄去心魄。那些陡峭的悬崖、时不时有落石坠下的峭壁极不友善地分布在通往山顶的必经之路上。然而可怕的是,到了半山腰时,就再也无法通过肉眼找到任何可以靠着行走达到的地方或者路径,山腰上只有数不尽的乱石,茂盛得过分的植物,以及一条宽度足以塞下三辆马车的大裂缝横在山腰与山脊的交界处,那便是最真实的无底深渊……一股莫名的阴寒之气,自始至终都弥散在这招寒山的四周,那不是简简单单的冷,而是令人即使拥着火炉也会瑟瑟发抖的寒,就如它的名字一般……
「那些零零碎碎的传闻,可能夸张了些,」游让想,「但现在看来,倒也不奇怪。」
这里一个人影都见不到,也没有任何动物的行迹,只有呼啸的山风会让人误以为这里似乎有野兽出没。游让还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那条一开始就险些让他摔倒的苔藓石路。
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都不会这么做。人们都知道,靠两只腿便想征服这招寒山,绝对是痴心妄想。
“喂,小子。”。
山林中忽然一个声音从山林中的某处传来,游让竟然辨别不出来是男是女,是老是幼。
“何人?”游让小声问道,而他的右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他准备着,随时都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拔出剑来进行厮杀。
“应该由我来问这个问题才对,”那个声音继续缓缓地说着,“毕竟,你这冒失的样子恐怕更像个外人些吧?”
话音渐落,一个身着青袍的长须老者忽然不知从何而降,游让知道,刚才说话的就是他,也只可能是他。老者落地后,单脚踩在了地面一块巨大的青石上,抖了抖身上的落叶,微笑着看向了面前的游让。他注视着这位黑衣青年,笑着笑着目光中倏地闪过一抹不易被看出的惊疑。
对面的游让也看得仔细,面前这位虽然五官样貌与常人相比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这位苍髯老者的身姿与气势,绝非是一个身处暮年的耄耋老人该有的样子……他让游让还算平静的心中竟然泛起一丝源于未知的恐惧。
“只身涉足招寒山,有意思。”青袍老者微微一跺脚,轰的一声,脚下的青石如遭受到了重击一般瞬间碎成了七八块。黑衣青年尚未反应过来,他又是一跃,跳到了游让的面前,“这里可很久没人来过了。”
游让一惊,将手中长剑举起:“人们都说,这里虽然人迹罕至,但居住有一位好养食人精怪的仙人,想必——”
“仙人?精怪?诶呀,全是些无稽之谈,”老者哈哈一笑,打断了游让的话,直视着他的双眼,“不过你……”
“我……我怎样?”游让警惕着后退,手中的长剑仍然保持在随时可以砍向对方的位置。
“你让我觉得……你这身血肉之躯……让人捉摸不透……你……你……不应该……”老人用怪怪的语气说着。
“不应该什么?”
“也罢,我并没兴趣胡乱猜测一个陌生人,你应该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快些离开就是了。”
“我必须登上这座山,还请行个方便。”
“行个方便?我?不,你硬要上山没人会拦你,但是你别真装糊涂,做些蠢事。”老者用手指抵住了游让的剑,撇着头打量着刻有繁杂雕纹的剑身,“但是你,对,你让人捉摸不透……你或许本该……我能看得出来……”
“我管不了您是哪位,也无谓您看出我什么来了,”老人再一次吞吐不言,令游让无奈,他一仰头叹气:“但我需要避开守境的士兵,而听人说,只有这招寒山一条路可以走。”
“谁给你说,招寒山是人走的路?你既然都知道有传言这里居住有仙人,却难道不曾听说过这里有多危险?”
“我知道。”
“这么多年以来,老夫还没见过谁能征服这座山,那些人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最后也无济于事。而你,孤身一人只是想凭借路这一个理由便想上山?未免有些可笑了。”
“或许没必要登上顶峰,我只是……”
“趁着没天黑,早点回去吧……有阳关大道你不走,非要只身犯险不成?”
“这是唯一的路。”
“我只是在劝你,没有威胁你。你要明白,非要送死的人,谁也拦不住,不过你……倒是真的很……但你不应该还……如果……”
青袍老者三番四次欲言又止,这让游让十分不满,但情绪却并没挂在脸上。他强撑出一个并不好看的笑:“但说无妨。”
“没什么,老夫只是觉得有趣——好吧,你要清楚的是,这座招寒山的险峻山势只是它最微不足道的众多危险之一,还有人说因为山顶太过寒冷才无人可至,也许也是一个原因,不过只是如此的话,也不会至于有那么多人连只是路过此处都提心吊胆,心有余悸。”
“食人的精怪。”
“你不害怕?”
“他们说那怪物是那位仙人豢养的,那么,我要害怕也该害怕您。”
“全是荒唐的故事!仙人并不存在,但怪物嘛,可怕得真切。”
“您只需要给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就行。”
“你就真的不害怕?小子,我能猜得到你也许曾经遭遇过许多可怕的事物,也许你将他们亲手解决掉了,也许你的手段比那些东西更加可怕,不过,不要得寸进尺,在有些时候,你应当畏惧。”
“拦路的究竟是什么?”
“阴昧龙。你可明了了?普通人未可理解的生物,对你来说应该不算太难以接受……毕竟你并不像是个囿于见闻的凡夫俗子……你……”
“不必在乎我是何人,烦请继续讲讲关于怪物的事。”
“倘若有十个人是在这招寒山上死去,也许其中有两三人是因为失足跌落山崖,而另外的七八人,则是遭遇了它,而死相绝对不会比第一种好。在早些年间,人们对招寒山的印象还没和恐惧沾边时,它残害了不少附近的百姓以及路过的旅人。”
“那您呢,仙人?我想你应该是能找到和那头怪物和平共处的方法吧?”
“不要取笑老夫。我在这座山上,独自一人不知度过了几多年岁,皆是为了寻找时机降伏那头恶龙。阴昧龙类乃天地最邪之物,与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某些会带来福运的形象可截然不同。有些说法是,它们于宙外而生,待其食饱天星后便会从天而降,潜伏于人世的山川河流之间作祟,想要消灭一条阴昧龙,其难度堪比登天。至于这些魔物的身世倒有待考究,不过想除掉它们确实绝非易事。老夫于此地正是为了对付它。”
老者忽然低下了头,不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