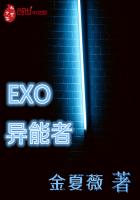“你怎么会在这儿?”
游让惊愕地看着乌和。他环顾四周,这里可离昨晚那个小山坡至少半里地。
“我……我不知道……”乏力的猎人慢慢抬起头来,他现在的样子看着十分难受。
乌和眼睛里满是血丝,他拍了拍身上的杂草和泥水,摇摇晃晃地试图站起身,又差点失足摔倒。
此时已经是晌午了。游让花了好些时间找遍了这个对他来说尚不大熟悉的村子,才找到这位瘫躺在一条小溪岸边的如只落汤鸡的乡村猎人。
“乌和,你知道昨晚发生什么了么?”
“我没印象……我只记得是像是听见了尖叫声与哭喊声……但又像只是幻觉……一定发生了不好的事……其它的我不知道……好似在做梦一般……那三个小伙子呢……”
“他们,他们全死了,绝对是那头怪物干的,不过并没把他们三个像之前那些人畜一样啃得只剩下骨头,看样子它的袭击太过仓促,但我没找到它。你呢,你是逃过来的?”
“我不知道……我像是睡着了,又像是没有睡着——什么?死了……他们全死了么……不……不……我头好痛……”
“是我太大意了……”游让咬牙切齿。他心不在焉地摆弄着长剑的剑鞘,“我一定会做些什么的,那三个孩子,我会替他们报仇——不过所幸,你还逃出来了,谢天谢地,我原以为你也……你是怎么躲过一劫的,到底又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一条河边?”
“我不知道……我说了我不知道——”乌和重复着,他着急了,语气也变得有些急促,但随即又缓和了过来,“我……不知道……”
“你也许真的该好好休息一下,你现在都语无伦次了。”
“不,不,不,这不是第一次了……”
“什么不是第一次?”
“没,没什么。”
“乌和,告诉我。”
“没什么。”
“告诉我!”
“唉,我……我的意思是,我不是第一次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这些地方。”
“什么这些地方?”
“就是这些意料之外的地方——村子外面、小溪边、树林里……”
“你能说得明白些吗?”
“也……也就是这几天的晚上的事……我经常发现自己第二天会在离家很远的地方醒来,就像今天这样,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躺在这儿,对昨天发生的事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却一点也记不起来……”
“你有梦游的习惯么?不过这也太夸张了。”
“没……没有。”
“看样子你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了……等等,你的嘴边怎么全是血……”
“也许是昨晚在某个地方摔了一跤……”
扶着乌和回家里休养后,游让独自一人去见过了村长。他细说着昨晚被野猪吸引去注意力的自己回来时是怎么发现同行的那三个年轻人的尸体的,他分析,也许是在自己与那头獠牙“怪物”周旋的时候,山坡上真正的怪物——有意也好,无意也好——趁机袭击了他们,自己赶到时已经太晚了。
老人靠在藤木椅上如坐针毡,他今天已经受了太多刺激了,并没多大心思听谁分享自己晚间遭遇,但游让除外。
“牲畜纵然不论,但已经六条人命了。”
“是。”
“我这愚钝的老东西实在是真的不知道要这么办才好了。大家都陷入了恐慌之中,个个提心吊胆,这是我这无能村长的责任。”
“是我……”
“不,不关你的事。我还是要说,你是一个和这村子毫不相干的外人,没必要为我们拼命。幸好你还无碍,否则我的内疚又得添上一份……”
说到这里,老人虽然面色无任何变化,心中已是悲不自胜。
下雨了。
淅淅沥沥的雨点洗刷着这座悲惨的村子,愁云密布在天空上,也笼罩在每个村民惶恐不安的心中。游让走在湿漉漉的小道上,正好这里就是昨天遭遇那头野猪的地方,那些燃烧过后的草灰还留存在这儿。他抬眼望向阴沉的天苦思冥想着,一滴雨水正好滴进了他的右眼里,带着酥麻的刺痛感从随即瞳孔散发开来……青年人将黑衣翻转盖过头顶,遮住了风雨,快步走回了猎人家——他想,此时的乌和应当清醒些了。
“你好些了么?”
“好多了。”
“那就好。”
“那三个孩子……”
“乌和,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肯定会为他做些什么的。但在那之前我想说说,关于你‘梦游’的事。”游让那还算俊俏的脸上只剩下严肃两个字,“我现在恐怕……恐怕已经知道了什么。”
看样貌,猎人应当比游让不止长了几岁,但现在的他,在这邋遢的青年人面前,宛如个孩童。
“什么……”
“你知道么,世上所有的生物都拥有灵性,那些东西——那些可怕的东西也不例外。”游让目不转睛地盯着猎人家里那面陈列着野兽残躯的墙,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万物皆有灵,而有些则是可怕的……”
“什么意思?”
“人死后不甘心的话,会变成厉鬼,动物也会。那些不安分的东西被统称为‘怨灵’。”
“你的意思是,那畜牲是某头死去的野兽变作的?它是死在我手下的么?所以才会回来报复?甚至连同整个村子也不放过?”乌和埋着头小声地问道,心中亦隐隐不安。
“不,不,没那么简单,怨灵无法通过自己本身来作祟。”游让面对着乌和接连的疑问,仍是头也不转地观瞧着那面陈列墙,他的目光在一张黄黑相间的虎皮上停留住了,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上面的花纹,“人死后化做的怨灵通常会附身于某个活人身上,或将其折磨致死,或迷惑其心以某些达目的,不过终究是精神上的控制。但动物的怨灵不同,它们虽无人类的心智,却比人类更野蛮,更直接,被动物的怨灵附身的人,不止精神会错乱,连身体也会变作野兽的身躯——被附身的人会变得狂暴,野性,嗜血,也就如真正野兽一般无二,甚至更加强大……”
“这些和我所谓的梦游又有何关系?”
“睡梦中的人,最易被控制。”
“你的意思……那头杀千刀的怪物其实……其实是我变的么?”
“我希望不是,乌和,你很爱这座村子,但……但我想不会再是其他人了。原本我也以为会是其它什么东西……”
猎人闻言,差些栽倒在地。
“你每次化作怪物袭击完人畜后,都会因为体力不支在第二天之前昏倒,不省人事地躺着野外的某个地方,这才解释得通我为何会在小溪那边找到你、为何那三个小伙子惨死你却无恙……你应该也知道……每次你‘梦游’到别处,在次日醒来时,恐怕嘴中与肚中仍然残留有生肉的味道……你嘴巴边的血到现在都没擦干净……而且,你真没闻见,你身上全是像由动物毛皮散发出来的浓烈恶臭味么——那可跟你的豹皮披肩没关系吧。”游让继续说着,但尽量将语气变得温和,毕竟谈话的内容已经太过残忍。
猎人呻吟着,浑身颤抖,口中胃中也是一阵恶心,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从未想到,自己要对付的竟然是自己,祸害村子的怪物竟然是自己……乌和设想过许许多多的可能,却绝没猜到,村西的那一户人家、昨晚的那三个帮忙的年轻人,还有那些被啃食的猪羊,通通是死在自己的手里,甚至被他一口一口吃掉……他手中的弓箭,最该对准自己……
“你别太过自责,那绝对不会是你自己的意愿,你只是被厄运盯上的人,”游让劝慰道,但明显,他也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至少,这和他意想的出入很大,“厄运就是这么出现的,无声无息。”
“怎么会是我?”猎人绝望地抬起头看着游让,一脸茫然。
“恐怕也和你猎杀的那些野兽有关,你是个出色的猎人,乌和,但杀了太多生,难免招惹上那些东西。如果我的猜想正确的话,也许就是因为你在山中猎杀的动物实在太多,它们中最强大而又带着愤怒的一只——甚至几只——变作怨灵附身在了你的身上。到夜晚时,在你精神力最薄弱的时候,它们侵占并改造你的肉身,夺去你的意识,唯一保留的,是你那狩猎的习惯……真讽刺,就如我所说的,它猎杀人畜,就像你猎杀野兽一般。它们缠上你了,或许是为了报复,或许是为了单纯的杀戮。”
“这是报应么……”
“因果循环,诸如此类。”
“我……我……我该怎么办……马上离开这座村子或是自我了断?”
“都没用,就算你自杀了,怨灵也不会消失,它会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你尸体的附近,找到下一个适合成为怪物的目标……”
“那该怎么办?”
“需要进行一些类似驱魔的仪式才可根除掉怨灵。”
“应当如何做……”
“我知道,并且我还可以试试。但有风险。”
————
深夜时分,下午的那阵骤雨持续到现在才停。村子里的人没一个敢入睡,明晃晃的烛光从每家每户的窗外传出,即使附近鸦雀无声,村民们仍然认定他们的耳朵里听到了不远处野兽的低吼,恐惧犹如恶鬼的长舌舔舐着人们的心尖,圈栏中的那些家畜,它们也仿佛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般,受惊了似的在围栏里乱叫乱拱……
一块被树荫和荒草遮蔽的破屋前,猎人正如昏厥一样瘫坐在地上,被粗布条蒙上了双眼、堵紧了耳朵、塞住了鼻孔。但从他嘴巴里传来的急促的呼气声,仍能知道猎人是清醒着的。
被附身者五感需暂失三感,这是除灵仪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么做,是为了引诱邪性却鄙昧的怨灵出现。它会误以为受害人正处于“睡眠”的状态,从而从宿主内心黑暗处苏醒过来,控制其脆弱的身心——只有在怨灵的意识完全占领宿主的意识、令宿主变得疯狂的一瞬间,迅速对其泼洒足以浇灌全身的瘟鸡血以及柳叶汁,便可驱散怨灵,使其化为一阵黑雾同着宿主口中呼出的一口浊气散在空气中化为飞灰……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通常不理想的情况发生的概率较前者大得多。
为了找到够量的瘟鸡血与柳叶汁,游让几乎将村子翻了个底朝天。瘟鸡在村子中还算常见,但那几颗柳树,在这花草树木包围的的地方却仿佛老天刻意刁难般罕有。更何况制作大量的叶汁,可并非容易事……
“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了么?”
黑影中,老村长从树荫下走出,端着锈迹斑斑的烛台,将火光照向地上那脑袋像是被裹成了个布球的乌和。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村长是游让唯一个告诉了事情真相的人。当老人听说那头惊悚的怪物竟然是这位勤勤恳恳的猎人过后,先是觉得游让就是个信口雌黄的疯汉,但慢慢的又无奈而荒唐地接受了这个说法,最后只剩下唉声叹气……老村长可以说是亲眼看着乌和从襁褓中抱出来到现在长大成人的,这种情况永远不在也不愿在他的设想之内,但他安慰自己,至少总算知道了祸害村庄的元凶后,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也算是拨云见日了。某种难以诉说的矛盾情绪如一块大石压着老人单薄的肩膀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还需要念上一段拗口的咒语,”邋遢的青年人摇了摇头。他抚着自己长长的头发,那油腻腻的感觉令他很不舒服,“不过我需要回想一阵子,实在是太长了。”
“你这后生到底是何方……唉……罢了……能救我们村子一命,老朽已是感恩戴德……”
“驱散怨灵后,你们会把乌和怎么样,虽然他不会再变成怪物了,但毕竟他之前做了这么多——”游让小声地说着,尽量不让地上的猎人听见。
“你早些时候也和我说了,他是无辜的。”老村长的声音却毫不避讳,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音量。
“那就好。”
“只不过,你也说了仪式有失败时会有意外发生……那会是什么?”
“最好祈祷不会发生这种事,还有,还请您离得远一点。”
游让半蹲着身子,思索着什么,随后从腰间抽出了一条赤红黑色铁链——就是他前些天束缚那暮妖时的那条链子。
黑衣青年将铁链如绳索般环绑在猎人的双脚边,紧紧勒住,以防不测。
“只是某种措施。”
老村长扶着额在一旁观瞧,好奇地估摸着他是怎么将那么长一条链子藏在那身黑衣下的。
游让往后退了几步,他一只手提着晃荡的木桶,里面便是那鸡血与柳汁的褐绿色混合物,它们粘稠又浑浊,还说不出的难闻;他另一只手则紧紧握着长剑,剑上散发着银光的古怪雕纹无时不刻在提醒着它的主人,它比起普通刀剑,更似一件艺术品……
“你别乱动,就像是假装在睡觉。”
“唔……”
“我虽然并不期盼这种结果,但还是必须告诉你,如果仪式出现了任何的意外的话,杀掉你是我最优先的选择,毕竟,我没有其它办法阻止那头怪物了,甚至我可能还会被你直接给杀掉。”
“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