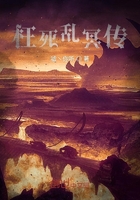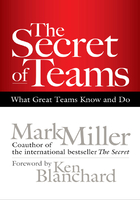“这……这是哪儿!?”
“你该来的地方。”
“周围为何一片漆黑?”
“死人的眼睛里还能看见黑色,这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
“死人?”
“你该不会觉得自己仍然活着吧……凡人……”
“我不知道……我记得我看见了好多人……好大的火和烟……熏得天都快烧起来了……好多血……母亲……父亲……啊……那些士兵……怎么连小孩和女人都没放过……真是一帮畜牲……可恶啊……”
“还是忘记那些吧,安心的接受这一切。你死得再悲惨也与现在的你毫无干系……”
“我真的死了么……我……”
“你很不甘心?怕死么?”
“是……是啊……我不想死……我不想死……等等……你是谁……”
————
北峵国,棱洲,猇夺城。
而今看似风平浪静的故城还是与游让那如一潭浑水般污浊的记忆里一样,一样缺少人情味,一样死气沉沉,仿佛藏匿于阴云后的太阳都不愿再多照耀此地片刻。
踏在故壤熟悉的土地之上,游让并未多么兴奋,但仍然算得是感概良多。
其实,他已经不怎么记得是多久离开这里的了。
但空气中那股死水般的铁锈味道依然如旧。那是由猇夺城外围那堵环城而建的古老城墙上镶嵌的巨型铁板散发出来的。
那些足有廿寸厚的铁板上全是箭镞与投石留下的坑洼——在很多年前,此地遭遇过小规模但极其之激烈的战争。闹剧般的内战。
“我只知道在以前,即使到了深冬,这猇夺城也没这么冷的。”
干冷的空气确实可恼,游让的脸上快掉层皮了。
青年人自言自语着,他在常着的那身黑衣上面又套上了一件厚厚的兽皮大衣,就与单薄的黑布衣相比而言,它很是暖和。那件引人注意的兽皮衣上面的紫红色花纹绮丽而罕见,从游让身边路过的路人与客商纷纷投来了好奇的目光,没人能认得出来那是出自哪种野兽,狼皮、虎皮都不是,也不是异色的豹皮——连帮忙加工的裁缝在游让递过这张皱巴巴的古怪皮料时,琢磨了半晌,也都没看出来。
“我只希望它不会发臭或者掉毛,最后怪到我身上。”这是昨日那位在商讨完价钱后憔悴的老裁缝对游让郑重其事地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
“哈,只有足够锐利的刀剑,才能让这块皮子掉毛。”
在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之前,游让很少与人讲笑。但没人会为了一头死了还被剥去了皮的无名怪物而笑,不过通常来说,还喘着气的怪物,更让他们笑不出来。
街上巡逻的披甲卫兵们站成了一道仿佛密不透风的墙,拦住了游让的去路。
他们的服色如烧得火红的铜块般显眼,令深知其威风的本地人皆退避三舍。
“喂!你可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士兵先行跨出一大步用力按住了游让的肩膀,动作相当之粗鲁,极不礼貌。
“现在是什么时候?”游让抬起头与士兵对视,目光里并没有后者意料中卑微。
“最不太平的时候!呵,如今全国戒备,局势如此之紧张,战争就要来了,人人都提心吊胆,你却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我大北峵的边陲重地、抵抗南国的第一道放线,嘿嘿,样貌嘛……又是这么的可疑……”士兵冷笑道,态度戏谑而轻蔑,“你别不是敌国的……”
“真是可笑,我进城的时候怎么没见有人拦我?”游让对着对方回敬以同样的冷笑,并试着夺回被另一个走上前来的士兵缴去的长剑,“而你,你别碰这东西,当心别伤着,这把剑和你手上的破铜烂铁可不一样。”
啪!
游让话一说完,正在抢夺长剑的士兵愤怒地一把抢过了剑,随即一耳光直接重重地打在了游让的脸上,打人的动作娴熟得就像是拿筷子吃饭般简单干脆,长剑也被他顺手甩飞了出去。
“他娘的,下贱的东西,敢跟老子这么说话?你以为你是谁?”
打人的那个士兵是这群人的头子。他摆出了一副令人作呕的夸张表情,语气中满是不屑与厌烦,眼神里闪过一丝似乎是经常出现的恶毒。他时不时摸摸胸甲前亮闪闪的银色鹰爪图纹,那是他们不需要任何正经理由都可以任意杀伐与抢夺的御赐通行证。
倚势凌人带来的虚荣,他们很爱这一套。游让不知道的是,这帮人在前日以“怀疑一对落魄父子是敌国内奸”为由,将在南街街头遇到的那对可怜的父子俩活活打死——只因这个卫兵队队长的妻子不久前难产而亡,内心积攒的怨恨与不快得不到发泄。今与敌国的战争在即,挥舞不惯刀枪的普通人的命会变得没那么稀罕,心狠手辣的兵丁士卒会更加被统治者们需要,所有烧杀抢掠都会得到理由,而所有理由都会变得高尚。
青年人撇着眼睛看着面前这个狠狠掌掴了自己的士兵,右手下意识朝腰间伸去,可是那儿什么都没有。
他无奈地咽下了这口气,打算就此作罢。但对方却没打算就这样轻易放过他。又有两个手持长枪的士兵,快步闪到游让的身前,将枪尖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看样子,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显而易见,归乡的青年人并未得到北峵同胞们的欢迎,相反,倘若他不想这些暴躁的同乡们对自己的态度更加不遂人愿的话,应该老实接受这一切。
他意料到了这一路可能会有不顺,但没想到麻烦来得这么快。
游让抬头对着故乡的天空摇了摇脑袋:“我并非是剑铜国的间谍或密探。”
“你说不是就不是?我们既然有所怀疑,就应该得到证实。”
“你们总不能无中生有,”游让强撑着笑容,内心已是翻涌起怒意,他可很少忍耐,“这未免也太过分……”
那个给了游让一巴掌的矮个卫兵队长突然又将手掌抬到与游让的颧骨齐平。
啪!
一声干脆的响声再次冲破游让的耳膜。
又是狠狠地一巴掌,这一次大概已经用尽了这位侏儒队长的全部气力。
青年人露出憎恶的表情,恍惚了半刻,嘴里喷出一口污血来。
“你这天杀的,是真蠢还是假傻?你看看你这副邋遢的模样吧,就像一个该死又下贱的乞丐,不过,你这身上穿的东西嘛……看样子可不是穷人穿得起的啊,该不会是你从哪里偷来的吧?手脚不干净的畜牲。”士兵开始阴阳怪气地大笑起来,令人骨子里都发毛。
“所以,我……到底是密探还是小偷?”游让咬了咬牙,随后不乏敌意地敷衍一笑,抹了抹嘴边的血迹。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老子觉得都是。”
“那我是……难逃其咎了么?”
“你知道就好。”
“真是近乡情怯呢。”
将长枪架在游让脖子上的那两个士兵收起了武器,从背后拿出一副大得吓人的镣铐,他们粗暴地擒住了游让的双手,准备直接铐上他:“乖乖站好别动!”
“小子,你会为你刚才的不敬而后悔的……”猖狂的卫兵队长将脸贴在游让的耳根边上,小声地说道,语气似冰冷的剃刀刮过,令人心中结霜。
游让一听此言,愤怒一摆身挣脱开试图将他锁住的士兵,将铁制的枷锁顺手夺过砸在了对方的额头上,这一下犹如雷击,一瞬间,鲜血淋漓,士兵躺在了地上,殒了命。
随后游让迅速往后一闪身,和对方的其他人拉开了距离:“恐怕,我不能和你们走。”
“抓住他!”士兵队长阴鸷的脸凶恶无比,他一挥手,示意手下们行动。
另外的三个甲士一拥而上,拿起手中的长枪就冲着游让刺去。
青年人欲低头四处找寻自己被扔掉的剑,但来不及了,尖利如牙的三杆枪头似蛇首般已经探到了他面前。它们像吐着信子,非要尝血不可。
游让半曲双腿,后仰上身,躲过了对方足以致命的攻势。他灵活地闪身,趁着这些士兵落空之时,迈步到对方的近前,手一张,顺势抢过他们的武器,将三杆尖头枪一并夺下,捏在掌心。
随后游让找准力道,利索地转身,没给对方任何准备的机会,一把将三柄枪朝前方奋力猛掷,这一下使出了他那远超常人的全部力量,在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兵卒没铠甲遮掩的面门上狠狠地留下了三个吓死个人的血窟窿。
血肉瞬间绽开。
“啊啊!”
剧烈的疼痛没多久便要了这个可怜人的命。他临死前撕心裂肺的吼叫,能让人感受到他的绝望。
看着自己面目全非的同僚在痛苦中失去了最后一口呼吸,剩下的两个士兵们开始面露怯色,双脚试图向后退让。
“你们在干嘛!?他就一个人!”士兵队长见游让气力如此之大,动作也快得惊人,他心中也是有些胆怯之意了,但那不容反对的语气仍然是坚定无比,“赶紧拿下他!”
士兵们踟蹰着,壮起胆子还是向游让扑了上去。他们俩用尽吃奶的力气将青年人死死地压在身下。
他们手臂都在颤抖,面目扭曲得已经不成人样。
“他娘的,”士兵队长从靴子上的皮鞘里抽出了一把带刺的短匕首,径直朝被两人压住动弹不得的游让走去,“把他给按住咯,别让他乱动!”
游让没法轻易摆脱两个穿着铁甲的男人的重量,只得半弓起背脊,像一只机警的猫似的尽量将身体保持住并不稳定的平衡。
他向后微微一缩,巧妙地调整身体,侧对着正走向自己的士兵头子,后者把玩着锋利的匕首,漫不经心地对着面前的空气挥舞,朝游让露出狰狞的一笑,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
“今天遇见了我,只能算你倒霉……”
游让眼见即将割到自己颈下的刀尖,又望了望附近原本喧哗却突然噤若寒蝉的过路人。看着他们熟视无睹、生怕惹祸上身的模样,青年人重重叹了一声气。
其实这一幕,大概在这猇夺城再常见不过。
游让喃喃自语道,他看着正和自己对视的士兵队长,露出了相当无所谓的表情:“你的这把小玩具,也只有这种用处了吧。”
“呵呵,你这卑贱东西,是真不知天高地厚啊。”矮个的士兵头子突然收起了匕首的刀尖,转而用刀背狠狠地拍打在一动不动的游让的下巴上。他假装着急地扶着额头,“那……那我倒要看看这没啥大用的小玩具,会先把你的鼻子切下来,还是眼珠子挑出来,亦或是割掉你的耳朵……”
很少有人能用这么平静的语气,说出如此可怖的话。
在两个壮年的牵制之下,游让用尽力气,右臂还是可以勉强活动。他眼看如此,便抓住了机会,迅速在某个人的臂膀的压力下抽出右手,靠着过人的力量,顺便一把扯下了那个人的厚肩甲。那块缺了半截的板甲就像一个半弧形的铁砖,还带有凹凸不平的纹路,游让拿起它,向面前半蹲的士兵队长重重扔去。
只听见砰的一声,头颅开了血花,这个侏儒身材的士兵头子应声倒地,这一下恐怕打着了他的要害上。他握着的匕首失手一撇,也阴差阳错地深深刺进了他自己的肩膀里。
“啊……”
呜咽一声,他再没说话的力气了。痛苦令他抽搐起来,死,对这连铠甲都不合身的矮个兵头来说,只是时辰问题。
游让不再等待,他青筋暴起,慢慢积蓄着力量,忽然身躯一震,终于挣脱了那两个手下的束缚。
他反应奇快,站直了身子,一伸手找到了落地的长剑,将其如旗帜般高高举起,无论是哪一个试图靠近的人,都会在最短的时间以内,狠狠挨上一剑,然后带着一条整齐的伤口切面离开人世。面前两个手无寸铁的兵卒以及旁边倒地不起的头子——这三个人,已然对他没有任何威胁。死了的那两个,血已经淌了一地,犹如一片散发着腥气的湖泊,湖泊里引来的不是鱼群,而是观望着的乌鸦。
游让在怕的,只是可能会被这里动静引来的更多巡逻士兵,毕竟双拳难敌四手,他不想再惹出更大的麻烦,不过现在,他也已经是罪责难逃。
“这荒唐的地方,可真是一点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