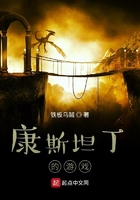难眠的夜晚,陌生的天花板,石头看着窗外,眺望着那唯一永恒不变的天空。
夜幕下的空地上,人们围着一堆燃起的篝火,勾肩搭背地喝酒。
他们情迷意乱地载歌载舞,婀娜的舞姿姿如火一样的妖娆。
阿阳就混迹在人群之中,搂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
他的嘴里叼着一根燃至一半的香烟,与女人在漫散的烟雾中含情脉脉地对视,空出来的手,不安分地在对方的身上游离着,就像两条在泥水里相互缠绕的蛇,冷漠的血脉中贲张出灼热的欲望,彼此之间默定对方就是今夜风流的归宿。
女孩坐在距离篝火不远的地方,沉默地喝着一杯一杯辛辣的土酒,面无表情地看着火光照耀下的那些被酒精和欲望支配了思想的男女们。
大海就坐在她的旁边,以着同一种沉默方式与她对饮。
不时会有快乐的男人和女人们前来邀请他们一起去火堆附近跳舞,大海总是淡淡地报以一笑,婉转地拒绝他们热情的邀请。
而女孩则置若罔闻,看都不看那些人一眼,依旧默默地往自己的胃部灌酒,一碗接过一碗,沉默的姿态,就像一朵需要酒水灌溉才能盛放的冷艳玫瑰。
渐渐地,人们或许是死心了,或许是习惯了他们的沉默,遂不再理会这对不解风情的一男一女,就像是遗忘落在冷板凳上的灰尘一样地将他们遗忘。
火热的舞会不知道会持续到几点,人们经久不散的热情犹如火光一般的明亮。
当女孩和大海喝下第五壶土烧酒的时候,那个黑色皮肤的女人拉着阿阳走了,然后,女孩和大海打开了第六壶酒,就像是在庆祝他的得手,还有他的离开。
屋子的本身并不怎么隔音,人们的歌声轻而易举地穿过了石与木的缝隙,混合在浓烈的土酒味里,隐隐地传来,响应在这间昏暗的房间当中。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世界,每个人的世界里都有每个人的孤独。
石头愣神地看着窗外很久,忽然想起了那个蒲公英一样的女孩。
如果她还在的话,会不会就像这些人一样,那样快活,那样欢乐。
又那样地...孤独?
就像一群如果不聚在一起,如果不生火取暖,就会冷死的动物一样。
“世界终究不过是外物,”黑暗中,有人在轻声地说,“你的灵魂才是你的本身。”
“孤独...你还能拥有更多的孤独,”那个人用风沙般缥缈的声音说,“享受孤独,承受孤独,让孤独在你的灵魂里生根,在你的灵魂发芽...”
“最后,”他或者她,说,“就在孤独中死去吧,在死亡里...拥抱灵魂最深处的孤独...它是你开出的花,是你结出的果,也是你唯一拥有的意义...”
“你从未拥有过什么,自由不过是生者的幻想,感谢孤独吧,请虔诚地感谢它,因为那是你短浅的生命里,”那个人又一次说,“唯一真正拥有过的...意义。”
“其余的一切,终不过虚妄...”
他或者她的声音,又像是一只纸折的白船,载着摇晃的烛火,迷离而又虚幻,在恒古不定的长河中奔流远去。
冷漠的风仿佛在这一刻暴动了起来,倏地打穿了蒙尘的玻璃,掀起一阵阵迷惑的土灰,流离的碎片散落在半空。
梦醒后的失落时分。
孤独的男孩在黑暗中猛地坐起身来,睁大了那一双紧闭的眼睛。
汗不知不觉浸满了后背,房间里的玻璃清晰地矗立在木质的窗框里,根本走不进一丝半缕的风来。
窗外面的篝火已经熄掉了,冷却的余烟缓慢地从黑色的灰烬里升起。
狂欢过后,空地上再无一人,散落的杂物堆得到处都是,一片枯黄色的叶片在冷清的月光下被风吹起,悠悠地在空中打了个转,随后又回归原处。
死去的树叶再一次软绵无力地重新落在地上,就像是疲惫的人陷入梦乡,在梦里走过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轮回。
“你是做恶梦了么?”大海在他的身后说,“怎么半夜忽然醒来?”
你...是做恶梦了么?
一段再简单不过的问话,不怎么大的音量,每个字都咬的很轻,但却又显得掷地有声,带有一种不同于梦境的,脚踏实地般的真实感。
石头愣了一下,失神地看着那张熟悉的脸,“刚才...一直是你在说话么?”
大海直接地回了他一句,“是。”
“没有其他人了么?”他不太确信地看向大海的身后,眼里满是惶惑。
尽管房间里大概一眼就能看完,但是他仍在努力着,试图从微暗的阴影里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以确定他刚才经历的不是梦,而是现实。
尽管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会有其他人?”大海怔怔地看着他,“阿阳去别的地方睡了,明日...她睡在隔壁,所以...”他顿了顿,“这个房间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从我回来以后,”大海补充似地又说,“这里,一直都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阿阳...”石头默默地念叨着,随之联想起了什么,“他是不是跟一个肤色很黑的女人搞在一起了?”
“就在你和她喝第五壶酒的时候...”他有些过于着急地问,“阿阳...他是不是跟一个肤色很黑的女人走了?”
“抱歉,当时没怎么留意,”大海说,“没有在意那个人的肤色。”
“抱歉。”他说,他又一次说,并且投以真挚的目光,就像一只懵懂无知的猫。
石头没有说话,他讨厌猫,特别是什么都不懂,分明不关他的事,但还要摆出一幅很自责的样子的那种猫。
抱歉,又是一个抱歉,这有什么好抱歉的,干嘛非得为了一件事道来两次歉,道歉有什么用啊,道歉有那么好道歉的么?!
为什么...你又没有错,你干嘛要道歉,你道什么歉啊,你到底在道什么歉啊?!
那种混乱压抑的感觉又来了,如同后遗症般支配着他,脑子的思绪像是被撕碎的棉布一样错乱,心脏被压制着蹦跳。
无名的野火在见不得光的暗处咆哮,不受控制地四下蔓延,不受控制地灼烧着他积郁的黑暗,灼烧着他的理智。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会变得这样的狂躁,恨不得马上要放火烧死自己,烧光眼前的一切。
他想他的孤独不是没有原因的,但那种原因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出来,他憋着,忍着,狂躁到想要捣毁一切可以捣毁东西,想要撕碎一切撕碎的东西。
包括这个该死的身躯,这个可有可无的灵魂,这个营地,还有那个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道歉的神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