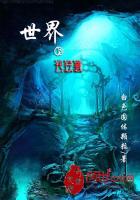“给妖怪吓尿了的软蛋们,都给老子听好咯,”一个貌似带头的男人沉声低喝,“听从警官姑娘的调令,成败就此一举,即便是豁出性命,也要确保警官姑娘的安全!”
“这一夜过后,我们已没什么可再失去了,”他说,“但求在最后能够死得体面一点,不要像那些只会逃跑的胆小鬼那样...”
“窝窝囊囊,死得不明不白,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不一定会死的,”琳低声说,“请相信我的判断,现在,请各位慢步向右移动,不要再说话,不要有过大的动静,我们要转换到月光照不到的地方。”
男人淡然一笑,没有再说什么,琳则目光专注地看着那个遍地阴影的地方,就像是凝视着一片影子的湖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知道怎么的,她忽然爆发出这种大而无畏的气魄来,似乎铁了心要与这头妖怪决一死战。
就像那个留在山道上的男人,誓死要与这该死的命运抗战。
即便往左往右都可能是死路一条。
移动的过程很顺利,每个人都在沉默中前行,直到脚下的影子被庞大的树荫吞没,宛如置身于这片辽阔的影子湖泊里。
深墨的黑暗消除了个体的微小差异,人与人之间似乎失去了间隔,仿佛融为了一个静谧的整体。
每个人的呼吸频率都是一样的,脚步都是一致的,恍惚之中,似乎就连埋藏在胸腔中的心跳速度都是一样的。
这群人在不知不觉间竟连成了一个整体,平稳且安静地徜徉在光照不进的黑暗里,一边提防着蜘蛛的来临,一边又随时准备暴起,迅猛地将其击杀。
就像是渔夫与湖里的水怪在玩‘比赛谁的反应快’的游戏。
地面的震颤仍在持续,远处的那场轰烈的战斗正往白热化的阶段发酵,很好地消除了他们挪步时发出的微声。
黑暗在不断地加深,到最后,琳干脆闭上了眼睛,把全副身心交给自然,仔细地聆听空气里微末的声音。
“留意,”她忽然眉头微蹙,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说,“东南方向,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是它,小心。”她猛地睁开眼,下达了一道如同水滴石穿般的命令。
靠近东南侧的男人二话不说地抡起手中的战斧,也不管前面有没有可供他劈砍的目标,他就那样悍勇地挥落战斧,动用浑身的力气,仿佛势要劈开一座巍峨的大山。
黑色的影子里浮起细微的波纹,突破界面的蛛矛与男人挥斩的斧刃在半空中相遇,仿佛命中的注定。
清越的一声交响,男人慷慨激昂的怒吼与蜘蛛嘶鸣直直地对撞在一起,锋刃交接,陡然迸射出冷漠的火花。
“兄弟们,老子逮住它了!”男人大吼,怒视着阴影中那一连串黑色渗人的眼珠。
然后,他猛地探出手,顺势攀过去,狠狠地拽住它的另一根蛛矛,就像是贪财的地主死守着家财那样,死也不肯松手。
他就像是他说的那样,抓住了这只蜘蛛,抓住了那刻入骨髓的仇恨,他残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其中最多的就是这种既可怜又可悲的恨。
如果连恨都没有了,他也不知道日后又该怎样,为了什么而活,当然,也有可能,可能再也没有日后了。
蛛矛上的细刺轻而易举地戳穿男人粗糙的肌肤,致命的毒素犹如涓流般汇入他的血管,他依旧怒瞪着眼,丝毫不顾手上灼热的疼意,转头对着其他的男人们大吼,“别他妈给老子发愣了,趁现在,快!快做掉这头该死的畜生!”
“我他妈...我他妈快要死不瞑目了!你们这些孬种王八蛋!”
他在黑暗中燃烧着咆哮。
男人们一拥而上,数十把钢铁锻造的冷兵器高举在他们的头顶,气势汹汹地朝向这边冲刺而来。
冲杀的声音淹没了脑海,拽住蜘蛛的男人似乎终于忍受不住体内激荡的痛意,持斧的那一只右手渐渐开始脱力。
他垂下了右手,换作左手攥住这头该死的怪兽,手里的战斧随之被横地打飞出去。
蜘蛛忽然洞开那一张深渊般的巨口,锯齿般的獠牙凛然直下,就像铁制的钉耙一样噬咬在男人的肩膀上,刺穿他的骨骼。
它一边剧烈摇晃身体,一边扭曲狰狞的嘶叫,就像一头暴走的恶鬼,发狂地势要勾走这个可怜男人的灵魂。
就在男人的意志力与蜘蛛的残忍较量之中,有人挥动砍刀,有人舞起重锤,有人把一条又一条乌黑色的铁索捆在蜘蛛的身上,锁住了蜘蛛的大部分关节。
这一刻,他们仿佛都化作了朴实勤奋的打铁工人,把这头蜘蛛当成了又黑又硬的铁块,不惜力气地痛下狠手,一下又一下地捶打,试图打破它那坚硬的外壳,砸死这头死咬着男人不放口的畜生。
被咬住的男人吼声越是撕裂,抡动武器的人们的举动就越是疯狂,绝望与痛苦的怒吼声持续回荡在这片巨大的阴影里,仿佛支离破碎的灵魂。
这是一场关乎于死亡的竞速,所有人都在卯足了劲地争取。
要么就是在同伴在被咬死之前砸烂这头蜘蛛,要么就是等到同伴被活活咬死后,事后再倾泻满腔无能的愤怒。
但是,包括被蜘蛛咬住的那个男人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怜人的命已经不长久了。
即便被救下来,充其量也就仅剩下半口气而已,拿半口气的作用,顶多就是让他再跟他们说多两句离别的话。
然后,他便要离开了。
但就为了这两句话,为了这半口气,这群如熊一样健壮的男人们,一个个就像是输光家财的亡命赌徒,精神错乱的疯子那样,一边发狠地尖叫着,一边发狂地暴跳着,一边又放肆地唾骂,一边又悲痛地恸哭。
似乎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来得更为悲伤的事情了,阴沉的天空好像马上就要塌下来了,大地依旧在震动着,哀嚎着,仿佛也在痛诉这个混蛋的离去。
那个被蜘蛛咬住的男人的声音渐渐微弱,直到如同树叶落地般静止,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声响。
他终于死去了,在剧毒与咬噬的包围中得到解脱,当他闭上眼的时候,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的疼痛可以令得他感到痛苦了,也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令他感到恐惧,还有悲伤,此刻,他已经起航,在这片阴郁的湖泊里,去向那些曾经到过的大海。
那里...有他的家人、朋友,还有那些孩子们...在那里等着他。
钝重的锤子猛地一下砸穿了蜘蛛的头盖骨,将硬壳里那一团掌控意识神经的大脑捣成一堆令人作呕的烂泥。
蜘蛛松开了口,把咬住的受害人放下,庞大的身体也跟着闷声倒下,搁置在黑暗的草丛里,就像一具风干多年的野兽残骸,再也没有动静。
男人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这场恶斗的胜利,可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为这样获得的胜利感到庆幸,大家都沉默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似乎都尾随了那个男人远去,变成了一块又一块爬满了苔藓的墓碑。
那种曾经由里到外支配着他的痛苦似乎没有散去,而是被平均分成了很多个等分,然后分摊给在每一个沉默的人。
那些痛意,那些绝望,就像是种子,埋在他们的心里,在那里生根,在那里发芽,从此以后,永无休止地缠绕他们的灵魂。
琳在沉痛中抬起头,目光冷漠地仰视某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在一条带刺的荆棘藤上,一个微笑的女孩坐在那里,静默地看着一切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