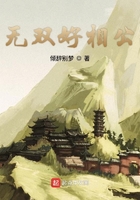“没想到几年不见,你已经进步到这般程度了。”宁子蔺眼皮都不抬一下,“来吧,让我看看你现在到底有多少本事。”
谷阳关城头,御水披着厚厚的两层大衣,娇弱的身躯仍能感受到北国冬季的逼人寒意。宁子蔺出城迎敌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她就那样靠在城头,美目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城下的战局,丫鬟数次恳求她暂时进暖房里歇息片刻,都被她直接无视了。
那个辛国将军应该是武定侯邱以天,他看上去要与宁子蔺决斗,全身发出红光的样子似乎甚是可怖。刚才邝飞扬折了一阵,不知道宁子蔺能不能赢下这一战,御水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
目光不自禁地向斜下方飘去,略显瘦削的身躯还是那样的引人注目,并不魁梧,却恍若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自信而冷傲。
一如许多年前的那个傍晚。
彼时她还只是个贪玩的小女孩,虽然接受着严格的礼仪训练,仍然改不了玩闹的性子,仗着女皇的宠爱,在皇宫里随意出入,奔跑玩耍不避闲人。
这一****仍如往常一般在御书房外的小花园追着蜻蜓玩耍,不意只顾抬头看天,没注意脚下,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在地。她一向性子坚强,虽然疼痛难忍,也不愿开口求救,龇牙咧嘴地在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忽然她感到身子一轻,一双温暖的手将她扶起,背后传来轻柔的低语:“下回走路小心点,别再摔了。”
回眸一瞬,便再也无法忘却这张脸。
清秀俊朗的面庞,温暖自信的笑容,满足懵懂少女那若有若无的所有期许,在她小小的心底里,就此埋下了一颗种子。
直到女皇宣他进御书房,方才知道他便是新近临危受命,就任南方军团军团长一职的宁子蔺。年少成名的他,傲而不狂,骄而不躁,不光是京城所有的贵妇名媛都为他疯狂,就连军中那些只认资历的老将,也对他青眼有加。
她忘不了他进门前那回眸一笑,仿佛着了魔似的,往日那个疯疯癫癫的小丫头从此收敛了脾性,变得格外的安静,用心学习着为她安排的所有课程。
所有的一切,只为了再遇时能以最美的一面展现在他眼前。
然而那个傍晚却粉碎了她所有的幻想,面对柔情少女的含羞表白,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消融,变成冰一样的冷傲,冰冷地吐出三个字:“不可能。”
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她都在努力地逼迫自己忘掉这噩梦般的一切,以至于整天失魂落魄,就像没了主心骨一样。直到很久以后,在女皇的刻意培养下,学会了机谋权变的御水,方才知道那三个字的意思——
外臣结交近侍,是绝对的死罪,罪不容赦。
回想着如一场梦般的过去,当她醒过神来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稳操胜券。
“呼……”邱以天只感觉手中的战锤似有千斤重量,艰难地抵挡着宁子蔺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冰寒真气不断透入体内,让他感到无比的难受。
差距比几年前更大了,真不知道这个怪物是怎么办到的。邱以天越打越心惊,看到宁子蔺嘴角挂着似有似无的笑容,便知道他还未尽全力。
“去死吧!”见他又是一枪迅猛刺来,邱以天恶向胆边生,索性不管不顾地抡锤砸向宁子蔺的胸口,想要拼个鱼死网破。
刹那间,御水几乎要惊叫出声,宁子蔺去似乎微微回头,向她投来一个暧昧难明的笑容,细微到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呼——”巨锤带来的风声从原本宁子蔺端坐的地方一扫而过,那里已空无一人。千钧一发间,宁子蔺终于展现了真实的实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将身躯扭转,藏入马腹,手中长枪去势不变,如同一条毒蛇,狠狠地将牙尖扎进邱以天的小腹。
两人纵马交错,邱以天只感觉到伤口处的血液都凝结了,他并不对此感到庆幸,宁子蔺一向以寒冰真气的纯正著称,伤敌之后很快会顺着伤口处的血管侵入对方体内,若不及时运功抵挡,怕是下半辈子都别想站起来了。
他闷哼一声,丢下战锤,紧紧抓住战马缰绳,落荒而逃。
“哈哈哈哈……”宁子蔺张狂的笑声响彻整个战场,他高调地勒转马头,猛地挥下手中的枪杆!
“咚!咚!咚!”城头上的战鼓被擂响,黑压压的羽军精锐骑兵开始动了起来,重骑兵在正中突前,轻骑兵分散两翼,重步兵在后压阵,趁着士气高涨,发动了第一次冲锋!
这是真正的集团式冲锋,八万精锐铁骑顺着地势很快将速度提升起来,隆隆的蹄声混合着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以雷霆万钧之势狠狠撞向对面数十万大军的方阵!
羽军重骑兵,一向是各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编制部队。选用北地出产的精挑细选的踏羽马,这种马极为高大神骏,力能负千斤,只有这种马才能承受数百斤重的铁铠包裹。
厚实严密的锁子甲将马上的骑兵保护得近乎刀枪不入,同时这样的重量冲锋起来光是冲击力便足够恐怖。
整整一万名这样的重骑兵突在整个骑阵的最前方,密如飞蝗的箭雨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在挠痒痒,根本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随着惨烈的嘶叫声和撞击声,重甲铁骑就像一柄尖刀,狠狠掼入拦在正面的宪国春华营长枪兵阵中。
两军接战处,早已成了一副人间地狱的惨象,无数的枪兵被铁骑的强大冲击力踏为粉末,也有不少骑兵被四面八方的长枪挑落,瞬间被身后的友军踩为肉泥。重骑兵的第一波冲击便让号称铁壁的春华营损失惨重,阵线岌岌可危。
皇甫怀月等人眼看赵子仁独力难支,赶紧出动来援,却被左右两翼的羽国轻骑兵拦住纠缠不休。
血浪飞舞,断肢齐飞,这场双方精锐主力的殊死较量,很快变成了一场混战,也正式揭开了谷阳关之战的序幕……
尤世春近来的日子很不好过。
作为辛国封西道参将,本来手里只有几千杂兵的普通军官,就在大军西征前夕,突然被赋予了保护粮道的重任,虽说只是负责封西道境内这一段几百里的官道,还是让他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尤其是这两天,原本平静的官道上似乎突然多了一批马贼,经常抢劫过往的运粮队。
这帮人神出鬼没,来去如风,也不曾留下哪怕一具尸体。而且每次只劫少量粮草,剩下的一大部分都被直接烧掉。尤世春不怎么灵光的脑袋,只能想到马贼这一种可能性了。
当然,依据惯例,大部分的劫粮报告都被他私自扣下了。开玩笑,粮草被劫事小,要是让太子爷知道自己办事不力,这乌纱帽他还要不要了?说不准连项上人头都得搬家。
但他也知道,瞒报归瞒报,该办的事还是必须得办。三天之内必须抓到这伙该死的马贼,然后自己再想办法填上被烧掉的粮草,才有可能逃过一劫。
他阴着个脸,带着三百骑兵游弋在马贼最常出没的官道上,身后还跟着一支运粮车队,四周早已安排了弓箭手和大队骑兵埋伏。为了早日抓到马贼,他也是不惜以身为饵,亲自押运粮草,就等着马贼出来自投罗网。
螳螂可悲的不是捕蝉的时候发现背后有一只黄雀,而是发现自己捕的就是黄雀。
五里开外的一处背阴的小山坡,第七旅的骑兵们纷纷或躺或靠,在草丛里休息养神。洛宇,杨舒和尉迟虎站在山头望着不远处那支傻乎乎的“诱饵部队”。
“洛大哥,看尤世春这架势,还真把我们当马贼了。”尉迟虎跟洛宇已经很是熟稔了,称呼也随之变成了洛大哥。
“呸,还玩钓鱼这一套。顺路把这一票收拾了吧,不过是一帮杂碎而已。”杨舒无聊地拿脚尖在雪地上画着圈。
“大哥,你下个令吧,不出半个时辰,保准让那姓尤的跪在你面前啃土。”尉迟虎早已跃跃欲试,这几天跟着洛宇好好过了一把当马贼的瘾。
“打,自然是要打的。”洛宇眯着眼睛,脸上浮现出一丝狡猾的笑容,“不过,我不要你们活捉或者杀掉尤世春,只要把他赶跑就行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难道留着他去通风报信?”尉迟虎不解道。
“没错,就是要他去通风报信,他若是不去,说不得还得赶着他去。”洛宇笑道。
“你是吃饱饭没事干,自讨苦吃?”杨舒忍不住挖苦道。
“别忘了我告诉过你们,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洛宇正色道,“尤世春只不过是一条小鱼,就算吞掉他也无关大局。但是这样一来,就会打草惊蛇,让周围其他的辛国军队心生警戒,集结重兵往路上一堵,到时候我们想再撤回去就难了。”
“所以,你想主动出击,把那些垃圾先清扫了?”杨舒想了想,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才不管那么多弯弯绕绕呢。”尉迟虎嘟囔道,“反正大哥你总是有道理的,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吧。”
“那就出发吧。”洛宇微微一笑,转向坡下的骑兵们,左手放在口上,吹了个响哨。
听到指令,第七旅的士兵们纷纷起身,披挂的披挂,牵马的牵马,不多时就完成了集结。八千铁骑枪在手,箭上弦,就像是一头正在成长的幼狼,亮出了自己尖锐的爪牙。
尤世春不知道自己这是倒了几辈子的血霉,本想钓鱼,没想到鱼是钓上来了,可来的却是鲨鱼。当黑压压的羽军骑兵出现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马蹄声震得车轱辘都开始晃动,他才发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
慌不择路的他命令伏兵即刻出击,以求稍稍拦阻羽军骑兵的冲锋。这样规模的一支羽军骑兵深入敌境,他想当然的以为是羽军派出来执行最危险任务的精锐部队,却不知道仅仅是一支普通的轻骑旅罢了。
依据这种推测,他知道自己手下绝对不是眼前这支羽军的对手,于是当机立断,带了数百亲兵便向北撤退。
洛宇哪里肯放过,随便一冲便将军无斗志的辛国军队冲得七零八落,留下杨舒率主力清扫残余敌军,自己带上四百多亲兵队,风一般掠过混乱的战场,紧紧追着尤世春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