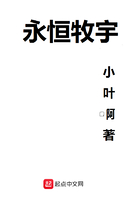“宋大人今日又是旬休吗?”
庄阿腴缠绵倒在贵妃榻上,身上裹了两床厚厚的棉被,鼻尖几乎要沁出汗来。船舱里温暖如春,四角都摆了烧得正旺的炭盆,毕毕剥剥地响。
她今日早上稍微扭了颈子,连带着右肩到指尖也僵得隐隐作痛,索性倒在床上躺了一天。小丫鬟乖乖地为她捏着肩颈,撅着小嘴数落她:“他刚派了仆童来送信,说晚上来喝茶。庄阿姐,天气晴好,下船逛一逛又何妨?你天天窝在床上,关节都酥了,一不留神就要扭着。”
“不碍事……哎呀,这书真叫人看不懂。”
她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古籍,槐花黄绿的封面一半写着什么下篇,一半却被烧焦了。
“不过,好像不是旬休,是小公主满月,皇上又给他们放了假。”丫鬟满心歆羡地叹了口气,“怎么有人这么会投胎呢?有皇帝爹爹疼爱着,吃喝穿戴肯定都是天下独一份,全国的百姓也念她带来的大庆。人家过的日子,我这辈子都没福分过一天的……”
庄阿腴突然面色一变,她双唇抿着不由一阵阵地发颤,怔怔地落下泪来。
小丫头才发觉自己又说到了主子的伤心事,慌忙握着她的手道歉:“阿姐!对不起,我说话又不过脑子了,你别伤心……”
若干年前,庄阿腴还年轻的时候,身怀有孕,生了一个孩子下来。
听雨眠舫的规矩很大,一般不允许姑娘怀上孩子,除非恩客为她们赎身。没人知道鸨母怎么默许了这个孩子的诞生,还容阿腴将养身子,为她请大夫,等她坐月子。
但这个孩子满月的时候,就被抱走了。至今去向成谜,生死也不知。
孩子呀,她怀胎十月,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才生下的孩子。
没有他时,这天地是一方江海,庄阿腴漂泊其中。
有了他,小耗子般温暖地挤挨着她的怀抱,几乎要结束了她的孤苦。
她还没给他起一个名字,孩子就丢了。
春末的黄昏,街上有小贩在叫卖,阿腴想去买一支平安符给她的小耗子,匆匆跑着出去了。回来时窗户两面敞开,疲倦湿软的春风吹拂着芙蓉绿的窗纱,丫鬟晕倒在床榻边酣眠,摇篮里已不见了小婴儿。
她几近哭干了一生的眼泪。
“不怪你,是我又忍不住想起来。我已经老成这个样子,他应当也已经变成一个男子汉了。”庄阿腴轻轻捏了一下丫头柔软的掌心安抚,泪眼中她望着窗外,红墙掩映间的楚宫。“多么有福分的孩子……但是她的母亲不在身边呀。”
.
庭院深深深几许?燕宫柳,楚宫蔷,乱红都要飞过秋千去。
那一道道的红墙似乎有无限高,无限远,燕宫柳轻抚着朱砂染就的墙面,与淮河绕宫两岸的河面,每一棵都有百丈高,像是为王宫守伫的巨人。
听说楚国的王宫里种满了楚宫蔷,每一株都如同身姿曼妙的官女子,想来远没有柳树般萧瑟。
正殿前匆匆经过的太监噤若寒蝉,互相连眼色都不敢递。
昏暗的大殿内,燕王踱步在王座前,抱着一个哭泣不停的小婴儿,柔声安抚。
两旁的宫女太监黑压压地跪了一地,十几名身披金甲的殿前武士将一个华服迤逦的老人团团围住,有的揪着她苍苍的白发,有的扣着她枯树皮一样老到不知寿数几何的手。
她脚下有一支匕首,沾了几点桃花般稚嫩的血。
小婴儿的面颊上,有一道崭新的血痕,若是没有偏几寸,没有浅几分,刚刚满月的燕国小公主,千万人民为之同放烟花,共贺大庆的神仙宠儿,也许就要陨落在此日。
“柔儿乖,不要哭……唉,算了,她一直是乖乖的,不哭也不闹,我还担心来着。今天被吓了一跳,哭一哭也好。许天师,你这又是何苦?”
几个太医连滚带爬地冲上正殿,跪在燕王面前。燕王摆了摆手,将大掌覆在小婴儿颊畔上方,玄奥的灵气让血滴瞬间凝固,伤口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红印。
他口中的天师,就是正被武士们扣押着,长袍曳地的老太太。
当一个人已经老到分不清性别,会诞生一种有尊严的美感。她耷拉着老朽的眼皮,浑浊的双眼难得炯炯望着一心牵挂着小女儿的君王。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陛下怀中抱着的不仅是一个小婴儿,还是一颗祸国殃民的不幸种子。她死,燕国就能活。她活,燕国有无数人要死。”
“荒唐,荒唐!朕勤政不辍,轻徭薄赋,爱怜万民犹如怀中的这个小丫头。燕国如今的平安世道,历年征伐混战的其他六国百姓有哪个不羡慕?如此都不能保全国家,还要靠杀掉我的女儿吗?”
燕王重重地拍了一下书案。
他怀里的小婴儿打了个哭嗝,感觉脸上不再痛了,就眨巴着大眼睛乖乖啃起手指来。桌案的轰鸣和父亲厉声的呵斥,都没能让她重新哭出来。
“敢问陛下,您的女儿生母乃是宫中的哪一位妃子?为什么小公主诞生以来都是您亲自照看,没有母妃在身旁?”许天师的声音兀然尖锐起来,猛地抬起武士禁锢着的瘦弱手臂,长长的指甲直指着绣金线的襁褓。
燕王一怔,沉默不语。
“公主降生的那一天,夜空中虽有血月吉兆,我燕国的祥瑞却逃跑了!
公主满月,祥瑞藏进苍南山里放起火来,他的本命真火!
此子不除,燕国休矣!!!燕国休矣!!!”
天师凄厉的嘶号在大殿中回响,襁褓中的小公主打了个哈欠,居然迷瞪着水汪汪的眼睛睡着了。燕王连忙摆了摆手,殿前武士们拖曳着老者下朝着宫门外走去。
“王上莫要动怒,依老奴看,小公主福大命大,自诞生以来就有天数庇佑,这才是我大燕真正的祥瑞!姓许的准是老糊涂了,她的话不听也罢。”旁边的一个老太监举着手里花白拂尘,哑着嗓子上前进言。
“哼,钦天监的某些人就是不明白,朕以国库之资供养他们天天无所事事,上香祷祝,为的就是要一个顺耳的天意。什么吉兆,什么祥瑞,没了我家柔儿,要这燕国祥瑞万世又有什么用……柔儿乖,睡觉觉了……”
燕王捻着胡须,乐呵呵地哄女儿。他的话尾却让伴君数十载的太监总管打了个颤。
大殿之外,老者最后的呼喊从遥远处戛然而止。
“苍南山那边怎么样?”
“回陛下,半月前太子调派了附近十几个宗派的人手前往搜捕祥瑞,早间大火,正好他们都在。太子已飞赴苍南山,目前火势已经在控制内了。”
“那便好。这些奴才,护主不力,全拖出去。听到许天师胡言乱语的武士们,找个机会发到边疆去,别给他们散布谣言的机会。”
“是,陛下。”
太监总管抬头,见燕王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冷不丁汗流浃背,心领神会地跪地叩首:“老奴的嘴用钉子钉好了。”
.
晚空之上,成百上千的飞剑曳出青光,直奔浓烟滚滚的苍南山。
寅西青站在飞剑尖上,他身后坐着一对青年男女,和抱着养气草花盆的郭大锤。
叶庭有些迷惑地望着身后越来越远的上清宗。他本以为会被抓到戒律堂关上几个月,等内门考核结束再被放出来。
没想到忍静峰的地面还没踏上,他们就和一大堆上清宗的弟子一起被分成十几个小队,由筑基的戒律堂弟子押上飞剑,奔赴北方。胡清正被分进另一组里,老实孩子郭大锤就负责了叶师兄的躯体安全。
“寅师兄,我们这是去哪儿啊?”那互相依偎的一对男女中,胆子比较大的男子开口问道。
“苍南山。这一趟去也不是为了惩罚你们触犯戒律,毕竟我们忍静峰的大师兄蓬天阁也在,守一峰的大师兄李惊鸿也在,情况紧急,所以才拿你们抓了壮丁。说起来还要算拜托诸位帮咱们宗派一个大忙呢。具体的等到了南山脚下,蓬师兄会为诸位讲解的。”
寅西青这一番话说得随和又客气,也没人驳他的面子。
“叶师弟,我看你出手时灵气虽然充沛,却没什么章法,应当是只修炼了心法但未修炼剑诀吧?”他又回头,向着叶庭问道。
“啊?是。”小叶还在发呆,想着错过了今年内门考核的事,听得他问,反应了很久。
“我这随身还真带着咱们上清宗的基础剑诀呢,你先拿着看看。”寅西青从怀中掏出一本被翻得老旧的薄册,上清剑诀四个大字赫然其上。
一对男女有些好奇地望过来,不明白戒律堂的师兄为何要关照一株还未化形的草精。
“……”叶庭沉默不语,也没有接。
这个师兄对他很和善,却是沉月师姐恨透了的人。这一份人情欠下,他不舒服。
“给你你就拿着呗,苍南山肯定出大事了,你看这烟!”滕老仙就像是个劝小孩收压岁钱的家长,他倒挺怕叶庭没有剑诀傍身,一不留神出点什么事。
飞剑缓缓落地,巍峨万丈的苍南山巅冒着浓烟,被遮蔽的天空昏暗得恐怖,仿佛酝酿着一场浩劫。
“不要客气了,商师妹的事情,有缘我再跟你解释。”寅西青将剑诀拍在养气草的花盆上,摆了摆手。“去前面找你们蓬师兄吧,我先回去了。苍南山一行,务必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