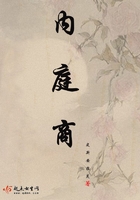惠陵,沿濮寨。
入夜之后,璟瑶穿上一件长过足底的白衣,将长发完全披散,站在月光之下宛如飘渺鬼魅,她脑筋一歪,决定先用四哥做个试验,果然璟瑞乍见她的装扮时惊得大叫大跳,盘熹见过之后亦是拍手称奇,可见这般变装的效果甚如人意。璟瑶对二人交代道:“我稍后只打算现身片刻,说几句话便躲起来,二位老人年事已高,倘若被我吓坏可就是罪过了。你们要紧接着上前追问,一定能够问出其中的秘密。”
午夜寂静,二老对枕难眠,突然听到屋外传来怪异的声音,起先略感害怕,随后眼中生出某种希望,老婆婆道:“赶快出去看看,是不是他们把孙女送回来了?”
璟瑶独自站在院子中央的枯树之下,早已备好用素白绢纱笼罩的小烛灯,藏在树后发出幽幽冷光,只听她戚声切切地说道:“阿爹,娘嘞,我回来看你们……”
二老瞠目结舌,双双颤抖道:“……你……你是谁?”
璟瑶道:“我才离家两日,爹娘怎不认得我了……”
老婆婆既有惊恐又有惊喜,唤道:“你是……七巧?你……怎么回来了?”
璟瑶以小碎步向前飘移少许,哀声道:“儿媳的心中尚有郁结,阴公不让转世投生,故而特地回来找到爹娘……”
老公公显得极为不安,试探道:“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们?”
璟瑶表现得愈加幽怨,带着哭腔说道:“爹娘送我去做那般见不得人的事情,却还不知道我为何心中含怨么……”
“巧儿呀……”老婆婆猛然悲痛地坐倒在地,哭道,“我们的确做出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他威胁我们,如果不把你送去,家里人恐怕都活不下去了啊……我只是想,委屈你一次,就能让全家过上好日子……如果你没死,你回家来,我们也一定不会嫌弃亏待你的,你是这个家的恩人呀!”
璟瑶努力控制自己不为所动,继续用凄切的声音说道:“可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老公公此刻也显得十分歉疚,以足顿地,郑重地说道:“你放心,我们将来一定会好生对待宝妹,补偿从前家里对你的亏欠!”
璟瑶依旧哀怨不改,悲叹道:“可是你们眼下却在帮助害我的奸人,还说什么将来的补偿呢……”
“巧儿呀……你不知道……”老婆婆呜咽大哭道,“他们……抢走了宝妹!”
璟瑶立即抢问道:“是谁抢走了宝妹?”她一时过于激动,甚至忘记掩盖自己的音色,幸而二老已经心绪迷乱,未加留心分辨,脱口答道:“是禺门镇长家的大儿子……盘决。”
此时璟瑞和盘熹正躲在屋后,璟瑞将拳头重重地砸向土墙,怒道:“原来是他!盘兄,你还记得辛未说过的话么,想必是盘决做出恶行,去找胞弟帮忙遮掩,这才设计出来这般阴险狡诈的手段栽赃给廖兄!”盘熹的眼中亦显愤愤不平,但先按住璟瑞的拳头,作出一个噤声的手势,示意他们暂且旁观璟瑶的动向,勿要贸然惊扰此局。
璟瑶见事情的真相已经大致明晰,便悄悄拉了一下手中的细绳,大量粉尘和烟雾从树上坠落下来,她则趁机隐藏于树后,完美退场。璟瑞和盘熹接着现身,扶起神情迷茫的二老,老婆婆诧异地问道:“……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盘熹道:“我等昨日隐约察觉二位家中有所异常,担心歹人会在夜里暗行加害,因而一直未敢离开。”璟瑞接道:“老先生,老夫人,你们方才所说的话我们全都听见了,我们的一位朋友正是因为此事受到牵连,被盘决陷害他伤了七巧姑娘的性命,请你们向外人道出真相吧!”
老公公颤声道:“你们方才……也看见七巧了?”
盘熹道:“是的,七巧姑娘含怨而死,如今专程回来向二位告知她的心意,你们为了她和孩子,也应当将真相如实说明。请放心,我一定会还七巧姑娘一个公道,也还你们全家一个公道。”
老公公不安而彷徨地说道:“可是……我们已经收下了人家的钱财……他们说,如果我们胡乱说话,就会要了我们的性命……而且……小孙女还在他们的手里呢……”
盘熹长作一揖,随后横眉直立,展现出令人信服的威严姿态,说道:“在下乃是经纶堂少主,今日在此向二位保证,只要你们据实以告,此事绝对不会降罪于你们。请二位将盘决拿来的好处交给我,也将救回宝妹的事情交给我。”二老听他言明身份,双双大骇,慑于威势,连声应是。盘熹又道:“璟瑞,回想昨日盘冼所言,想必他们已经苟同沿濮寨主做好了虚假案卷,想要抢先呈递给经纶堂掩盖真相,你我这就另拟文字写明实情因果,且让他二人签画留证,即刻连同收买作伪的赃物一并带回去,再看他们还能如何抵赖!”
------
惠陵,经纶堂。
阿程在公子外出期间颇为闲暇,每隔半日便去北阁楼内探视片刻。廖绎接受她精心打理的三餐时总是免不了连声称谢,她每每回道:“廖师兄,公子交代我照顾好你,如有任何需要请你尽管告诉我,一定莫要客气。”阿程一向敬重廖绎是一个才德兼备的师兄前辈,明明有过人之能,明明应该得高贯众,他却时时事事待人拘谨客气,上至堂主、下至刚入门的小弟子,他都要求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步路做到仪礼周全、绝无踏错,如此长久只会令人三分相敬、七分疏远,连日接触下来总让阿程暗感无奈。
璟瑞和盘熹快马加鞭,在两日之内离返经纶堂。盘熹于午后匆匆见过阿程一面,即需立刻去向父亲回禀。璟瑶也一同跟着回来,她则急于与璟瑞先去看望廖绎。
屋内空落无声,廖绎稍显憔悴,垂目沉默不语。璟瑞在旁边没话找话地说着,又站又坐,不肯停闲。璟瑶静静注视许久,忍不住开口关切道:“廖师兄,让我诊一诊你的身体恢复得怎样了吧?”廖绎全身微滞,抬眼看了看她,依言将手腕抬到桌面上。璟瑶搭脉细诊,担心地说道:“你连日忧思过甚、劳心伤神,怎能恢复得好呢?”
璟瑞听得困惑,急忙跨近两步问道:“廖兄,你有何忧虑,竟至这般累及身体了?眼前的蒙冤之事尽管交给我们解决,你可要安下心来好生休养呀!”
廖绎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乐兄,你为人豁达、心思单纯,自然极少会有烦心之事。可是我……近日以来思绪繁杂,一时之间总也理不清楚。”
璟瑶微笑着说道:“从前幼时不懂事,总是劳烦廖师兄费心开导我们,如今你有了什么烦心事,不妨也说与我们听吧。四哥虽然平日里疏懒,嘴巴还是很严密的,你们向来亲密无间,想必你也不会担心他将这些私话道与外人,至于我……你如果介意的话……”她故意将“至于我”一句话说得尽显委屈,使人不忍推脱。
廖绎忙道:“我自然也是信任你的。”
璟瑶于是眨着眼睛笑盈盈地看他,意思是说:那便请你尽管将烦心之事说出来解忧吧!
廖绎犹豫再三,但见她眼波清澈、面容温恬,对自己的关切之意溢于言表,心内渐生温暖,便道:“经纶堂于我有恩有义,我暂时蒙冤并无大碍,况且心中亦已知晓,乐兄和盘大公子必定会尽力替我寻回公道。只是……近日以来,我愈是得闲无事却愈发思虑良多。之前我目睹沿濮寨村民的中毒情状,一时因为怨怪自己的族人而无颜立世,后来得知堂中弟子竟然在无山原上屠肆无辜,又会反过来更加怨怪同门。往日我全心全意只在围墙之内修习,尚能假装不闻外事,现在我日渐感觉自己身处两难,不知将来应该走向何方……”
廖绎心想:我身世特殊,自然不敢有过分的期许,堂主对我从无慢待,我也理当心怀感恩。但是我自认才德中上,却始终难有立足之所,整日被差使调管一些闲杂事务,或是终己一生倚靠乐兄这个闲散王子、度过轻松无用的日子,二者均是非我所愿。这几日间我反复思量,我所欲为、我所应为之事,是时候迈出第一步了。
璟瑞似懂非懂,迟疑道:”积土成山并非须臾之作,双方恩怨均有是非功过,也不是简单就能说得清楚的。”
璟瑶心思较密,更能理解廖绎的焦愁,她斟酌言语,用心说道:“四哥,诚如你所言,日久冲突并非一方错责,如今再去追溯当初的源头,也于现状并无助益。廖师兄,我曾经听过大哥一言,‘平宁则求稳,饱暖则思安’,只要恢复无山原上安定温饱的生活,自然不会再有人愤世作乱,也不用经纶堂自损无数精力只为打压勍栾。可叹在于各族长者始终记恨于当年的仇怨,如今却连这一星点的恩善都不愿意付予。我也曾想过,眼下这种境况不是单凭几人了了之力所能化解的,不如顺应时势、依其自然,你看前尘历史的故事不都是这样讲述的么,等到再过一二十年,世间之事皆由下一代做了主,廖师兄今日所忧一定能够逐步转寰,那时我们便可以释然地将往日故事道与后人说了。”
璟瑞对于小妹言辞之中的远见暗暗心服,廖绎则微微蹙眉道:“那可是要等到何时,彼此之间又会有多少无辜之人遭受牵连摧伤呢!”
这时盘熹和阿程面带喜色地推门进来,三人随即休止了话题。盘熹神采飞扬地说道:“我们知道宝妹可能被藏于何处了,多亏阿程,她发现了经纶堂的一个秘密!”说罢将阿程从身后牵出,推到众人面前。
阿程对于公子在外人面前少见的亲昵举动一时含羞,双颊飞红,对三人浅笑道:“经纶堂中藏有密室,你们可知道吗?”
璟瑞和廖绎双双茫然摇头,盘熹道:“我今日也是第一次得知。”
阿程解释道:“我常日往来于各处居所,无意间发现许多屋舍与众不同,从外看去似是长形、进入之后却是方形,便在心中猜想,是否屋内大多藏有密室。堂中弟子尽皆对此毫不知情,我此前也是只在心中暗忖,从来未敢与旁人多言。近日我依从公子的交代,留心注意三师兄的动向,昨夜掌灯之时仿佛听见他的房里传出孩子哭声,声音微弱,只有静默贴墙才能细微察觉。于是我借由送茶点的缘故敲门求进,他许久才得出来开门,而我进屋之后却未见异常。那时我突然想到密室之事,推测是否三师兄也在暗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却只道除他以外再无旁人知晓,因而大胆地将兄长委托藏匿的孩子困于众人眼皮底下的密室之中。不过这密室之事堂主从未言明,想来应是堂中禁地,而三师兄却擅用密室做出害人之举,他的罪责必然推脱不掉了。”
璟瑶对阿程刮目相看,由心称赞道:“阿程姐姐你怎得这般又美貌又聪慧!你所料一定不错,我听二姐说过,经纶堂原是当年在御敌边堡之上重建的殿阁,其中藏有密室暗道自然不奇。”
璟瑞眼见真相将明,心中既舒快又气愤,义愤填膺地说道:“盘冼此人居然如此阴猾,竟敢将人藏于经纶堂之内,即便我们寻遍全城也不能找到宝妹,幸好被阿程姐姐发现了。这下可好,那些害死七巧姑娘、诬陷廖兄的奸人,再也无法抵赖了!”
是日掌灯之后,盘熹代传堂主谕令,召集所有弟子汇聚于慎省阁。盘冼已被禁足反思了两日,再见众人时满脸皆是愤愤不平之色,他与几个平素要好的弟子凑在一起,故意大声引导众人说出关于廖绎的恶言,假装看不见盘熹正在不远处面色暗沉地凝视着他们,直至璟瑞和璟瑶走进阁内,才将声音逐渐降低。璟瑞冷笑一声,心有不甘地走过去嘲讽道:“三师兄,刚被放出门便这般闲不住了,方才在说什么呢,怎么不让我也听一听?”。盘冼尚且不敢在明面上对王子不敬,言辞闪避推脱,众人见状亦皆陆续闭口消停下来。
待盘章忌现身施令,盘熹当众将近日所查实情一一禀明,盘冼的脸色越听越难看。阿程随后从弟子群中走出,双臂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儿,这是她适才趁着各房空无一人,迅速机巧地进入密室找到宝妹。阿程毫无羞怯退畏,面向众人提声说道:“奴婢从大公子之命,在盘冼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孩子,她正是死者七巧姑娘的独生女儿!”话音一落,满堂杂议,她则趁机稍稍凑近一步、对盘冼小声说道:“三师兄,你如若抵赖不认,方才宝妹的一只鞋子好像被我不慎掉在了她受困之处,不妨让公子带堂主过去亲眼见一见这个罪证。”盘冼张口结舌,眼前已然大罪难辩,偷用密室之事更不敢再向堂主挑明,自己的把柄落在眼前这个小丫头的手里,他却只得瞠目哑口,不能反驳。
多番证词证人之后,盘章忌逐渐明白真相,他怒目责问,盘冼跪倒在地,无言狡辩。盘熹终于心生扬眉吐气之感,他傲视堂下,严责盘冼及相关人等,又急于立威,抓住此事便要重罚。盘章忌思虑再三,还是压制了儿子的行为,严厉斥责当地镇长、寨主徇私,勒令将盘决收监再议,而对盘冼罚工罚俸、追加禁足悔过。
盘熹心中痛快和不服并存,心想:我有心拉拢廖绎为己所用,为他劳心劳力地奔忙了数日,能够就此还他公道,事情也算顺利解决。可是父亲终究顾及盘决、盘冼本家长老的颜面和权势,未能严惩真凶和帮凶,如果由我主持决断,定然要让盘决以命相抵,也要将盘冼逐出师门!也罢,今日之事到此为止,来日我必得另寻良机,重新树立自己的少主之威。
盘冼深知在堂主的宽恩和本家的庇佑之下,连大公子亦不敢严惩自己,瞬间竟又暗自得意起来,竟道:“堂主明见,我与家兄自然甘愿领责,这就回去反思悔过,不敢有异。但是廖绎在外行踪不定、拖迟归期,是否也应当追究严查?”
璟瑶嗤笑一声,心中暗骂这人真是心思不正而厚颜无耻至极,她脸上似笑非笑地抢言道:“三师兄是指廖师兄留居酒馆之事么,那是我做的呀。他前几日为救多人性命而损失了大量鲜血,身体尚未痊愈便要逞强出行,途中突发不适,幸好被我去镇上采办药材时遇见。我看他走在路上摇摇晃晃的,才要唤他,他却晕倒了,半天也叫不醒,我急着赶回寨子,便将他寄托在酒馆里。他那时一路昏迷,自然不知是我,我今日来到这里方才说起,四哥还说这样巧呢,是不,四哥?”
璟瑞当然附和属实,盘冼则当然不服,质疑道:“如若属实,怎么先前你不早说?”
璟瑶对他愈发鄙夷厌恶,仰头嘲道:“先前三师兄可曾问过我吗?”
盘冼面色恼怒却不敢发作,旁边也有与他交好者低声劝说他暂且作罢,他咬牙将委屈咽进肚里,然而心中郁愤越想越深,与廖绎等人的怨结自此而积。
------
众人退散之后,盘章忌将璟瑶和璟瑞留下,他原本惯于悍厉严肃,在唤兄妹二人上前之时转换为慈蔼老者的神态。他与乐王年轻时候曾有过命之交,因而对待兄弟的子女更比对待亲生子女另有一番爱护之情。
璟瑶离开经纶堂已经五年有余,对于幼时的记忆大多印象模糊,眼前面见长辈的举止中不免显出些许敬畏和拘谨,盘章忌便有心刻意慈善地说道:“小璟瑶,你不记得我这个大伯了吗?当年我曾经带着你采花、钓鱼、放风筝,手把手地教你和你的熹哥哥写字,你可是还偷偷拔过我的胡子呢。”
盘熹罕见父亲如此心悦,顺应着笑道:“璟瑶妹妹,这世上除了你,再没有人敢拔父亲的胡子呢。”
璟瑶不好意思地笑道:“璟瑶犹记您疼爱晚辈,待我极好,我幼时不懂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盘章忌呵呵笑道:“你可的确是个多病多灾却又总不安分的小人儿,从前没少让堂中各位师傅们费心,也让你的熹哥哥担心。”
璟瑶应道:“璟瑶承蒙旧恩,离开经纶堂之后也总能念及您的怜恤包涵和熹师兄的照护。”
盘章忌称心如意地对她招了招手,示意她再走近些,说道:“大伯许多年未见你了,还没来得及给你们兄妹俩备下几个礼物,你过来,”他招呼侍者递上一枚小盒,只见其中一块精巧罕见的碧绿奇石,他爱惜地摸索着说道,“这是去年族中采石工匠在尧光山下得来的宝玉,取名叫作‘苍头冷翠’,他们不敢私留,呈给了我。四王子殿下,这里你最懂玉,你看这件石头可算得现世珍宝?”
璟瑞方才远远看见之时便已眼眸闪光,此刻上前近观,更是由衷地称赞道:“这是上品、极品、绝品呀,我往日见过的珍奇物什可都被它比下去了!”
盘章忌轻捋长髯,满意地说道:“这玉原是一对儿,我本想雕琢成型,只恐我老人家眼光陈旧、手下之人工艺蠢笨,反倒累得它拿不出手了,便将玉胚子留着,一块去年生辰时给了他——”他意味深长地指向盘熹,又对璟瑶说,“这一块就送给你了,他日用时尽可全依你的喜好,花样由你们年轻人裁定。”
璟瑶忙道:“这太贵重了,晚辈确是不敢收呀。”
盘章忌温和但不容反驳地说道:“给了你便收下吧,若是你父王在这里,也会许你收着的。”
璟瑶心中生出朦胧的不安之感,男女赠玉的含义在九族风俗里非同小可,盘公此举莫不是有意要给自己与盘熹牵红线么,就差没有当面言明了。她便侧目去看盘熹的眼色,心想他俩既然互不属意,应当一路心思、尽早想法子消除这突如其来的牵线主意才好,却只见他低眉垂目、毫无波澜,似乎一切听从安排之态。其实方才盘熹同样骤然惊愕,然而他既往习惯于在父亲的威严之下妥协,遇事常不由得自己做主,因此一时未敢逆言。璟瑶心中暗生郁闷却无从言表,终于忍耐着将玉胚接下,又见盘公看看儿子、再看看自己之后心满意足的神情,心中愈发忐忑了。
三人退出之后,璟瑶面色不佳、径直要走,璟瑞也看出端倪,不想小妹与朋友闹别扭,急忙赶上几步拉住她。
阿程一直在外等待,上前迎候公子回房,却见三人皆是神情怪异,不敢多言,小心翼翼地探问道:“这是怎么了?”
盘熹顾不及理她,只对着璟瑶抱歉地说道:“璟瑶,方才父亲……只是玩笑话……我并无……之意……”
“我知道!”璟瑶果决地回复他,然后抬眼看了看阿程。她原本略知这二人之间的多年情意,眼见阿程眉目清明、言行聪慧、仪容温顺、一心为人的美好姿态,心中不由自主地充满歉疚,复而越发觉得莫名其妙,只因此事原本与自己无关,却被无端牵扯介入,心中不悦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忍不住又向盘熹责怨道:“可是熹师兄,你方才怎得一句话也不说,倘若让盘公当了真,日后便更加理不清楚了!”
盘熹蹙眉叹气,纠结地说道:“那只是父亲一时兴起的意思……或许以后未必再提……我方才也实在不知如何诉说……”
璟瑶与他说不通畅,转头住口、不再平白多言,心里的小人儿连连跺脚叹息,并想:熹师兄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盘公交代的话他即便在心里有千万个不情愿,也从来不敢明言反辩。盘夫人早不在世,而盘公对于儿子的私情着落却半点也不留意、不知情,今日他这般乱点鸳鸯,我该如何是好!不行,终身大事可由不得错乱,倘若下次谁再如此说起,我便是厚着脸皮也要直言清白才行。
(问世篇完,下续问情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