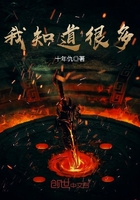(一)当爱遇到林徽因
有人说,爱一座城市,实际上爱的是这个城市里的某一个人。所以,在爱上城市以前,请先在这里谈一场恋爱。这样,你才能把心留给这座城市,而如果你的爱人没有离这里的,那么,你的心就永远无法从这座城市离开。
徐志摩说,康桥是他的爱。康桥令他觉得幸福,幸福得他从未忘记,以至于多少年后,当他重新回到这里,仍旧向它倾弹了深情的夜曲。这样的情感,或许正是因为他爱上了这里的林徽因。
感情很玄妙,有的人日日在你眼前,你却对他视而不见;可有的人,只一眼,便是一世的记挂。徐志摩从来没有想到,他为了追随罗素,从美国追到伦敦。罗素没有见着,但却认识了让他一眼,便记挂了一世的林徽因。
那天,徐志摩听说国际联盟同志会理事林长民先生,将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上发表演说。这位人称“书生逸士”的林长民,在当时提倡宪政、推进民主、热心公益;他与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是政治上的知己,生活中的挚友。徐志摩早就仰慕这位前辈的人格魅力,这次听说他来伦敦演讲,便拉了同在伦敦的陈西滢与章士钊一同去看。这一看,两人便成了忘年交。林长民很喜欢这位年轻的朋友,一见面便引为知己。此后,徐志摩便常到林长民的家里喝茶,聊天,说点政治,谈点诗艺。也正是这时,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
林徽因,系出名门,慧质兰心。这年她16岁,跟着父亲到欧洲。依着父亲的意思,她到这儿来,为的是增长见识;同时领悟父亲林长民的胸怀与抱负,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这样的抱负,在徐志摩初见她时,想来也洞察不到。徐志摩在林长民家里见到的,只是一个16岁的少女。她16岁的面容,没有风霜与世俗尘埃,秀丽纯净;但她16岁的眼中,已有聪慧的光在闪;16岁,少女一身白衣,仿佛刚从烟雨朦胧的南国小巷里走出,带着一身水漾的诗意与一身清丽,优雅而灵动,如一件精美的瓷器。这样的女子,让徐志摩一眼,便是一世。
那是一个关乎理想的时代,甚至连爱情都与理想有关。偏偏,徐志摩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很多人都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热烈的爱只是一种理想。在他眼中,林徽因是新女性。她自小便受过新式教育;她16岁便跟着父亲游历欧洲,眼界开阔;她会流利的英文;她结交众多外国名士……不必说,这样的女人与张幼仪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徐志摩恋爱了,第一次,以自由的名义,从他的灵魂深处,爱上了这个从自己的理想中走出来的女子。纵使他爱的,真的只是那个被自己理想化了的林徽因又如何?他生来便是为了理想而前行。
于是,徐志摩愈加频繁地出现在林长民有寓所。或许就连他自己都未曾觉察,究竟从何时开始,他的初衷从找林长民,变成了找林徽因。
徐志摩叫这个灵气逼人的女孩“徽徽”。有了徽徽的生活一下变得丰富起来。他可以与徽徽谈诗,谈艺术,谈书法,看戏剧,跳舞;他所有的情感可以向徽徽倾诉;他的理想与追求可以被徽徽理解;他每一次的激情迸发,都能得到回应……
浪漫的徐志摩开始了对林徽因的热烈追求。他想用自己的热烈换他的徽徽许他一个未来。可1920年12月,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给他去了一封信,信上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徽言附侯。”看来,徐志摩的热烈着实吓着了林徽因。本来,他们认识不过月余,况且林徽因第一眼见到徐志摩时,差点管这个爱慕她的男人叫“叔叔”。这也难怪,那时的徐志摩已为人夫,已为人父,而林徽因无论如何新式,却终归是个十六岁的女中学生。或许,这小小的误会正折射出一个事实:林徽因初识徐志摩初时,对他更多地怀着尊敬与仰慕。
此时的林徽因,面对徐志摩的追求有“惶恐”,有羞涩。她或许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徐志摩的追求,但她的心里,也定然藏着喜悦——那样一个才华才华横溢,浪漫而多情的男人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哪一个少女能不心动。所以,当时间前行,最初的惶恐与羞涩褪去后,他们的交往愈加亲密起来,特别是在林长民到瑞士开国联大会以后。
那是1921年6月,徐志摩经狄更生介绍,成为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特别生。幼仪此时已经到了伦敦,与徐志摩一同住在了沙士顿。不久,幼仪便发现她的丈夫频繁地往理发店跑。尽管幼仪明白这与一个女人有关,但她却未必知晓其中的细节。其实,徐志摩每天一大早出门,为的是赶到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他用那里当作收信地址,收林徽因从伦敦的来信。
伦敦那边,林徽因由于父亲到瑞士开国联大会,而过着“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的日子。用林徽因自己的话说,当时的她总希望生活中能发生点儿浪漫,而所有浪漫之中,最要紧的是,要有个人来爱她。但她面对的,却是伦敦除了下雨还是下雨的天气,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同她一起玩。这时,沙士顿的来信,无疑是为伦敦下雨的阴沉天空里注入了一点浪漫的阳光。而她从伦敦寄出的信,也仿佛是一阵奇异的风吹过徐志摩的心头,他的“性灵”也似乎一下子从懵懂与彷徨中看到了光亮。于是,康河柔荡的水波旁,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浪漫多情的诗人。
寂寞少女的心头有了浪漫的诗人,浪漫诗人的灵魂有了伴侣。可是一切就像电影突然中断了放映,几个月后,诗人的灵魂伴侣却抛下他回国,没有给徐志摩留下任何解释。
徐志摩的爱,像不断跳荡着向前的小溪,欢快热烈,无遮无掩,这正像他;而林徽因的感情却像伦敦永恒的轻雾,轻轻晕出迷蒙的暧昧,这也像她。今天,我们将这段感情从记忆的旧书箱中翻出,也只能看着点模糊的光影。我们用想象描摹着光影,再无法还原当年的影像。但无论如何,“林徽因”三个字,如康桥上升起的轻雾永远缭绕着徐志摩,从不来曾从徐志摩的生命中消散去。
(二)康桥的名士们
在著名汉学家魏雷(Arthur Waley)眼中,徐志摩在英国的经历 ,是一场充满了东方色彩的寻师问道。徐志摩怀着顶礼朝圣的心情要来跟从罗素,为此他甚至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都不珍惜,漂洋过海到了英国。可罗素那时已经离开剑桥大学,无奈之下,徐志摩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他转到了康桥。
在康桥,他进行了一场心灵革命。他先是下定了决心与幼仪离婚,这决心一下,灵魂便得到了释放。而他生活中的忧郁,似乎也在幼仪离开沙士顿后被带走。于是,那一年,离了婚后的徐志摩开始了真正的康桥生活,他眼中的一切都变得韵致非常。
他每天在清晨富丽的温柔中骑着单车上学,又伴着黄昏返家;当黄昏的晚钟撼动时,他会放眼一片无遮拦的田野中,或斜倚在软草里,等待天边第一颗出现的星;有时,他也会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榆荫下,眺望妩媚的校友居,瞻仰艳丽蔷薇映衬下圣克莱亚学院里玲珑的方庭;而康河两岸协调匀称的学院建筑,是他永远看不厌的风景;他也曾在河边的一处果园里喝茶休憩,等着成熟的果子跳入他的茶中,看着跳跃的小雀落到他的桌上觅食。
也许,他最喜欢的,是单独一人到康河那儿去,在这份“单独”里寻味着康河,就像寻味着一位挚友。河流梦一般淌过翠微的草坪,怀抱住了这里所有的灵性。徐志摩就像当年的拜伦,徘徊于河边,久久不去。这是他向往的自然,是他爱的“美”。当年康河的水抚慰了拜伦的心,而今它激荡了另一个人的性灵,如一帖“灵魂的补剂”注入了徐志摩天性敏感而多情的心里。
但是,徐志摩的心灵革命历程中,不仅仅只有柔丽风光与闲适的生活,如果仅是这样,那便称不上“革命”。康桥生活之所以能让他脱胎换骨般重生,与他在那里结识的人有关。
还是先从他刚到伦敦时说起。
徐志摩刚到伦敦时,很快便与一众中国旅英学者、留学生们打得火热。林长民,章士钊,陈西滢等人,都是在他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结识的。后来,借着陈西滢的关系,徐志摩认识了著名作家威尔斯(H. G. Wells),又通过威尔斯认识了魏雷。威尔士与魏雷都是英国顶顶有名的作家、学者,他们对徐志摩的印象极好,威尔斯甚至认为,和徐志摩的会见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这句话,对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学生而言,已是极高的赞誉。
与倾心仰慕的名士相交,还能得到如此荣耀,羡刹多少旁人,可徐志摩却实觉得“闷”。但如果你能了解,此时的徐志摩已经冲淡了留学之初的野心——做中国的Hamilton——那就能理解他的“闷”所谓何来。
在美国时,徐志摩也是钟情于政治的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政治学系,也算是政治学科班出生的人。无怪乎当年的他会自动自发加入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组织 “国防会”;也难怪他会写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当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潮从中国越洋袭来时,他热情高涨。多少年后,吴宓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徐志摩又是要打电话到巴黎阻止中国和会代表签字;又是要在美国报纸上登文章,还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讨论弹劾某人……忙得十分起劲。就连他自己也说,那时他对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称为“中国鲍雪微克”的政治青年,到了英国,结识了众多英国名士后,对文学的兴趣日长。于是,美国的日子在他眼里变成了一笔糊涂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那些枯燥的政治学课程与古板的教授,也自然变得烦闷无趣。正当徐志摩开始揣摩,如何换条路走时,他遇到了狄更生。狄更生看出了徐志摩的烦恼,便介绍他进剑桥大学,做了“特别生”。
进了剑桥,徐志摩的交际愈加广泛。这位风度翩翩的儒雅中国士子,时常身着长衫与师友们高谈阔论。瑞恰慈(I. A. Richards),欧格敦(C. K. Ogden),吴雅各(James Wood)这样的先锋学者,都是他乐于交往的对像。在这些人中,欧格敦是邪学会 (The Heretics’ Club)的创立者。这个学会主要研究诗歌创作与翻译,由于他们总是发表一些与传统思想相异的,所谓“异端邪说”,故而自称“邪学会”。徐志摩参与其中,与人积极地讨论中国诗学,成为了团体中的活跃分子。
除了青年学者外,徐志摩的剑桥岁月,还与作家嘉本特(Edward Carpenter)、曼殊斐尔(Katharine Mansfield)、美术家傅来义(Roger Fry)的名字连在一起。徐志摩跟他们说唐诗,也跟他们说中国诗翻译,他的深厚的文学素养,加上流利的英文,令他这些文人雅士的中,如鱼入深潭,悠闲自在。当其他中国留学生抱怨难以融入欧洲生活时,徐志摩似乎是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些欧洲文人、学者们通过徐志摩,第一次真正清晰地看见 “文学艺术这些事物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2而徐志摩也在他们的影响下,真正将自己的兴趣指向了文学。
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已经在徐志摩的心里扎下了根。他开始奉拜伦为偶像,总爱把自己视作拜伦式的英雄。尽管在魏雷看来,徐志摩缺乏拜伦式的愤世嫉俗,但他的确在日后的生活中,彰显了拜伦式的我行我素与倔强叛逆。
或许,徐志摩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在康桥遇到一场心灵革命。他查过家谱,祖上无论哪一代,都不曾有人写出过哪怕一行可供人诵读的诗句,但现在他开了家族先河,成了诗人。这一切都起源于康桥,而来康桥则全为罗素。
作为蜚声国际的哲学家,罗素也一向热衷与讨论政治,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就积极从事各种反战活动。他先是进行了一系列和平演讲,接着又撰写反战传单,为此罗素被罚了100英磅。他不服,拒不付罚金,于是政府变卖了他在剑桥大学的藏书。不怕,继续发表反战文章,最后终于被逮捕。正是带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同情,罗素对抗着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捍卫真理,绝不屈节。这一切,落进当时还在美国当“中国鲍雪微克”的徐志摩眼中,引得这位青年学生对他的人格无比景仰。
所以,徐志摩开始阅读罗素的书,这下更是教徐志摩领教了罗素的渊博学识。1920年10月罗素访华。这期间,他发表了多次演说,其观点震动当时中国知识界。这种震动,随着报纸,波及了大洋彼岸的徐志摩。终于,徐志摩毅然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头衔,乘船到了英国,想跟罗素这位二十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
可直到徐志摩到了伦敦以后才知道,罗素竟然会因其在一战期间的和平主张,被剑桥三一学院除名。这多少令徐志摩觉得失落。无奈之下,他只得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着拉斯基教授继续学他原来的政治学。第一次寻访,他与罗素失之交臂。
直到徐志摩进了剑桥大学,终于又有了机会。1921年9月,罗素回到英国,与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伦敦,靠卖文章过日子。十月,徐志摩从欧格敦那里打听到罗素的地址后,便找机会拜访了这位神往已久的二十世纪的伏尔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