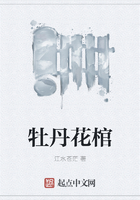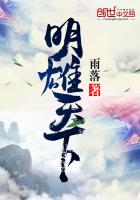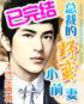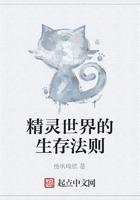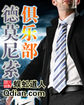大明是汉唐之外宦官势力最为庞大的朝代,这一观点,哪怕在此时也是不证自明,人所共知的。
原因则是由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
没有了宰相,权力全部归于皇帝,而全国政务也就得皇帝自己事必躬亲。
但人主以一身而临天下,不可没有帮手,朱元璋自己精力充沛又不信任外官,可以不辞劳苦夜以继日的处理国事,所以没什么问题。
成祖朱棣既精明又狠毒,不容易被人糊弄,也没人敢糊弄,并且他还设立了内阁辅政,所以也没什么问题。
但后面的皇帝,可就不肖二祖了。
纵观史书,二祖之后的大明之君很少有在用人上面不出问题的,而且一出问题,通常还都是大问题。
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结果。
二祖是什么人?
是造反得天下的枭雄,满脑袋尔虞我诈,一肚子阴谋诡计。一生之中只有他们防备别人篡权的时候,别人则很难防备他们的算计。
但他们的子孙,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不知世态炎凉人心险恶,更不知二祖开基创国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巨大,性格上就很容易乐天达观或是幼稚调皮,也很容易对身边百依百顺的宦官产生信任感。
而皇帝集权力于一身,没有人能制约他这盲目的信任感。
所以一个宦官只要博得皇帝欢心,便能凌驾于百官之上的事情就时有发生。
大明皇帝总以为宦官没有家庭没有后代,只能以皇宫为家,以皇帝为主,便不会谋私,更不会胳膊肘往外拐。
却不知道宦官们就因为常待在皇帝身边,比外官更了解皇帝的性格,糊弄起这天下之主来也就更得心应手。
皇帝出于信任不会管,内阁只是为皇帝出谋划策的顾问机构,没决策权也管不了。
宦官处于这种得天独厚的位置,能让他们不作恶的因素也就只剩下了个人的道德自律。
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易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亦是儒家的道德教条,宦官既都已经自残和无后,那也不大会被道德所约束。
所以宦官掌握权柄之后,往往比文官更贪、更狠、更疯狂。
比如成华年间的汪直,正德年间的刘瑾,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哪一个不是闹的怨声四起。
虽然宦官即使权势再大,皇帝都可以轻易把他们杀掉以缓和矛盾,但是宦官掌权时期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跟本消除不了。
因为他们能做的事,别人为什么不能做?他们不讲道德,别人又为什么抱着道德不放?
即使对自我标榜道德修养很高的文官而言,由于宦官许下的诱惑无法抵御,宦官带来的迫害难以承受,趋利避害之心一起,又有几个人还能顾得了道德?
这不是小事。
原因是,本朝终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更是只过多的依靠道德教条。
所以身居上位者即是领导人物,也是道德榜样。而榜样都不遵守道德,道德阵地岂能不失守?
没了道德约束,人性中那种弱肉强食的兽态心理就会复发,社会秩序随之就会崩坏,天下又岂能不因此而大乱?
皇帝放权让宦官作威作福,其实是在自己破坏本朝合法存在的根基。
这也是儒家制度为何将‘亲君子,远小人’视为君主执政的首要任务之根源。
“既然如此,那恢复三纲五常不正是救世良药?救世先救心不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那你又反对个什么?”
钱谦益点明姜洛话中的破绽,盛气凌人的逼视着后者。
对钱谦益,姜洛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先不说对方日后失节降清,就是以正妻礼节迎娶小他三十六岁的风尘女子柳如是,不也违背了他时刻挂在口上的圣教礼法?
他自己都遵守不了的三纲五常,还妄谈什么恢复。
是以,姜洛内心对蕺山先生刘宗周和虞山先生钱谦益的态度可说是截然相反。
刘宗周因救国理想的破灭绝食而死,殉国的同时也殉了自我坚守的道义,这总是让人值得钦佩的气节。
钱谦益却在亡国之际首尾两端,摇摆不定……
好罢,这也没什么,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
再说,大明又不是人人都是岳武穆,因此谁也没资格逼你一个老人去死。
可是你最后剃发易服,滂泼大雨中跪着迎清军入城……现在却表现的刚正不阿,急公好义,别人说句轻视道德作用的话都要喊打喊杀,这难道不是虚伪?
这实在让姜洛难以起敬重之心,所以对钱谦益的数落他根本不屑一顾。
姜洛的嘴角再次勾起,“我反对什么?我反对的就是三纲五常,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骗人的谎言。”
“竖子!”
钱谦益拍案而起,姜洛竟敢污蔑圣教,简直让他气炸了胡子。
“先不要急,我们就来说一下三纲五常的纲纪。”
姜洛一边说,一边有恃无恐的坐回了座位,这把钱谦益不当回事儿的态度显露无疑,让不少人都对他怒目而视。
在众目昭彰的时刻坐安稳后,他继续说道:
“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纪要求妻忠于夫,子忠于父,臣忠于君。
那么请问先生,夫要忠于妻吗?父要忠于子吗?君要忠于臣吗?
不需要吧?
既然不需要,那又如何在君主羞辱臣子,父亲厌恶儿子,丈夫背叛妻子时,让这臣子、儿子、妻子不心生怨恨而依旧忠诚呢?
不就是靠三纲五常来骗人嘛。
但这样的三纲五常,又置儒家亚圣孟子于何地?
孟子可是说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两者孰对孰错?”
……
姜洛的这个问题,若是按本朝以孝治天下的官方意识形态来讲,当然是三纲五常对,孟子不对。
因为洪武三年,太祖朱元璋读《孟子》,当读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句时,勃然大怒:孟子要是活到现在,就应该砍了他!
朱元璋遂颁布圣旨把孟子撤出孔庙,虽然后来又恢复其配享,但仍命当时的儒臣,刘三吾等人修改《孟子节文》。
把《尽心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离娄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梁惠王》‘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可杀’;
《万章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以及类似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有大过则谏,谏之而不听,则易位’……等等八十五条不合‘名教’的话全部删掉。
命曰:‘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
这确实是一种思想管制,但这事情其实要分两面来看。
如果朱元璋是站在统治者愚民维稳的出发点来做的,那大家无话可说。
毕竟太祖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你不服也没办法,谁让天下不是你打下来的。
可是,朱元璋是以中华文明复兴者的身份自居的,喊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却做起了这几同于‘焚书坑儒’的事情,不合适吧?
再说那些儒臣,身为儒家弟子,胆敢删改亚圣的思想主张,这也属于欺师灭祖吧?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本朝虽以四书五经治国,但又哪里真正的独尊儒术?都是对统治者有利的尊,不利的不但不尊,还要消除……
对大明皇朝阴阳两面的这一认知也不是姜洛所独有的,场中不少人就心有戚戚然。
比如说黄宗羲,作为日后的思想家,这种被隐藏不深的问题他早就看了出来。
又比如说陈子龙与夏允彝,这两人是同一年中的丙科三甲进士,此时亦都还有知县官职在身,只不过一个因祭祖,一个因省亲,都请了事假。
又赶上刘宗周行至金陵讲学,他们共同来拜访,这才适逢其会。
他两人身在官场,虽是七品小官,但已深刻的了解到,本朝统治阶层的专制思想是与儒家封建制度不自洽的。被高举起的仁义道德大旗之下,掩盖的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荒谬。
……
而在当下,姜洛以孟子的主张对理学的三纲五常,可以说是诛心之言。
但钱谦益毕竟是理学大师,而理学虽然不讲逻辑,可却囊括宇宙万事万物之理,这一问题自然也难不倒他。
只听他游刃有余的辩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要求每个人都各安其位的。
所以只要恢复三纲五常,那君自然是仁君,臣自然是忠臣,父自然是慈父,子自然是孝子。
而仁君慈父又怎么会做毒害臣子的事情?没有毒害,忠臣孝子又怎么会无故心生怨恨?
在三纲五常的教化下,大家互敬互爱,何须骗人?
这样的纲常,又怎么能称得上是骗人!
……”
不对!
作为听众之一的黄宗羲,几乎要呐喊出来。
钱谦益的说法在他心中,根本就不对!
可他最后却依旧没有出声,因为要克制情绪,嘴巴反而用力闭的更紧。
他要隐忍的不可言之事,他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的处世态度,使得他不能像姜洛那般不顾场合,做不留情面的舌战。
可他深知,父慈子孝的概念是不能导向君仁臣忠的,而父子关系也与君臣关系是两码事。
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虽是两人,本质却是一体,父慈子孝因此是天经地义的。
但对待君主则不能像对待父母一样。
因为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本是为了共同治理国家的目地才后天产生的。
如果一个人不当官,没有治理国家的责任,那君主对这个人来说就是陌路人,陌路人之间也就不存在忠孝关系。
如果这个人出仕做官,把治理国家当做职责,那这个人就是君主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之间也不该存在忠孝关系。
除非这个人不把治理国家当做首要责任,而将逢迎主上放在第一位,那才有了忠孝关系。
但如果是这样,这个人还能称之为官吗?充其量也只算得君主的仆人和婢女罢了。
因此理学把父子关系强行与君臣关系联系起来,是不对的。
而君臣即便名义上有君为上,臣为下的区别,那也只是职位分工不同而已。
从本质上来讲,两者则都是以‘兴天下之利’为目地的国事服务者,并没有贵贱之别。
尤其儒学体系是做了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预设;也就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依据的,于是君主就更不应该具备超然于整个国家政治架构之上的权力与身份。
所以子孝顺父可以,臣孝顺君不可以。
如果君对臣的要求是忠孝,而不是合作;那就等于是把国家当做自家,把臣民看做奴婢。
这样的君主,在黄宗羲的理念中实为天下之大害。
而理学的三纲五常,就是培养这大害的温床……
……
其实,像黄宗羲对儒家思想的既继承又批判一样,和他同一时期的文人,也已经有不少呈现出‘变异’的特征。
如陈子龙辑书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的经世致用;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众治’思想;
王夫之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的反禁欲主义……
甚至还有那个主张中西合璧的方以智。
明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真正的一元化,专制思想松动的皇朝末期就更是群星璀璨。
这时的反理学思潮已成燎原之势,一个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前的‘异端’思想活跃期也在孕育。
有差别的是,这边还没爆发,就被外来的一场大雨给浇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