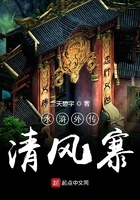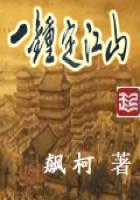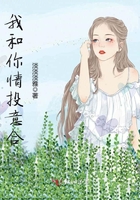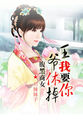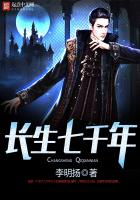钱谦益与姜洛对视一眼,也是很快的将头微微一偏,不去看对方。
他十分瞧不起这个满嘴歪理邪说的商贾之子,也依然有将对方驳倒批臭的打算在心中酝酿。
只不过大儒刘宗周的态度十分反常,竟对此子莫名其妙的透露出几分欣赏意味,因此他即使鄙夷和愤怒姜洛的言论,却也不能不给刘宗周面子。
虽说自古以来,文人相轻。
但实际上也要看对谁。
下层社会的文人之间有了矛盾,顶多你用之乎者也骂我一句,我用者也之乎损你一番,做些嘴上占便宜耳朵吃亏的无聊事,却不会伤筋动骨。
但他和刘宗周都是上流社会的上等人物,不要说两人有交情,就算是已经形同陌路,也决不能轻视或挑衅。
不然一但起了冲突,凭借各自的名望、地位和能调动的门生故旧,那就与神仙打架没什么区别,极容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双方而言都是巨大的伤害和牺牲。
所以钱谦益哪怕已经有些心生不满,却也不得不克制自己在刘宗周表态后尽量三缄其口,这并不是出于对刘宗周的畏惧,更不是他的性格随和,而是他的理智要求他这么做。
大儒与名士之间,互相成全,强强联手,才是正道。
不过钱谦益也认为,自己既然如此为刘宗周的颜面着想,那刘宗周也理所应当的要顾及到自己的威望。
刘宗周不知为何任由姜洛胡言乱语而不加以制裁,自己对先前之事虽然也可以既往不咎,但姜洛如果胆敢再次肆意妄言,那自己作为江南文坛领袖,照样不能坐视不管。
想来那时刘宗周也不会一而再的对自己加以干扰。
……
高挑身量,清瘦脸庞的刘宗周已经六十多岁了,虽未有老态龙钟之像,但精神到底不比壮年,自然也就不可能注意到姜洛与钱谦益两人的小动作。
“确实如此。”
他顺着陈子龙的话点头称是,一开口,暗黄色的脸上就皱起布满眼角腮旁的褶纹,让人看着笑眯眯的十分和善。
“只因一个人在独处时最容易放松戒备,从而会把自己最真实的本性不经意间表现出来。
而人性,是有恶的,所君子必慎其独。
也就是即便在独处的环境下,都要严于律己,从内心约束自我,使本心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有一种至诚至善,天青日白的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真心的体现。
真心虽说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性向善,只要时刻保持真心,人性便能时刻向善。
现在虽然世道大坏,但只要真心不变,人性依旧,那就有挽救的希望,所以救世必先要救心。”
最后,他正言正色的强调道:“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镂。”
果然是大儒!
刘宗周最后一句可谓是点睛之笔,使得屋内众人思绪激荡,左摇右晃,俱都露出一副欣然受教的表情。
连钱谦益也都颔首抚须,显然对这番道理颇为认同。
唯一的例外就是姜洛,此刻他竟眼观鼻,鼻观心,安安静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全无与屋内众人一般感同身受的样子。
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些人从这些话里到底受到了什么启发和教育?
既然世道大坏,刘宗周想要凭思想振奋人心,那就要用醍醐灌顶般的震撼言论将世人惊醒,或者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深刻忧思使人们彷徨,从而有朝不保夕之感,去做那舍死忘生之事。
姜洛知道这些人里面很多都不怕死,但他们想做事又没个紧迫感,慢吞吞的在温水里泡着,等到天下鼎沸时便一死以明其志,结果就跟刘宗周这不温不火的言词一样,对国家并有没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
这还真不如后世运动中打倒某某某的标语,与夹杂着脏话的声讨口号更能调动人的情绪。
虽然是洒狗血,简单粗暴,却好歹会比这样更有效一些。
不过姜洛想想之后也随即了然,凭刘宗周博学好古的才识,应是跟自己一样,是喊不出‘我大明以前如何如何,现在是怎么怎样,以后要哪般哪般’的话语的。
虽然曾经辉煌过的民族永远不会沉沦,但非要牵强附会说这是种族主义的功劳,则大可不必。
而且动荡时期百姓参与其中的大运动,其主体学历普遍较低,甚至多为文盲,是典型的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的智商上限取决于群体内智商最低的那个人,即使有较为理智的人处于其中也会为了获得认同而抛弃是非。
因此整个群体的智商就会严重拉低,变的极度无知和疯狂,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就能让他们愤怒到头脑不清醒。
但刘宗周宣扬思想的受众却都是读书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精英群体。
他们是不会相信那些简单肤浅和没有逻辑性的话语的,甚至一种思想若与仁义道德不挂钩,他们还会怀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观念而拒绝接受。
这种刻板偏见,是当今精英群体与后世的不同所导致的。
在道德至上、道德唯一的教化下,他们的头脑过于僵化,过于保守,习惯把一切实际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去理解,并只从儒家思想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基于这种文化习惯,一个人创造了一种学说,若不假借儒家之名,或者直接说这就是孔孟所创造的,自己不过是刚刚发掘体悟出来而已,那就很难在这些读书人当中散播流传。
当然,也不是什么学说都能往儒家身上套关系。
它首先必须要符合道德范畴,甚至要跟理学一样,宣扬要打造一个把道德作用发挥到极致的所谓完美世界,才能有机会为儒家殿堂添砖加瓦。
像是利益至上、为了变强大可以残忍嗜杀、为了生存可以苟且偷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凡此种种言论就与孔子孟子的形象极不相符,因为圣贤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正直的读书人也就绝对不会认同。
既然现实如此,刘宗周不管是真正表里如一的儒学大师,还是不得不顺应这种规则,因此哪怕他时刻挂在心上的家国天下现在正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他也不能表现的状若癫狂,而必须心平气和的,不脱离道德范围的把事情说明白……
而当代文人群体的这一特性在姜洛看来,其实是很容易被人利用的。
因为仁义道德未必就不会骗人,大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未必就都有圣贤的思想与智慧。
比如说是起于董仲舒,完成于朱熹的三纲五常之说,这明明就是他们自己发挥创造出来的社会生活规范,却非要假借托词说是继承于孔孟。
熟不知,他们过分甚至极端强调的愚忠愚孝文化,恰恰就是孔孟所不认同的。
三纲五常要求臣下对君主,子女对父母,唯一明确的态度就是忠孝,说什么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也没有不圣明的君主。
从而把孝曲解为对父母的百依百顺,对君主的绝不违逆。
而孝字当先,其它因素如社会规范中的是非,判断事件善恶的标准,则在忠孝文化内都可以不予考虑。
不顾是非善恶而绝对服从?呵。
孔子可从来没有说过,天下的父母做什么、说什么都对,做子女则必须无条件服从的话。
有反抗精神和大丈夫气概的孟子要知道这事儿,也非得把桌子都给踢翻了不可。
因为儒家先贤是着重研究过人性善恶的,不说讲人性有恶的荀子,就是提出性善论的孟子也只说了人性向善而没说人性本善。
既然不是本善,既然君主父母首先也是有血有肉有喜有怒的人,那他们就不可能一定都是向善的。
不一定都是向善的,就会有邪恶的。
试想邪恶的君主逼着臣下去作恶,那也要去做吗?
邪恶的父母逼着子女去杀人,那也要去杀吗?
这些邪恶的要求也要绝对服从吗?
三纲五常说:君主有过错,做臣下的也只能柔声以谏,不能触怒。而且出于忠孝原则,还要对外隐瞒这君主的罪责和过失。
孟子说:君主如有大过,臣下谏之,谏而不听,易其位。如遇桀纣,诛灭之。
‘柔声以谏、不能触怒。’与‘易其位、诛灭之。’,两者根本不同。
文人们却不多加思考,听人说是继承自孔孟,便趋之若鹜奉为真理,结果不但养成了可耻的奴性,就连灵魂都被人给骗了过去……
华夏从古至今都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但它整体的地理环境却又十分恶劣,因此就需要比其它地方的人更苦、更累、更加强调纪律才能够生存发展。
像是黄河泛滥,波及范围能北达天津,南抵江淮,纵横几万里……人们若不相濡以沫,众志成城,就很难合力对其进行有效治理。
而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就更需要强有力的执政组织。
这是儒家文明形成并最终独尊的核心根本,也是政治制度必须从封建走向集权的初始原因。
但谁能想到,本朝集权之后就开始皇权专制,结果为了维护皇权专制,不但百家思想被彻底罢黜,儒家自身也被篡改的面目全非。
及至后来的大清走向君主独裁,并造成全民奴化,使中华思想尽去精华,只留糟粕……
导致这种历史大退步的始作俑者,是谁?
朱元璋……
辅助朱元璋进行皇权专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是理学……
确实,朱元璋不是理学的发明者,创造理学的那些人也未必就是坏人。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种群体,说我们创造一种社会规范,创造它的目地就是为了骗人害人。
没有这样的。
哪怕是经常武装暴动的白莲教,不也说自己是为了普度众生?
理学的创造者,或许只是太相信道德作用,同时又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又或许是这些创造者本身只有道德,没有人性,所以才会心理变态的喊什么‘存天理,去人欲。’
但是他们喊就任他们喊吧,统治者不用,他们喊破了喉咙又能怎么样?
就像法家制度,哪怕它再有效率,再有吸引力,而统治者不敢用,它也不是不复存在了?
可朱元璋却是将这种学说钦定为官方思想的。
他不但用了,还是有目地的用……
姜洛面色平静,旁人看不出什么异常,但他自己却早已是心猿意马。
那因为刘宗周一番话而产生的联想,让他搭在双腿上的手掌不由自主的渐渐收拢,握紧……
“临渊,对救世之道,你可曾想过?”
刘宗周有意留下姜洛,本就怀了考量对方才具的心思,此刻见他对自己的话无动于衷,只是呆呆的坐在那里目光出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便出声询问道。
众人也随着这一问,再次集体的把注意力放到了姜洛身上。
不少人的眼睛还都透露出复杂的含义。
他们想不通蕺山先生为什么对这人颇为青眼,即使对方才识不凡,但其说的那些现在也不过都是纸上谈兵罢了,不值得如此吧?
终于又轮到我上场了……
姜洛收住思绪,望向刘宗周。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孟子气势磅礴的话语在脑子里隆隆作响,使他消除了心中面对大儒的最后一丝胆怯。
他微笑着站起来时,已胸有定见,在众目睽睽下,不但显得从容自若,竟还不答反问道:
“自然想过。但,蕺山先生可知世道为什么会大坏?又该用什么方法解救?”
嗯?
钱谦益眯起了眼睛,望着姜洛的目光霎时间就变的冰冷。
像是陈子龙、夏允彝、黄宗羲等对姜洛印象还算不错的人亦都是诧异的倒吸口凉气。
其他人也都感到惊讶,继而就是愤怒,暗道这人是疯子吧?
对蕺山先生也敢如此狂妄!
作为当事人的刘宗周自然也知道姜洛这句话不是为了投砾引珠,而且对方的语气也实在没有请教时的谦卑。
但他却没表现出什么。
他虽然有时会正直的让人畏惧,但秉性和脾气其实都很好,虽然不至于‘好’到唾面自干的程度,可姜洛也毕竟没有冲他吐口水,所以他只是把姜洛的这种语言语气,当做是年轻人的意气风发。
尤其重要的是,他心中是有那么一点欣赏姜洛的。
他是大儒,也是大教育家,他的后半生点拨指导过的门生弟子无数,因此也阅人无数。
凭借这一点教育经验,他知道那些愚笨无能、只会唯唯诺诺的年轻人很难教,即使他付出比对待其他弟子更多的时间去培养,得到的结果往往也仅是可以让其独善其身。
而像姜洛这种发扬蹈厉,自身又具备个人思想与观念的人就不一样了,自己往往只要在其人生旅途中的节点上简单指明一下方向,就有可能让这人成为兼济天下的贤才。
而他,是可以包容有贤才潜质者的懵懂脾性的。
他观姜洛之前言行,已了解对方性格中有好为人师,擅长雄辩的一面。
这会儿打的主意也必是为了引出自己的观点,再辩驳自己的观点。
在自己面前班门弄斧?
有意思……
往常或是与理学巨子激烈的切磋学问,辩的对方哑口无言,或是对当今天子也敢说‘人心为祸之烈,其它不过小节’的刘宗周,此刻却像是面对一个自己喜欢但又顽皮不顺从的幼童一样,突然感觉到饶有兴致。
等了一会儿之后,他语调柔和的说道:
“只因人心有贪私二念,二念一起,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世道因此而坏。
至于解救方法……
先前说的治心、慎独都是我之主张的前提。目地,则是要求人人都回到三纲五常的规范当中。
只要人人克制私心贪念,各安本分,世道也就能变乱为治。”
他一说完,在别人还在咀嚼其中道理的时候,姜洛却连弩似的不留间隙,紧跟着就答道:
“含糊不清,听着好像很高深,但却根本没说明世道大坏的真正原因,晚辈因此对先生的解救方法也不敢苟同。”
刘宗周笑而不语,他没有因为姜洛的唐突而感到生气或是不满,只是好奇对方为什么有这么好斗的性格。
而姜洛既然如此表现,那接下来,暂时也就用不着自己开口了。
果然,姜洛话音刚落,一个高高壮壮,面向粗犷的中年男子登时离座而起,对其愤怒道:“你有没有一点对尊长的敬重?在家中没有学过礼数吗?”
“你是……”
姜洛看向他,原本勾起的嘴角慢慢收回,有些迟疑的问道。
这是之前屋外,继钱谦益和黄宗羲之后第三个插话打断过自己的人,那时的语气就很是不善,只是书院山长并未给自己介绍过他,所以还不知叫什么。
“哼。”
中年男子鼻中冷哼一声,却没有要自报姓名的意思,脸上则是充满了不屑的表情。
“这是冒襄,是复社大名鼎鼎的四公子之一,曾被文苑巨擎董玄宰称赞为能点缀盛明诗文之景运的冒辟疆。”
黄宗羲见场中气氛又因为姜洛的言语变的有些剑拔弩张,而他既是刘宗周的弟子,也比冒辟疆早入复社几年,自恃能居中调和,就站起来代为介绍道。
他出于好心,还特地着重讲了冒辟疆的身份,以免姜洛不知轻重,没由来的得罪许多人。
同时他心中也十分纳闷儿,姜洛的才识是他亲眼所见,确实不凡,但怎么在人情世故上就如此不堪?
不,不对。
因为按照常理来说,姜洛既有这种才识,那早就应当在文人圈中扬名了,不管是善名还是恶名,反正应该被广为人知才是。
而自己之前从未听说过金陵才子中有姜洛这等人物,想来是他把心思全部用在了做学问上,不大出来走动,所以不了解这些社会名流的身份与地位,才会有这么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
黄宗羲像是突然发现觉了什么似的,开始暗自思索。
“哦,原来是冒绳绳啊。”
姜洛恍然大悟,直接把冒辟疆那又特别、又可爱的乳名给叫了出来。
呃……
黄宗羲刚刚对姜洛做出的判断,在这轻飘飘的一句话中瞬时烟消云散。
知道冒辟疆小字叫什么的人可不多,他竟能脱口而出,这难道是不经常出来走动的人能了解到的?
噗!
夏允彝嘴巴一咧,又赶紧用手捂住,怕别人看出他在发笑,就扭头装作左顾右盼的样子,正好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偷偷的笑,而一旁坐着的陈子龙则在对他做嘘声的动作。
“这!你!”
冒辟疆被看着小他十来岁的姜洛直接叫起乳名,先是惊愕,然后就又气又恼,激愤的说不出话来。
姜洛却不管这些,似笑非笑的冲着冒辟疆问道:“听说你年轻时喜欢借古讽今,经常写骂秦桧的文章来暗指魏忠贤?”
他先前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所以话语上还有的放矢,哪怕是唇枪舌剑,也会尽量把内容调整到对事不对人的角度。
而现在他知道了这些人的底细,骨子里那种顽劣乖张的脾性就又冒了出来。
说什么才子文豪,不过就是些有些文采的书生而已。他们那舞文弄墨,把事情描述的天花乱坠的本领,自己还不屑于拥有呢。
尤其是这冒辟疆,什么复社,什么四公子之一,不过就是个屡试不中的落魄文人罢了。
虽然他也敬重这些人里面的其中一部分,但诚如他之前所想的那样,既然大祸将至,既然要个人顾个人,那就不要在意这些表面上的客套了,赶紧给自己打下名声,并由此获得自立资源才是最实际的。
同时他也相信得罪君子总比得罪小人好,既是读圣贤书的文人,那未必会因一时之争而记恨并报复自己。
就是真有受不了气,报复心强的,可等自己得到家主父亲赏识之后,那也不怕什么。
自家虽是商贾,但家中生意却担着为这南京城中一位国公爷揽财的勾当,在可见的有数几年太平时光里,南直隶地界上是没几人敢得罪那位世代勋贵,又专横跋扈的国公爷的。
“大奸大恶之辈,自然该骂!”
冒辟疆从被叫及乳名的气恼中摆脱出来,心中的那股子浩然正气再次占领智商高地,果断大喝道。
“那怎么不敢直接骂魏忠贤?”姜洛面露讥讽。
“我自然敢骂!”冒辟疆忽然脸色涨红,可仍旧强加掩饰道:“那等祸国殃民的小人,我有什么不敢骂的?”
“可天启年间怎么不敢?”
姜洛先是疑问,然后露出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自问自答道:“哦,原来也是欺软怕硬之辈。那是不是今日我若也有魏忠贤一般的权势,你就不敢与我针锋相对了?”
冒辟疆在这么多年里,一直都为自己当初敢于对魏忠贤指桑骂槐而自得。
因为在魏阉掌权的那个时期,多少人都趋炎附势,又有多少人都只敢怒不敢言,而自己担着身家性命做出那等壮举,还不值得自豪?
但如今让姜洛一说,又确实脱不了欺软怕硬的嫌疑,他无法自辩,只好恨声道:“自比阉人,败类!”
“嗯哼……”
钱谦益清了清嗓子,准备发言。
刚才他就想训斥姜洛,此刻见对方表现的如同恶棍一样让冒辟疆吃瘪,就更是按耐不住了。
“姜临渊,这里是书院,是讨论学问交流思想的地方,不要任由你逞口舌之快的市井!你既说蕺山先生讲的含糊不清,那你就把你对世道大坏的看法拿出来。我倒要瞧瞧你有什么能耐,敢如此目中无人。”
钱谦益在刻意引导话题。
因为姜洛那种如同地痞无赖骂仗一样的锋利言辞他并不擅长,也碍于身份不耻于那样。
所以他要把话题引回到学问,以及个人的观念上面,再从自己精通的领域里进行批驳。
姜洛却无所畏惧,他淡笑着看了一阵儿钱谦益,然后说道:
“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动。”
众人皆是一怔,因为姜洛念的这段话,乃是本朝开国太祖朱元璋研究元朝灭亡原因时所说的,在而今读书人当中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这算是什么?剽窃?
不过等他们再一细想此话之后,又都觉得这似乎与本朝世道大坏的原因有共通之处。
本朝不就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君为臣纲的立国之本,导致皇帝荒于政务,大权旁落,朝臣操弄权柄作威作福,使天下失去凝聚力和约束力而致大乱吗?
看来姜洛这是要以前朝的灭亡经验作为论证依据了。
果然,后者也如他们所猜想的那般继续说道:
“我们可以把这里面的元改为明。
太祖对元朝灭亡得出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元以宽纵失天下。
本朝亦是如此。
只不过前朝权柄落于宰相权臣,本朝却多是被宦官所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