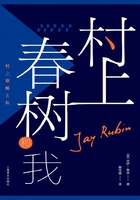要过很多年,直到读到那篇《毛家湾的女主人》,我才知道,原来毛家湾还这么有名。
我说的毛家湾,当然不是京城里那处宅子,而是毛家庄前水面连绵的水湾。
毛家庄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孤零零的独处者。它四邻不靠,周围三四里地范围内都没有村子,远远地看去,只能看到一些树影和房檐屋角。而村子周围,又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当初,我们这些刚上初中的孩子,边打听边拐弯抹角地找到这个村子时,心里着实凉了半截。这还是人间吗?地里白花花的,长的庄稼跟草差不多,稀稀拉拉,还不如没有看着顺眼呢。更重要的是,这里好像到天边了。一个同学甚至用到了刚刚学到的一个词——发配——咱们就这么给充军发配到边疆来啦?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不毛之地。
也难怪,在我们的印象里,村子都是紧靠着的,不过半里一里,就是一个,站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邻村里走来走去的牛,吃草的羊,做饭的炊烟。邻村里吵架,或者来了马戏,甚至来了卖豆腐的,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你回家拿个碗,再出来,那卖豆腐的也就来到村边了。而现在,这毛家庄好像连个依靠也没有,孤零零地悬着,让人心里空得慌。但是,万般无奈也好,心灰意懒也好,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里是联中,我们的初中就在这里读了,也只能在这里。
毛家庄的房子稀稀拉拉的,跟盐碱地里的庄稼相似,从东到西,战线拉得很长,南北却很单薄,像切得薄薄的一片豆腐,不知道有什么讲究。让人感到好奇和惊讶的,是村前有一条大河似的水湾,这就是毛家湾。毛家湾随着村子的排列,也长长地拉出去,却又宽窄不一,时断时续。我们去的联中学校,与村子隔着毛家湾相望,像一个孤岛。毛家湾中间,有一条土坝,将学校和村子连了起来,也方便村里人去学校南面的庄稼地。
整个毛家湾的南面,又是一片辽阔的洼地。洼地仍然是盐碱地,除了零星的红荆条和紧贴地皮的芦扎,就是白花花的碱壳,要么一层皮一样半张起来,要么是白色的粉末,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刺眼。这片洼地和再往南的庄稼地有个明显的界限,跟半堵墙一样,相差多半人。我们骑了自行车,顺了斜坡,一个俯冲,就冲下来,轻松得很。夏天的时候还好,春秋却很艰难,因为这盐碱地很特殊,一阴天下雨,地里的水分多,动不动就跟淤泥一样,却不陷人,而是如橡皮胶一样的地皮,踩上去上下忽悠,吸力很大,尤其春天,走路要比平时费一多半的力气。
学校在毛家湾的南面,紧贴水边,地基却很高,有三四排房子,老师也很多。因为与村子隔了毛家湾,村里人没事就轻易不到这里来,这就显得学校非常安静。
好在那片水很喜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几乎没有人见过这么大的水湾,跟个小海一样,那水绿油油的,平时稍微有点风,那水就有细小的波浪翻滚,甚至在岸边冲起白沫,还哗啦啦作响,既然见不到海,这里也算能满足我们对海的向往。
我们的语文老师姓范,讲课很幽默,思路也跟小学的老师显著不同。他时常带我们到野外去实地作文,我们欢呼雀跃,兴奋中写作文就有了新鲜的东西。这个时候,毛家湾就时常派上用场。春天了,水暖花开,杨柳依依,春水激荡,鹅鸭潜水,我们就去瞪大了眼睛,来一篇写景作文;夏天了,偷偷找个偏僻的地方下水,过一把玩水的瘾;秋天鱼都肥了,村里有人找闲下网打鱼,我们就去看个热闹;冬天一到,水面结冰,且越结越厚,村里的学生就直接从冰上来往,顺路还抽个陀螺,滑几圈冰。这些,老师都是允许的,而且,还把写得生动的作文拿到课堂上讲读一番。所以,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喜欢上了这个“蛮荒之地”。
范老师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课外书,他家的书很多,都拿来给我们看,《动脑筋爷爷》《十万个为什么》《中学生》……每天上语文课,我们几乎都处于激动得满脸通红的状态。他脾气还好,有几次,放学的时候大雨,他不光把家里的塑料布、床单、门帘都带来,还发动毛家庄村的同学回家拿雨具,让我们觉得,在这里上学,算是来着了。
由于老师的默许,我们就有了很多的空闲时间,可以去水边背课文,说闲话。我的一个新朋友,小名叫秋收,名字新鲜,更新鲜的是他哥哥叫麦收,让我觉得他爸爸很有水平,起的名字这么好玩。秋收从另外一个学校转过来,他原来是跟着姑姑的,只是她那里没有初中,就又回来了。他知道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他弟弟丰收,从小喜欢吃土,打了多少回也不管事,尤其喜欢吃炕土,被烧得焦脆的那种,谁家换炕了,就去抽冷子偷一块,藏到一边,跟吃锅巴一样,嘎巴嘎巴的,吃得很香甜。找医生看了,说是缺营养,但家里穷,没有营养,唯一的法儿就是全家人严密监视。“不管用,吃够也就不吃了,你越不让他吃,他就越馋。”这是秋收的意见,他很想得开。多年之后,我再见到他弟弟,靠贩运粮食,据说资产已经百万,而且很富态的样子,我就想起秋收的话。估计,他现在不是营养不够,而是担心营养过剩了。不知道他现在贩运粮食发家,是对小时候的一种心理补偿,还是一种巧合。
课文背累的间隙,秋收还告诉我,说再往东几里地,那里的人说话zh、ch、sh和z、c、s不分,说话很有意思。他听村里人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人去赶集,回来给人讲,他啄(昨)天,买了二斤冲(葱),山(三)斤涮(蒜),一瓶子老怵(醋)。我感到非常好奇,说离得这么近,为什么他们说话那么难听,你们就没事呢?他很得意,说村里的老人说了,是毛家湾的水好,养人,那些人那里没有这么好的水,舌头就不灵便,说话拉不直舌头。村里人对这湾水看得重,是村里的风水,谁也不能脏了。你看看,村里没有一个人敢往水里倒脏东西。随后他神态很严肃地说,多少年了,老辈的人都这么传下来的,要不是这么保护水,我们村在盐碱地里是待不下来的,早就给“碱”跑了。
由于离家远,我们中午不回家,而是拿了干粮在学校里和校长搭伙。校长住校,个子矮小,说话有点咬舌,但是脾气好。学校里的闲散地,都被他种了蔬菜,我们沾他的光,他吃什么,我们就跟着吃什么。他办公室门前有一口压水井,我知道这水紧靠后面的水湾,有“风水”,沾灵气,就常偷偷使劲地喝。校长就很奇怪,怀疑我得了什么病。弄得我喝水的时候跟做贼一样,要先偷着看看他在不在。
校长也带课,教我们美术。他本身不会画,而是教给我们大量描画的方法。有几个家伙入了迷,专门画小画书上的武将,开始印着画,后来就脱了纸,在八开的大粉连纸上画,那武将骑马、抖枪,神态英武,跟真的一样。后来,其中的一个一直迷到初中毕业,耽误了学业,没能考出来,就专门去学画画,最后去了济南,做舞台设计,成了学校的骄傲,村里的人物。
这个村里的同学名字都很接地气,比如,有个嘎子,有个河水,还有个马路。据说,马路的母亲待产时回娘家,有了感觉就赶紧往家赶,最终生在马路上,就给了他这个名字。他的弟弟,干脆就叫土路了。他还有一个哥哥,叫文革,很气魄的样子。
我们上学的时候,也要走毛家湾的边。先是一片浅水,里面种满了柳树,树台子很高,露着红色的树根。水边上长满了水草,我们时不时地,可以看到拉蛋的鸭子和鹅,将雪白的蛋下在草丛里,于是不顾水冷热,脱了鞋冲过去,谁抢到是谁的。印象里,毛家湾的水从来就没有少过,似乎永远都那么多。这个村里的人浇地非常方便,从毛家湾里引出来很多水沟,沟里的水充足,到时候把机器拉过去,抽水就是了。有这么多的水,却又有那么多的盐碱地,我感到很奇怪,问过同学,他们说,现在的盐碱地已经很少了,以前更多,治理盐碱地很麻烦,要先撤地,把盐碱的那层去掉,用新土,然后用好水浇,一年年地改,慢慢地就改过来了。你们来的路上,那些长得稀稀拉拉的庄稼地,就是正在改良的盐碱地。
就在那一年,我忽然对一个女同学有了奇怪的感觉。她喜欢穿浅黄色的上衣,上课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浅黄色。见不到她就想,见到了却紧张得冒汗。尤其回家的路上,喜欢跟着她的影子走,远远地,只要看到那片浅黄色,心里就一涌一涌地起波浪,跟毛家湾的水一样。我害怕了,知道这么下去非毁了不可,就在日记里把自己大骂一通,从古代的殷商皇帝,到三国的董卓与吕布,一个个数一遍,又把坐怀不乱和关羽的故事反复地温习,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惩罚和警告自己。
好在不久,那女同学竟然转学走了,我才算脱离苦海,渐渐地恢复正常。后来再想到她,却再也记不起名字,想起来的,只是毛家湾阔大的水域。那水面波光粼粼,好像撒满了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