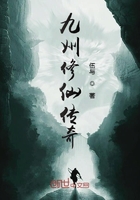夜渐深,天上的星星稠密起来,田间道路似乎有了点白亮。悄无声息的一行人路前行,时间不长前方出现黑黢黢的一个村庄。蓝彩云压嗓儿问奚长胡:“老人家,前方就是范锭杆村?”奚长胡低声回话:“是。”蓝彩云又问:“您到过范多文的家吗?”奚长胡说:“到过。前几年他没拉杆子的时候,我到他家买锭杆。他家位于中街,向阳大门,上好的大院。”蓝彩云细问:“南五团到底多少人,多少枪?”奚长胡说:“人们经常见的就五个人,一短两长三支枪。听说最近又买了几支,不知道是长是短。”身后有人低声补充:“我见过,一短二长。范多文配成双匣子,另两个的笤帚疙瘩换长枪。”蓝彩云又问:“他们的枪法怎样?”这是她最为关心的事情。有个名叫奚小宝的,一笑发话:“他们的枪法十分了得!有多么厉害呢?听人说,有一天范多文带着手下四员大将赶集敛款,路过一片空旷草场。也巧,天空有一只盘旋的老鹰,赶起一只兔子来。兔子跑,老鹰扑,眼看那老鹰抓着兔子。范多文一声喊:‘哥们,咱们一枪打俩,也好显显本事。’背长枪的四人齐声说好,于是两短四长一齐朝老鹰兔子开火。乒乒乓乓,吓得路上人们捂耳朵,那只老鹰赶忙飞上天。五人跑到跟前一阵寻找,觉得打只兔子也很好,不料找了半天连撮兔毛也没有,只是找到一只麻雀。打老鹰兔子怎么打下麻雀来?原来那麻雀不是他们打的,是一群麻雀在草丛觅食,听到枪声赶忙飞起,一只麻雀撞到子弹上。人们编溜:
瘸子跑步——乱点,
瞎子打枣——胡抡,
五团打枪——瞎碰,
结巴说书——胡云。
“大姐,老百姓害怕南五团,是乡下人一盘散沙,手中无枪,抗不住五人结伙。如果结起伙来,手中有枪,南五团算什么?早就除掉那一害!”
蓝彩云不语,心中盘算:乡间民众不是不想抗日,不想灭匪除奸,而是无人组织。无人组织,一盘散沙,几个打枪瞎碰的地痞流氓都惧之如虎,何谈抗日!今晚到南五团团部送赎金,去会这个范多文,真乃天赐良机。五人六枪算什么?何况她身边有这多帮手。如能趁此机会把南五团打掉,在太平庄一带定会引起很大的震动,鼓舞乡间广大的民众。今后组建除奸队,是个立足点。
蓝彩云谋划行动计划。她问奚长胡:“老人家,范多文见过酆三妹没有?”奚长胡思虑一阵:“没见。酆三妹自从过门以后,除去大年初一给本家族长辈拜年,平日不出家门。就是走娘家,她家有辆棚子车,出门钻车里。”一听这话,蓝彩云觉得可用酆三妹的身份进去赎人。不料奚小宝便插言:“范多文不认识酆三妹,范多文的狐朋狗友不一定都不认识酆三妹。那伙人都是尿尿冲墙角的狗杂碎,专爱打探哪里有美女,谁家的媳妇俊。他们这次绑黑小,说不定是打酆三妹的主意呢!”
没人反驳。范多文绑票的因由很多。蓝彩云立即打消充当酆三妹的念头,另想对策。她觉得奚小宝是个人才,对本地情况熟,组建抗日除奸队,一定把他拉上。想到这里,她便轻声问奚小宝:“你摸过枪没有?”奚小宝说:“摸过,不过我摸的不是洋枪,是打兔子的土枪。我姥爷打兔子,教过我怎么放。”马上有人问:“你打着兔子没有?”奚小宝说:“打着半个。”有人呸:“吹牛!打着就是打着,打不着就打不着,半只兔子怎么打?”奚小宝不慌不忙:“说打猎你们外。凡是打猎的人,都带着猎狗。我一枪没把兔子打死,那只兔子翻了个跟头又往前跑,猎狗跑去把它追上。”
眨眼来到范锭杆村头。蓝彩云说:“停一停吧。”众人站住,不约而同听她指挥。蓝彩去说:“咱们到范多文家门前,不能全进院,要在大院门口留两个人。为啥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咱若是全在院内,范多文呼喝一声关大门,咱们外边没人接应。”众人点头说是。蓝彩云又说:“进屋之前,在屋门外也得留两个人,防备他堵了屋门咱出不来。”众人又点头称是。奚长胡更是敬佩,若不是蓝彩云提醒,他真想不到这些事情。
议罢,奚长胡带路进村。范多文的瓦门楼十分显眼,奚长胡轻步上台阶,故意壮胆一声响咳,拍响那副黑漆木门。门内一声呼喝:“谁?”奚长胡说:“太平庄的,送赎金来了。请您报告团长。”门里喊一声:“等着!”接着传来朝内院跑动的脚步声。时间不长,跑动的脚步又返回,而且多了一人的脚步声。一声喊:“进来吧!”抽开门栓,敞开一扇大门,门内两人各持一条长枪。
蓝彩云留下两人同门卫搭讪,同奚长胡一起,带另二人进院。转过影壁,前方是座青砖大瓦房,前出厦,高月台。月台下两只长枪岗哨,是临时设的,显示团部的威严。蓝彩云示意奚小宝,奚小宝立即拉一把身边的汉子停步。蓝彩云让奚长胡前边走,登阶上月台,奚长胡两腿直哆嗦。好在台阶不高也不宽,他伸手扶着花格子扶栏。上得月台,见房门大敞,房内烛光明亮,冲门摆一张方桌,后一把紫漆圈椅。范多文椅上端坐,桌面上放着两把匣子枪。桌子周围别无座位,来人一律站立。见这阵势,奚长胡两腿更软,忙弯腰鞠躬,说话嘴唇不由得哆嗦:“团长……我们……送赎金来了。”
说罢,奚长胡从怀里掏出十亩地当来的50块大洋,两手抖抖地放在范多文面前的桌面上,后退一步等对方发话。从来人进门,范多文就故意绷着生气般的一副脸面,眼皮没抬,以显示他居高临下,瞧不起任何来人,仿佛来送赎金也对不起他。见50块大洋放桌面上,他慢慢地抬起喝酒过量、已经发红的泡子眼皮。就这时候,他发现进房来的还有一个人,竟然是位十分漂亮的女子。南五团虽然不是采花团,可是到手的花儿不能不采,他一笑,朝蓝彩云问:“你是谁?”蓝彩云故作胆怯之态,退半步道:“我是来领人的。”范多文听人说过,黑小有个俊俏媳妇,名叫酆三妹,只是他没见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想不到今天送上门!范多文好是高兴,又一笑:“真想不到,你酆三妹亲自前来。”蓝彩云原本想装酆三妹,经奚小宝提醒,怕假装不成反露马脚,便直言道:“我不是酆三妹,是酆三妹的姨表姐。我替表妹领人来了。团长,赎金送来,我妹夫呢?您放出他来,我领走吧!”
范多文顿时麻达脸。他眼珠子一转:“你不忙走。走了好远的路,人困马乏的,我请客,喝壶酒吧。”便要招呼手下人员。蓝彩云怕他招呼人来不好下手,抢先说:“不了,我表妹在家着急呢。人在哪里?给我们吧!”动手之前,她得先见到黑小。范多文觉得无论如何,人是捂不住的,便直截了当说一句:“有人买他的命,我把黑小戳到村外井里了!”说这话时一副凶相。奚长胡首先惊叫:“啊?范团长,你怎能这么做!”急得跳脚。范多文两眼一瞪:“怎么不能!”奚长胡拍屁股高叫:“我们这不给你送钱来了吗?这可是你要的数!”范多文冷笑:“送钱好哇,我收下;人我也给,你们自己到村西北那口井里捞去吧。”奚长胡一劲儿大叫:“不行,这样不行!”范多文手拍桌面,开口就骂:“妈那疤,怎么不行!也想让我把你戳到那口井里?”奚长胡急了,他知道领不回黑小他不仅无法向酆三妹交待,也无法向全家族交等,便冲着范多文放胆高喝:“就是不行!按道上的规矩……”一副拼命的架式上前来抓。范多文是让人抓的人吗,立即伸手拿起桌上的匣枪:“你敢!我看你老小子活够了,来人哪!”
听得范多文呼喊,房门前月台下那两个手提长枪的哥们,立即应声:“来了!”他们两人原先在茶馆、包子铺当过小伙计,只因一个爱偷钱,一个爱打牌,被茶馆、包子铺掌柜轰出来。两人觉得憋气,一个夜间偷偷潜回茶馆,撬开店主的钱柜。店主发觉,提棍子追来,他一刀子把店主捅倒,投范多文门下。另个也是夜间潜回店内,只是没有撬柜偷钱,而是背出店主闺女,先奸后卖。虽说二匪恶行不一,却都有当伙计的职业习性:“紧咋呼,慢动弹。”听得呼喝立即回应:“来了!”其实脚还未动。这声“来了!”传进房内,范多文洋洋得意。
即然黑小已经被害,蓝彩云明白不能再等,必须在外边的人“来了”之前动手。她发句缓言:“团长别急,我这里还有给您的礼儿。”一听这话,范多文顿时异想天开:“有什么礼物?藏到怀里吧!”一副淫邪的目光。蓝彩云说:“您说对了。”伸手掏出匣子枪。范多文立时打一寒战,可是没等他的寒战打完,胸口钻进要命的子弹。
这时,房外也传来两声残叫。原来月台下二匪应声“来了”,转身迈步上台阶时,奚小宝手中的扁担抡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叭”的一声响,正打在一个匪徒的后背。这是奋力一击,来得猛,打得重,那土匪一声“哎哟”便栽倒,奚小宝又忙补一扁担。另一汉子行动少有迟缓,扁担抡得不快,另个土匪已经迈上了两个台阶。这汉子的扁担抡过去,没有打在土匪的背上,而是打在撅起来的大屁股上。虽然疼得那土匪哎哟大叫,嘴磕台阶,可是没有大伤。他忍痛爬起,跑上月台,进房的同时大声喊:“团长,不好……”可他只喊了这么一句,猛然发现蓝彩云的枪口正对他的胸口前。太突然,太意外,一时间惊得他魂飞魄散。他只张口一声“啊?”仰面后跌,撞在砖房的墙角上,顿时流出脑浆。
院门口也没有多大周折。面对前来送赎金的人,门岗根本放不到眼里。他们手持长枪,嘴叼香烟,脚尖打着拍节哼浪当曲:
一更里来呀月东升,
我敲响姐儿后窗棂,
姐儿姐儿你快开窗,
让我爬进你绣房中。
二更里来呀月进窗,
我跟姐儿……
院内突然传来枪声。哼曲的立即止住哼曲,叼香烟立即吐掉香烟。一个说:“不长眼色的死货,又惹团长生气了。”他们以为范多文开枪打人。另个说:“若是真打死了,还得咱俩拖出去。我进去看看。”说罢转身进院。奚小宝手提扁担大步跑来,这门岗立即呼喝:“跑什么?给我站住!”奚小宝不语,快步近前的同时手中扁担猛力一戳,那门岗立即倒地口中吐血。留大门的太平庄人见奚小宝得手,毫不怠慢,眨眼把另个门岗打倒。嚣张乡里的南五团全部报销!
渤海谣:
得势的,别自喜,
害人终归害自己。
别说没人能治你,
雷劈你,雹砸你,
狗咬你,鹰啄你,
天塌地陷埋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