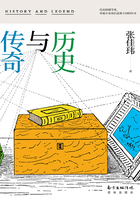蓝彩云让笤帚王把笤帚搭到驴背上,她同笤帚王一起跟在驴后走。她是跑惯路的人,走三五十里路脚不起泡腿不痛。走过一条弯曲的斜插小路,面前出现印有铁瓦大车车辙的大道。又前行五六里路,小老儿朝前一指:“那村就是太平庄。”蓝彩云问:“大叔,这太平庄有啥来历?”敌后工作需要了解乡情民俗。小老儿说:“传说,全真道长邱处机北上,在此路过,发现周围妖气甚盛,便在村东建造了座道观镇妖,起名太平观。由此,村名就叫太平庄。”大叔啊,我去太平庄一带。那里有没有咱的熟人?”小老儿摇头:“没有。我没去过那一带。不过我听媳妇说,她有个姨表姐,嫁到太平庄。”年轻女子大喜:“大叔,婶那表姐叫啥名?”笤帚王说:“小名叫妮妮。离得远,多年不走动,不知她男人叫啥名。”有一线希望也是希望,年轻女子又问:“大叔,您再想想,婶说去过姨表姐家没有,姨表姐家住在太平庄的哪一头。”笤帚王连连摇头:“她没说去过,只说姨表姐和男人都已去世,有个孩子叫黑小。”年轻女子显得高兴:“这么说,黑小就是您的表侄了!有您这个表侄,我到太平庄就有落脚地。
话间,两人到村头。蓝彩云举目,村东果然有座道观。青砖墙,鸳鸯瓦,主殿坐北朝南,东西两廊房,南大门。走近道观,木门敞着,红漆剥落,院内杂草丛生,主殿房门半掩,不见任何烟火,殿门台上雀屎斑斑。蓝彩云一句感慨:“道姑离去,烟火熄灭,想必神也无人供奉了!”笤帚王小老儿一声长叹:“唉,如今这世道……”张口一段溜:
善人不得好,
恶人不受惩,
烧香引来鬼,
谁还把神供!
这话刚落,庄里猛然传来一阵号啕。那是女子撕心裂肺地尖声哭啼,定是遭上塌天大祸。蓝彩云忙说:“大叔啊,您回去吧。街上有了人,您再回返,反倒引人生疑。”笤帚王点头:“也是。您可要小心啊!”说罢提下驴背上的笤帚,穿上扁担,拐向庙后的路。蓝彩云则骑上驴儿,顺街前行。
哭声惊人,街上很快有人聚集。一家有事众人帮,不成文的乡俗。哭声继续从街南胡同传出,人们立即涌向这条胡同。蓝彩云跳下驴来,问街上人:“那是谁哭?”立即得回答:“像是黑小媳妇。”她正要找黑小呢,立即牵驴跟人进胡同。胡同南端路西一家院,院门朝东开,院南边是个树园子,栽着枣树和榆树。蓝彩云将驴拴在那棵大榆树上,见一位大嫂身边过,又问一句:“大嫂,这就是黑小的家呀?”那大嫂惊奇地望着蓝彩云,问:“您是……”蓝彩云道:“我是黑小的姨表姐,多年没有来。那个哭的……”大嫂道:“是黑小的媳妇酆三妹。”
蓝彩云跟随大嫂进院。院子不大,房屋倒很整齐。三间北上房,东西两厢房,南棚连着大门洞。虽然皆是砖根脚的土坯房,房顶上无瓦,但门窗齐整,整个院子严实合缝,无有一处敞漏,可见是乡间既不贫穷、也不富贵、囤有存粮、锅不缺米的殷实人家。哭声来自北上房门前,地上坐着位哭嚎的小媳妇儿,四周一圈闻声跑来的男人和女人。蓝彩云立即快步上前,蹲下身子抱着酆三妹,大声呼叫:“妹呀,表姐来看你了,你这是咋了哇,出了啥事情?”不由得滚出串串眼泪。泪水蒙眼的酆三妹,没有看清蓝彩云的脸面,只听得“表姐来看你”,便扑到她怀中一声叫:“姐呀……”一口长气没有吐出来,竟然身子一挺,昏厥过去。
蓝彩云知道该怎么办,赶忙用她的指甲给酆三妹掐人中。为时不长,酆三妹哇的一声哭,又还过阳来。蓝彩云赶忙招呼身边的几个年轻女人,把酆三妹架房中,百般安慰。直腰喘息的当儿,蓝彩云觉得先要问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迅速扫一眼周围人员,见一位长胡老者急头麻脑不停地辗转,便上得前去道个万福,轻声道:“老人家,我不知应该对您怎么称呼。我是黑小的姨表姐,多年不见,前来看望,不料刚进街,就听到三妹的哭嚎声。请问老人家,我表弟家中,到底遇上什么灾难?我心中明白,也好帮着出个主意。”
长胡子老者一副清癯脸面,凸突额头,长眉花白,眉下眼窝很深,眼窝中一对亮眼睛。他姓奚,是太平庄奚姓人的家族长,因留着一把长胡须,人称奚长胡。只要本家族有事,奚长胡必然出面,而且要代表整个家族做决定。听得蓝彩云问话,奚长胡停住走动,把攥手中的一块纸片抖蓝彩云面前。蓝彩云上眼瞧,见纸上歪歪斜斜一行字:
黑小活命五十大洋送五团
蓝彩云顿时一声“噢”,表情沉重。沉思片刻,对奚长胡说:“老人家,我听到这么一首民谣:‘太平庄,不太平。南五团,害人精。黑无常,采花贼,阎王殿,三虎营。’纸片上写的‘五团’,想必就是民谣中的南五团了。看纸上写的,像是他们绑走黑小,要五十块大洋去赎人。”奚长胡连连点头:“是的,是的。”清癯的脸面现一副震惊,觉得面前这位年轻青女子,张口说出那个溜儿,说明对那些杂七么八的土匪了如指掌,非同一般。蓝彩云又问:“五十块大洋凑齐了吗?”她知道土匪绑票就为要钱。奚长胡摇头道叹息:“我就急这个呢!咱太平庄虽说有几十户奚姓人家,可多是贫穷主儿,50块大洋不好凑。刚才我问黑小家里有多少钱,她说上集卖了两只羊,家里只有5块大洋。我想让人们分头去借,可是人家要的急,限咱今天晚上三更天,准时把钱送到,不然就撕票。保得住人,就得立即凑齐50块大洋!”
蓝彩云当机立断:“老人家,我骑来一头上好的小灰驴,你派人牵了去卖,兴许能值十块银圆。也算我给表弟如急。”奚长胡十分赞赏蓝彩云仗义,却立即摇头说:“不中,不中。天这时候,赶什么集?不等到集上天就黑了。若不……我给你牵到当铺,试试?”蓝彩云立即答应:“好,好,你让人牵去,无论啥条件,咱能拿到钱,就行。”奚长胡怕别人办事不精明,他亲自来到院外,牵上那头小灰驴,直奔太平庄西头的郎家当铺。
太平街西街当铺,面朝大街,黑漆大门,门前蹲着两座石狮,门柱上挂一面菱角形牌子,牌中间一个大“当”字。见奚长胡近前,当铺大当家郎光让离开柜台迎上来,半秃的脑门闪着光,双手作揖满面笑:“奚当家,一向可好?忙活活的去哪里?”虽然客套,却也不失大家身份。奚长胡忙说:“郎掌柜发财!这不,家族中碰上事了,我来当这头驴。”郎光让一听这话收了笑脸,麻达一下油光光的嘴,郑重地说:“不是我驳奚族长面子,是眼下世道太乱,土匪太多,铺子不得不改章程,再也不当驴啊、马呀、牛啊这种牵了就走的大玩意。”奚长胡当头挨一棒,不得不放下身架求人家:“郎掌柜,黑小遭事,急着用钱。无论改啥章程,你也得掏腰帮忙。不是?”郎光让一副关心的样子,探身问:“用多少钱?”奚长胡如实说:“大洋五十块。”郎光让一副惊态:“啊,要这么多?”说罢,他捂了捂半秃放亮的脑门,慢慢地说:“钱,我给你凑,谁让咱是庄乡爷们呢;不过……这多的钱,怕是只能押地。”
郎光让这话说得声音不高,却板上钉钉一般,结实、坚定。说罢,他又摇晃着脑袋长叹几声,似在表明对他这是无奈之举,然后便退回当铺,去柜台里边低头落座,不再瞧当铺门前的奚长胡。面对这样一副再也不能通融的样子,奚长胡深知好话白说,说也无用,当铺从来不会救济危难人,因为他们发的就是危难财。事态紧急,容不得犹豫,然而押地借贷非同小可,必须征得酆三妹同意,于是奚长胡立即返回。
见奚长胡牵回小灰驴,众人便知情况有变。酆三妹听说郎家当铺要她押地,立即哭叫不应。她对奚长胡说:“爷呀,我公公在世的时候,再三嘱咐:‘家里无论多么穷,也不能卖地卖房。哪怕穷得要饭讨食,只要家中有房,跑一天回来,也有个住处;只要有地,无论是旱是涝,点上种子就有收成,人就饿不死。卖了地,今后我们怎么活呀,死了也没地方埋。’”奚长胡说:“黑小家呀,我不是不懂这个理儿。可是,咱凑不足钱,赎不回人来,地有何用?地和人比,还是救人要紧!”听得这话,酆三妹只哭不语。蓝彩云则当机立断:“三妹,就听家族长的吧。只要表弟平平安安回来,还愁赎不回地?”
酆三妹这才点头发话:“全仗家族长做主。”得了这话,奚长胡立即再奔西街郎家当铺。签字画押,拿好当票,奚长胡回来交酆三妹收好。此时日头早落,星儿一个一个从天空的深处陆续闪出。家族中的几个女人,早替酆三妹做好晚饭,家族中的来人在这里吃饭。其实人们并不是单为吃这顿饭,而是为的再有啥事,有腿的去跑腿,有力的去出力,不然怎么算一个家族的人呢!
饭罢,众人立即商量前去送钱赎人之事。虽说前去送钱如还债,但匪巢不是饭庄酒馆,最怕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对于此事,无论谁腿软,奚长胡子不能软,因为他是家族长。他响咳一声,说:“我是得亲自去的,因为那送信人进村先找的我,他们知道我是家族长。”说罢这话,少停片刻,又说:“可我不能一人去。一呢,带着50块大洋,一人上路有风险,何况是夜间,咱得防备;二呢,他们虽说放人,却不知黑小让他们折腾的啥样,能不能走走正正。如果黑小腿痛脚伤走不得路,还得有副担架。不是?”
众人赞成家族长想得周到,立即挑出四名身强力壮的小伙,一人扛一条槐木扁担,腰里缠上绳子。一切做罢,奚长胡带着四人立即动身。
渤海谣:
被绑票,最窝囊,
青天白日遭祸殃。
快去送钱能保命,
怠慢一步见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