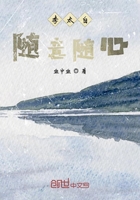这是黄河三角洲河口荒原上的一个疙瘩小村,仅有七八户人家。最早的逃荒人到达这里的时候,唯一的地标是棵柳树。柳树一年年长大,移民一年年增多,“大柳树”也就成了村名。一男一女,一前一后,离开村头篱笆小院,院门口的大黄狗朝他们摇尾告别,并不跟随。男子50岁,有点弓弓腰,满面皱纹显老,肩挑一副担子,两头是荆条筐,筐里装的是高粱苗笤帚,堆大并不沉重。担子后边跟一个年轻女子,上穿入乡随俗的蓝印花布小袄,下穿老中轻皆宜的青布裤子,梳着乡间媳妇通行的盘头,足穿有绊带的跟脚布鞋,外罩一件蓝花大夹袄,手提着一个小衣包,一副乡间女子走娘家的架式。
黄河口的荒原地广人稀,播种高粱多。高粱穗子是一宝,可以用来纺笤帚。这男子纺笤帚的手艺好,长年串村赶集卖。他的笤帚压满街,得一绰号笤帚王。日军占了县城,日伪修起大碉堡,四处抓劳工运往东北,笤帚王的儿子逃到黄河南的大鹰盘,参加了八路军黄河抗日纵队六支队。笤帚王长年串村赶集,人熟地熟,消息灵通,大柳树也就成了六支队的联络点,有人过河到敌占区,请笤帚王引路。
往日,从六支队来的都是男子,今天却是个年轻女子。六支队对他有要求:“你只管引路,不要问姓甚名谁,做啥事情。”笤帚王点头:“知道,这是为我好。管闲事惹是非,一问三不知,有事好推。”因此上路后一直无语,还有意与女子拉开一段距离。不料,出村不远,茅草路上只有兔子跑过,远近无人,年轻女子紧走几步跟上来与笤帚王说话:“大叔啊,这太平庄周围,有哪些知名村镇?”笤帚王张口念出一段溜儿:
喝茶你到茶棚园,习武你到三沙岗。
买布你到棉花桃,典当你到太平庄。
谁家媳妇不怀孕,柳林镇去拜娘娘。
年轻女子一笑,又问:“有名庄就有名人。大叔可有了解?”笤帚王张口又一段溜儿:
铁板会当家沙恒刚,商会会长苏仁旺。
八面溜光的袁传寿,最坑人的郎光让。
“大叔真行!”女子由衷称赞,“怪不得支队长给我打保票:‘有啥情况,尽管去问笤帚王。’大叔啊,太平庄一带有这多名村,这等名人,怎么变成魔鬼区呢?”这是她一直不解的问题。笤帚王听罢一声长叹:“唉,还不是让日本鬼子闹的嘛!”说罢又是一段顺口溜:
大碉堡,鬼门关,
鬼子杀人不眨眼。
中队长,彭清臣,
摧粮逼款恶作端。
南五团,说保安,
明抢明夺明诈钱。
蒙道士,蒙女人,
溜逛村头伏路边。
黑无常,杀人魔,
谁碰上他命就完。
念罢溜儿,笤帚王又一声长叹:“原本这是一片富庶区,如今到处鬼哭狼嚎,魔鬼翻天!”
年轻女子不语,只是步履沉重。她姓蓝名彩云,龙王庙蓝五爷的二小姐,只因蓝五爷树旗抗日,遭日伪发兵血洗,只逃出她和丈夫石信明、还有一个学生排,过河奔投六支队。学生排分到大部队,支队长把蓝彩云、石信明和卫先生、娄先生留在情报队。先是政治培训,又以老带新实践锻炼,回到营地再作分派。支队长先是把娄先生派走,去哪里,做什么,蓝彩云不知。接着又传蓝彩云:“派你去执行一项艰巨任务,怎样?”蓝彩云挺胸道:“行。去哪里,做什么?”支队长说:“龙王庙大战以后,渤海县局势大变。一是日军增兵驻扎,大挖封锁沟,建碉堡,扩大皇协军汉奸队编制;二是国民政府的部队出现分化,有的抗日,有的投日;三是杂牌丛生,土匪猖獗,奸淫绑票,无恶不作。太平庄一带甚之又甚,这个村庄男人被杀,那个村庄女人被抢,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称‘魔鬼区’。抗日首先除奸打匪,揭露投降派的丑恶嘴脸,不然百姓哪有胆量抗日!你是个女子,进敌占区不扎眼,因此支队决定派你到魔鬼区走一趟,摸清那一带的情况,踩出一个两个的落脚点,然后再派除奸队进驻。”
这是培训后的第一项任务,蓝彩云响亮地答应。先由交通员带她过黄河到大柳树,再由笤帚王送她去魔鬼区。两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十多里路,前方的村庄多起来,庄稼地也多起来,高粱、谷子、棉花、玉米、大豆、芝麻、黍子、稷子,还有的人家种瓜种菜,在地里搭起四面通风、谷苫子搭顶的瓜棚。风儿溜儿吹,豆地里蝈蝈吱吱欢叫,棉田中蝴蝶翩跹飞舞,谷穗儿低头哈腰,棉花棵底部的棉桃也开始咧嘴。本是农家欢庆的日子,四野却很少见人,更别说歌声笑语。又走十多里路,前方出现好大一片高粱地。
路从高粱地间穿过,风吹高粱叶子沙沙响,让人觉得头皮发麻,脊沟发冷。突然唰啦一声响,高粱地里跳出一个人,手持木棍拦路呼喝:“站住!”笤帚王吓一跳,立即停步,放下笤帚担子,扁担却拿在手。上眼看:面前这人黑布蒙面只露两眼,个头不高,是瘦条子,那声“站住”怯怯生生,拿棍的手在发抖。这不像杀人越货的人,笤帚王不发话,只注意这人有何举动。蒙面人却再也没动,只横棍站在路中间,笤帚王顿觉奇怪。他没有想到危险不在正面,而在背后:一位蒙面大汉脚步轻轻,从二人身后悄悄钻出,手拿一条长布袋,走至蓝彩云身后。
蒙面抢劫的歹人惯用刀枪,这人为何只拿条长布袋?原来,这人劫道不是为的抢钱夺货,而是为抢劫女人,抢到手连夜运外地,卖给人贩子。用什么办法抢呢?他们多是埋伏在路边等候单身女子,趁其不防贴近身边,猛地将布袋套住女人的头。这是乡间装粮食的长布口袋,只要把人头套住,再猛地往下一撸,这人便整个儿被装进长布袋里,手脚动弹不得,放到驴上驮外地,碰上人问就说赶集上店卖粮食。劫匪惯于黑布蒙头蒙面,长袍罩身,有点道士装扮,故人称其“蒙道士”。
此刻,蒙道士已经来到蓝彩云身后。蓝彩云见前方拿棍的人站立不动,意识到背后有鬼,迅速扫视周围。见那大汉提袋近身,她迅速一个左旋,将蒙道士闪至一侧。蒙道士蒙人必须一下得手,失手人家就不让你再蒙,还会呼叫来人。碰上这种情况,蒙道士就得转身逃遁,或强行施暴。也许这个蒙道士觉得远离村庄,且有提棍的助手在前,便亮出一把尖刀,低声厉喝:“你不声不张跟我走,有你的好处;胆敢呼叫,我破你的相,割你的舌头!”笤帚王手持扁担大喝:“你这般伤天害理,就不怕上天惩罚?”蒙道士一声奸笑:“日本占中原,中国哪还有天?你小老儿敢挡横,我一刀把你宰了!”说着晃一晃手中的尖刀。蓝彩云倒是不惊,说那蒙面人:“看样子,你伤害过好多家良姐妹。”蒙道士又一声奸笑:“不多,也就是十几个,只割破两个娘儿的脸,因为她们着实不识抬举!”说罢猛跨一步至跟前,伸手来抓蓝彩云。
蓝彩云没有躲闪,只是举起手中的小包去迎。与此同时,她手撩夹袄掏枪在手,顶上那人的胸。手指那么轻轻一勾,几乎没有听到枪响,那蒙道士晃了两晃仰面躺地,手中还攥着那把杀猪的尖刀。前方那蒙面瘦子见此光景,愣呆呆吓傻一般,扔掉手中的棍子跪地磕头:“爷爷饶命,奶奶饶命。”蓝彩云走上前去枪点他的脑袋:“你这类祸害百姓的坏种,也知道求饶?说,你们这伙还有谁,藏在哪里,都叫出来!”跪地瘦子说:“实不相瞒,做这事不能人多,只我们俩。我是被他强制来的,头一回做这种事。”蓝彩云当然不会轻信,喝问:“他怎么强制的你?说个明白。”矮瘦子说:“他先是强占我媳妇,又要杀我。媳妇给我求情,他才留我一命。留我不白留,要我跟他合伙,帮他截人、牵驴。”笤帚王最瞧不起没血性的男人,呸去一口:“还有脸说道!你怎不叫上几个知己,把这坏种干掉?”蒙面瘦子说:“爷,我没那胆量。”笤帚王骂一句:“天底下怎么有你这般废物!”蓝彩云问:“你的驴呢?”蒙面瘦子道:“驴在高粱地里藏着。”说罢起身进高粱地,不多时牵出一头小灰驴。
蓝彩云打量一番矮瘦子,确实像个没有刚性的人,也就收了枪。她问:“你叫什么名字?”矮瘦子说:“小名叫三,人称黄三,也有人叫我黄面瓜。”蓝彩云鄙夷地“哼”一声:“看你这副埋呔样子,也不像个作恶的人,今天我就放你一马。”黄面瓜又跪地磕头。蓝彩云说:“我要你做两件事情,可办得到?”黄面瓜说:“奶奶饶我一命,别说办两件事情,就是千件万件,我也去办。”蓝彩云说:“那好。第一件,从今往后,再也不做祸害百姓的事情。”黄面瓜连连磕头:“记得住,记得住。我若是再做歹事,出门五雷轰顶,老鸹啄眼珠子!”蓝彩云说:“第二件事情,抗日救国,不替汉奸做事。”黄面瓜一阵沉思,说:“禀报奶奶,这‘不当汉奸’我做得到;抗日救国我做不到。我是个无能的人,啥本事都没有。连自家的媳妇都保不住,有啥能耐拿枪打鬼子?”
笤帚王鼻中一声响哼,嫌弃至极,扭头不睬。蓝彩云却有耐心,对黄面瓜说:“抗日救国,不一定直接拿枪打仗,你手中也没有枪。我说的意思,是从今往后,你不要给鬼子汉奸办事,遇事支持抗日军民,就算你抗日救国。”黄面瓜立即点头:“这好办,这好办。我保证不给鬼子汉奸牵驴。”
蓝彩云再不同黄面瓜啰啰什么,挥手令黄面瓜离去。她伸手牵过小灰驴,对笤帚王说:“大叔啊,蒙道士见咱没脚力,给咱送来头小毛驴。您骑上吧!”笤帚王连连摇头:“不,卖笤帚哪有骑毛驴的?让人笑掉牙!还是您骑。”蓝彩云说:“您那大年纪不骑,我年轻轻的怎么能骑?这样吧,将您那笤帚搭驴背上,也省得闲着驴!”笤帚王一笑:“那倒也是。”便将笤帚担子搭驴背,又一声叹:“唉,你说这世道,怎么冒出这么些贼玩意!”
渤海谣:
黑的黑,黄的黄,
也有羊,也有狼。
人类世界千般样,
菩萨难管交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