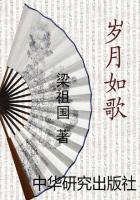成年的凯瑟琳婚姻并未那么幸福,由于她屈从了世俗,违背了自己的天性,所以当希斯克利夫突然消失三年之后再现时,她已无法协调自己与埃德加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关系,这时她才意识到窗外才是她所需要的、她的生、她的自由和灵魂的故乡。在她生病后、神志错乱之时,她对丁耐莉喊道:“把窗子再敞开,敞开了再扣上钩子!快点,你为什么不动?”(164)丁耐莉道:“因为我不愿让你冻死。”“你的意思是你不会给我活的机会了。”(164)昏迷中的凯瑟琳说完后,毅然从床上滑下来,步履蹒跚地来到屋子的另一头,推开了窗户,探出了身子,不顾寒风像刀子一样割着她的肩膀,朝着山庄方向呼喊着希斯克利夫。尽管这一切似乎只是一种徒劳、一种无奈,只能隔窗远望那边的山庄——遥远而朦胧,只能在幻觉中去寻找,这是多么巨大的孤独!在这场由窗内通向窗外的殊死搏斗中,凯瑟琳的心灵走向崩溃,最终死于精神迷茫。这里,开窗具有对新世界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等象征特点,同时也具有世俗****的特殊象征色彩。因为凯瑟琳深切地体会到窗内这个家庭的压抑与****,感受到窗内的黑暗足以把她闷死,闻到了文明家庭朽烂的气息,因此,她敢于冒生命之险打开窗户,让她仅存的生命活力散发出去,因为“自由的灵魂是无法真正忍受束缚的”。这里女作家借用窗这一喻体,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又一次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表现了女作家对精神自由与独立的不懈追求,“是英国天才作家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不到美满生活的宣言”。窗的这一喻义在随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一书里再次得到了印证:傍晚端坐窗前的拉姆齐夫人在那一瞬间体会到了自我与世界结合为一体,伍尔夫“在自己作品的艺术世界里找到了可与丑陋的现实相抗衡的理想境界”。在凯瑟琳下葬那夜,希斯克利夫因无法随她而去,返回了呼啸山庄,破窗而入,把他的满腔悲愤和苦楚向活着的人无情地发泄着。数年之后,洛克伍德来到山庄,夜间梦到一张苍白的脸,从窗外边靠在玻璃上,还有一只血迹斑斑的手,伸进打破的玻璃窗,要求进屋来。这大概是窗的意象最为残忍的一幕。这种“意象的荒诞,能令读者产生惊惧、敬畏的心理,感到它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而自己则渺小、微弱”。在这里,女作家艾米莉再次向读者暗示,天堂不是凯瑟琳的家,她更不愿自己的灵魂在外漂泊,她一心只想回到荒原,盼望和希斯克利夫厮守,因为他们同为荒原之子。惊醒后的洛克伍德的喊叫声引来了希斯克利夫,他早就期盼着与窗外的凯瑟琳相见,“他打开格子窗,一面拉开窗,一面激动得泪流满面。‘进来吧!进来吧!’他哽咽着说,‘凯蒂,来吧!……凯蒂,最后一次!”(33)这凄楚的呼唤声里,包含着多么强烈的痛苦和辛酸。他多么想跨越这时空的窗框,走上一条通向往昔、通向灵魂故居的小路。他苦等了二十年,依然无法实现这窗内与窗外的相见。在世界各国,恋人之间的爱意常常通过窗来表现,无论是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还是英国萧伯纳的《武器和人》,以及我国曹禺的《雷雨》,都是男主人公通过跳窗而入的方式,赢得了女人的心。但此时的这扇窗户已成为希斯克利夫的阳界与凯瑟琳的阴界之间的障碍。尽管希斯克利夫不费力气地打开了窗户,但仍无法“外出”到那个极乐世界里。后来管家丁耐莉发现了希斯克利夫死在那棺材式的床上,窗洞开着,“格子窗来回地撞”(439),他的那双眼睛露出“可怕的,活人般的,狂喜的凝视”(439)——他已经与窗外的凯瑟琳会面了,死亡成全了他们的爱情。无疑,这里的窗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承载着思乡之情,意味着一种灵魂的归宿。安顿生命,是人类的永恒追求。这扇窗为希斯克利夫打开了一个心灵的栖息之所,满足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凯瑟琳。在这里,女作家艾米莉“主张的爱与死已不再是对立的映像,而是交缠纠结:爱极而死,爱通过死达到完美的极致”。
三
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不再和谐,更趋于紧张甚至对立。在工业革命主宰的世界里,人们已无法依赖上帝,只能凭借自己的最后一点气力,暂时忘却现实世界的冷酷与束缚。而这“最后一点气力”则来自个体本身的主观意识。用自身的主观意识来暂时超脱现实,运用心灵自由的力量,将自己内心的愿望投射到闪闪发亮的窗户上,使之成为希望之光。窗的这一文化象征在女作家艾米莉的笔下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当洛克伍德最后一次拜访呼啸山庄时,这里已成另一番天地了:它在恬静的夜晚散发着花香,门开着,窗也开着,它不再门户紧闭、拒人于千里之外了。那敞开的门窗再次证明,古老而愚昧的呼啸山庄已敞开了通向象征着物质文明社会的画眉田庄的大门。小凯蒂和哈里顿亲手培植的小花园,在野蛮气息和文明养料的呵护下,定会盛开出爱情之花、希望之花。当从开着的窗子里看到小凯蒂非常亲热地教她表哥哈里顿读书,在那舒适温暖的客厅里,炉火照亮了他们健康幸福的面庞时,谁不在心底为他们深深祝福呢?当他们滞留在门槛上,再看一眼月亮或者更确切地说,借助月光再看一眼彼此的脸时,他们终于超越了他们的上辈,将要离开曾经给他们带来灾难、凝聚着野蛮气息的呼啸山庄而去散发着文明气息的画眉田庄去开辟新的生活。哈里顿与小凯蒂这年轻的一代就要双双走进更合乎文明标准的画眉田庄,那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无任何压迫和习俗的禁锢,享受着真正安逸和自由的幸福生活。这酷似一个美丽的童话,而女作家“艾米莉正是以这种方式摆脱世俗的枷锁,达到精神上的解脱”。最终,由窗户建架起的各种矛盾与障碍——自由与限制、生与死、文明与自然,随着第二代人建立起来的爱情,消失殆尽。当“小凯蒂和哈里顿成为一对幸福的伴侣,山庄和田庄这两个世界才终于统一起来。”
窗内窗外的和谐统一,让人们再次看到希望在人间,窗以弱势象征传达出其所具有的引领人们进入最高现实的内心向往的特点。可以说《呼啸山庄》是“一本不属于当时而属于后来的杰作”,女作家借用窗这一意象,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客观对应物,在那里,她“看见天堂的荣光闪耀”,实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现实社会里难以实现的一个完整的人生。
象征化描写的文化解读
《呼啸山庄》中运用了大量象征化的描写手法,艾米莉把自己在生活中所体悟到的深刻而又难以言传的人生哲理,通过意象的塑造,曲折地表现出来,为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要求读者去积极地思考、探寻小说背后那丰富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意”。
“象征意味着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越它所说的。”《呼啸山庄》中运用了大量象征化的描写手法,艾米莉把自己在生活中所体悟到的深刻而又难以言传的人生哲理,通过意象的塑造,曲折地表现出来。但有时读者也很少得到何物被象征化的暗示,因而在这部世俗骇惊的不朽作品里,往往是旧谜刚解,新谜又出。难怪长期以来,人们视艾米莉为英国文学中的“斯芬克斯”,并在20世纪不断掀起阵阵研究艾米莉的热潮。故我们有理由充分认识《呼啸山庄》中女作家用某些事物来象征一种主题的写作方法,希望借此能挖掘出小说新的内涵,给我们以更多的启迪和思考。
《呼啸山庄》中,女作家“将自由与限制、爱情与痛苦对立起来,与此同时将它们置于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表现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转化的特性”。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写,艾米莉使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具有了高度的诗意和象征意义,成为表现这一特性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门窗及钥匙和锁”这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在小说中频繁地出现,也正好反映了这种特性,或者可以更进一步理解为“囚禁”与“自由”的对立。这一对立的概念形成了小说中强烈反差的意象组合。女作家艾米莉笔下的人物所受的囚禁具有抽象和广义的概念:“肉体和尘世的存在即监禁,人物的孤独感也是在冥冥宇宙中无所归依的精神流放感”,所以女作家在小说中借用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来表达自己对另一超验世界的遥遥向往。
一
艾米莉生活在荒野,她热爱自然,她是大自然的骄子,她笔下自然环境的描写都与人物的塑造达到了一种和谐统一的程度。小说中的呼啸山庄虽说太小太局促,但它高高地托起了另一个和风雨雷电相呼应的内心世界。女作家通过对室外环境——呼啸山庄那蛮荒粗犷之景的反复渲染,来强化社会或者人性中恶的东西,使得挺立在风暴中的呼啸山庄,既是山庄,又不是山庄,形成了一种象征性意义——一个弥漫着原始罪恶气氛的封闭社会,像诗篇一般在读者心中唤起了纷至沓来的意象,它将印刻在人们的心坎,与人的心灵共振,借内心世界的无限张力,去探求社会对人性的桎梏和心灵对自由的渴望。
小说开篇扑面就有这样的描写:“可以想象北风的威力有多么强大。因为在房屋尽头有几株矮小的枞树过度倾斜,还有一排面容憔悴的荆棘都向一个方面伸展它们的四肢,仿佛向太阳乞讨温暖。”(2)这几句粗犷的诗意的描写,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作者有意将小说情节的展开建立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是别有一番用意的。终年不断的猛烈北风,不容许山庄的树木向天穹挺伸,强迫它们都向一边倒去,那萎靡不振的树木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发育良好的体型。“树性”被狂暴的猛风扭曲了。在这部作品里,树性就是人性的象征,人性同样终年不断地承受强暴的压力,就像那萎靡不振、倾斜得厉害的树木,人性同样被残酷地扭曲了。在这里,女作家暗示人们,远离尘嚣的呼啸山庄已经受到了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浸染。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浓厚、悲凉气氛的渲染,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压抑不住的气息,似有一种力量要冲破层层的阻力即将爆发出来。代表强烈个性的风雨雷电在荒原中到处显示着他们的威力,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在沉郁的荒原里正在酝酿着一场爆发。人性的歪曲,犹如自然的破坏,这里,女作家向人们又一次传递了自己爱荒原、爱自然,但更爱自由的心声。“自由是艾米莉的鼻息;没有自由,她就毁灭。”虽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然人性遭到了囚禁和扭曲,但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死亡最终证明了,他们在精神上回归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实现了自然之爱,最终也实现了自由。
二
室外自然环境的描写极大地渲染了小说的主题,但室内“门窗及钥匙和锁”的提及也频频跃然纸上,为作者笔下的人物再次增添了层层象征意义。小说中主人公总是通过窗子,看到另一边的景象。在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中,从19世纪开始,个体的内在世界与窗的意象就有了密切的关联,诗作与小说中(甚至是绘画中)都会出现站在窗边观望的人,观者与他周围的一切呈现出一种分割的状态,无法与外在的世界合二为一,常常是孤立寂寞的。小说的一位叙述者洛克伍德站在呼啸山庄里评论外边:“我走到窗前观察天气。我看到的是一幅令人伤心的场景:黑夜提前降临了,天空和山野混杂在一团凛冽的寒风和令人窒息的大雪中”(15);小说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也是从画眉田庄客厅外面朝窗子里面看;小说中更经常地用渴望从窗或门的一边到另一边这种意念来强调这种“囚禁”与“自由”的对比,总是存在一个想象中的分隔,有时物质的障碍物被清除了,这种分隔也难以清除。书中那个小精灵,即凯瑟琳的灵魂想进来,却被窗玻璃无情地隔开。凯瑟琳在画眉田庄里面,身体有病,心情又不好,渴望着到外边去,却出不去。不是门和窗把她隔开,而是无形的东西——她的健康状况把她囚禁起来。钉死的窗子,锁着的门及钥匙,更强化了这种分隔的概念。两座庄园里的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为获得个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由于别人的意志而遭受挫折,锁着的门窗及钥匙就是这种意志和权力的象征。辛德雷把希斯克利夫锁在卧室里,那便是他使用权力剥夺了希斯克利夫的自由。以后这一主题又在书中反复出现。当埃德加和希斯克利夫争吵时,凯瑟琳锁上了厨房门,并把钥匙扔到了火里;辛德雷和伊莎贝拉把希斯克利夫锁在门外;希斯克利夫把伊莎贝拉关在呼啸山庄,还绑架了丁耐莉和小凯蒂,并把他们锁起来;特别是当希斯克利夫把丁耐莉和小凯蒂关进房子又锁上了门,之后拿起了放在桌上的钥匙,小凯蒂就立刻跳起来去夺拿钥匙,这象征着小凯蒂拼命争斗,争取她的自由,而她最终没能抢到钥匙,说明希斯克利夫有制约她的权力。这里,女作家在暗示人们,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与外界的关系不再和谐,而更趋于紧张和对立。大自然已无法亲近,其不但冷漠无情,亦因工业革命而受到限制。当时在工业文明主宰的社会里,人们已无法信赖上帝,只能凭借自己最后一点力气,运用心灵自由的力量,将自己内心的愿望投射到远方闪闪发亮的窗户上,借那明亮窗户的希望之光,去对抗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