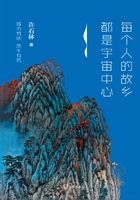一
我翻译叶芝的缘起在别处已有所交代,兹不赘言。迄今为止,不算散见于各种书刊和网络的零星发表和转载乃至盗版外,计出版《叶芝抒情诗全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1996年。译诗374首)、《叶慈诗选》(英汉对照,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2001年。自选译诗169首)、《叶芝诗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译诗374首)、《叶芝诗精选》(英汉对照,华文出版社,2005年。他人代选译诗43首)、《叶芝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自选译诗321首;剧本1部;短篇小说2篇;散文1篇)、《叶芝抒情诗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自选译诗199首,包括新增译诗4首)、《叶芝诗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自选译诗146首)、《叶芝诗选》(英汉对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年。自选译诗157首)等八种译著。其中,华文版《叶芝诗精选》是由书商策划并选编的,内容未经我过目,所选篇什既不代表叶芝创作,也不代表拙译作的精华;时代文艺版《叶芝诗选》的责任编辑极不负责,我仔细校改过的校样返回后,竟完全未用,而是用错误百出的第一次排版直接付印了,听说同系列(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其它诗选也是同样遭遇。
凡我经手的,每次再版,我都要对照原文逐首逐字修改译文。越是流行的篇什修改的次数就越多,远多于再版的次数。我曾半开玩笑地对学生说:叶芝人称“自我批评家”,对诗艺精益求精,几乎每首诗都是改了又改,直至一字不易的完美。能给别人改稿的是编辑,能给自己改稿的才是大师。我只是努力向大师看齐,译(艺)无止境,我的译文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令我自己满意。你们要学文学翻译,只需把拙译的新旧各版拿来对照着原文来比对研读,肯定会有所得。不传之秘即在其中矣,唯有心者得之。不过,在研读之前,如果自己也先试译一遍,效果会更好。我不怕献丑,只当是现身说法,为翻译事业做牺牲吧。
此次增订,除《叶芝抒情诗全集》原有的374首译诗又修改一过外,还新译了叶芝生前未发表过的早期诗作38首,加上选自评论小册子《在锅炉上》中的3首诗,共得译诗415首。本书虽仍未囊括叶芝所有诗作,但仍是现有收录篇什最多的汉译叶芝诗集了。
二
学界一般认为,叶芝早期诗艺主要受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和珀西·比舍·雪莱的影响,但在他正式发表的作品中却难觅例证。他的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它》(1889)主要是写爱尔兰题材的,只有部分涉及古印度和古希腊题材。诚如他在1925年所说:“许多诗,当然是那些关于印度或牧人和牧神题材的诗,肯定作于我二十岁以前,因为从我在那个年纪开始写《乌辛漫游记》那一刻起,我相信,我的题材就变成爱尔兰的了。”
1995年,斯克里布纳图书出版了乔治·伯恩斯坦整理编辑的《月下:威廉·巴特勒·叶芝未发表的早期诗》一书,收录叶芝作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诗作三十八首。这些叶芝生前因种种原因秘不发表的诗稿印证了学界的看法,其中有不少作品的确有模仿斯宾塞和雪莱等前人的明显痕迹,大多抒写遥想神仙英雄骑士淑女之类的思古幽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已开始表现爱尔兰和诗人私生活题材了。
少年学艺阶段不免模仿借鉴。叶芝还喜欢改写来自盖尔语或其他语种的作品译文,有时甚至难免剿袭之嫌而为人诟病。《静静的在达吉斯坦河谷》一诗即据俄国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梦》改写而成,较诸原诗,内容和措辞几无二致。《泉水中一个灵魂》显示了斯宾塞的影响,叙事诗《罗兰爵士》则从题材到形式都亦步亦趋追摹斯宾塞。《乌辛漫游记及其它》出版后,叶芝曾寄给前辈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一本。莫里斯以写欧洲古典神话和中古英雄题材的叙事诗见长,见了他说:“你写我这一类的诗。”于是乎对他大加奖勉,并答应为他写书评。《流寇的婚礼》也是这类叙事诗之一,只不过场景设在了十七世纪的爱尔兰,反映了叶芝在1885年结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约翰·欧李尔利之后的题材转向;写法则采用主人公对女友说话的戏剧独白形式,较以第三人称视点叙事的《罗兰爵士》更具抒情性。《你懂的我的歌》、《灰发老人》、《谷地》、《狂风吹打的碉楼》也都是以爱尔兰为场景的富有幻想色彩的小品。《居普良》、《日出》、《潘》则仍有古希腊的典故或意象或题材残留。叶芝一贯反对在诗中采用现代工业意象,也许因此之故而获评“无须是现代主义者而最现代”。《遮面的话音与黑暗的发问》中的有轨电车可以说是叶芝诗中绝无仅有的现代写实形象,诗人生前未公开发表此诗也许就是因为其风格异乎寻常吧。《路径》和《有关前世的梦》无疑是写给叶芝的单恋对象茉德·冈的。《路径》的结尾两行与收入诗集《苇间风》(1899)的《他冀求天锦》一诗的最后两行不无相似之处,甚至二诗的整体构思亦属雷同,后者应该是基于前者的改作或重作。《有关前世的梦》含有纪实成分,颇涉隐私,不免令人联想到叶芝在晚期诗作《他的记忆》(1926)中类似地珍藏的私房话。此诗的末行则可以为其另一首差不多作于同时的名诗《在你年老时》(1891)的末尾两行半作注脚,比较而言更清晰地勾画了“头戴繁星冠”的爱神丘比特形象,并点明无缘之人不受爱神眷顾的寓义。
叶芝晚年自称:“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选用/传统的圣洁和美好、诗人名之为/人民之书中所写的一切内容、/最能祝福人类心灵或升级/诗作的一切作为主题正宗”(《库勒和巴利里,1931》),这些早期诗作就是最好的证据。
三
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读者评论另一种拙译说:原作者的语言是海,译者的语言只是池塘,不禁哑然失笑。这是说,译者比原作者的词汇量差远了吗?诚然,这可能是事实,但量化就是决定优劣的惟一标准吗?在实际语篇中,两种不同语言的词汇量是不好相比的。从理论上讲,除非译者大量省略、合并,把近似的表达都译成同样,逐字对译的译文和原文的词汇量应该是大致相当的。我猜想,他(她)的意思更可能是说,原文的文体华丽繁复,而译文的文体朴拙单纯吧?实际上,我在翻译的时候,心中总是为读者着想的,生怕用词太生僻,太文雅,不合时宜,读者看不懂。可现在有一种不正之风,推崇绮靡、生僻甚至怪异词藻。例如今年高考,据说又有一位考生用文言文写作文得了高分,其用词之艰涩生僻令阅卷老师都汗颜拜服。实际上,在韩愈提倡“惟陈言之务去”的古文运动之后,古人也不会写那样佶屈聱牙的伪汉赋风或尚书体了;即便有,也不能算是好文章。我大学三年级初译叶芝,杨周翰先生评曰:“太文雅”;赵萝蕤先生指点曰:“要直译”。可见,掉书袋、弄词藻、尚文雅、喜意译是初学者易犯的毛病,而初学者还自以为是优点呢。
最近,诗歌翻译杂志《光年》编辑提问:作为译者,有何经验和体悟可以分享?我简答如下:
学国画,除书法基础外,先学工笔,后学写意是正途,否则易失之狂野粗陋。学译亦然,应先求精确,以直译为主,熟练后自会变通。以意译为主,不是初学,就是外语不够好,否则就是狂妄。
我常说,翻译没什么诀窍,只要两种语言都好,都达到熟悉各种文体,能自由创作的水平即可,那么翻译只是换一种说法而已;
不能全程使用纯原文词典(科技术语除外)做翻译,说明翻译水平还不够高;用纯原文词典翻译才是真正的翻译;借助源语——译语词典的翻译一半功劳应归于词典编纂者;
喜用华丽词藻、成语、熟语、生僻语、陈腔滥调的文学用语,甚至生造词语,都是初学者的表现;
译后最好放一段时间再看,不要急于拿出去发表。人说翻译是遗憾的艺术。我早年发表太快,后来译著一有机会再版就修改,改无止境。自己能修改自己的译作,是翻译水平提高的标志,创作也是同样;
我对译诗的要求是:不增一字,不减一字,不错一字,字字有着落;
译者如演员,好的译者应该是性格演员,千人千面;坏的译者是本色演员,千人一面。译者应隐身在译作后面,而不应突出到译作前面。曾见有译者把莎士比亚也译成现代自由诗模样,这就近于埃兹拉·庞德所为了;
译者凭借译作说话,犹如创作者凭借原作说话。然而,文学评论者可以不懂创作,翻译评论者却不可不会翻译,否则难以令人信服。然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弄不好会得罪人,甚至引火烧身。也许最好的评论是提供自己的译文。
以上体悟,自己也并非时时处处都做得到,做得好,只因自己是过来人,愿与从译(艺)同道共勉而已。总之一句话:宁拙勿巧。
我已故的武术老师常说:听过不如见过,见过不如做过,做过不如错过。就翻译而言,我更多是个实践者,而不是研究者。我做过,错过,改过。
傅浩
201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