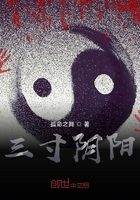实验体的主要问题在于前脑岛左侧出现了病变。
前脑岛与情绪加工和意识有着重要的联系,目前学术界虽然尚不能达成一致,但已有科学家拿出分析案例力证前脑岛与人类意识有着重要的联系。多次的猿类大脑实验,虽然目的并不是研究大脑具体组织的影响,但没想到间接记录下了前脑岛的病变过程。
我对比了数据,实验体的病变是一种突然间的质变。在复现实验以前,并没有很明显的病变,只是偶尔在大脑的零星区域找出了极其微弱的异常。然而,在复现实验开始时,实验体的大脑大量呈现出了块状异常,而且异常数值随着实验的进展变得越来越不具有规律性。我把数据通过电脑进行比对,发现在初期,异常数据呈现出线性的增大过程直到第一次复现实验完成。但是在第二次复现实验时,数据呈现出一种凌乱,这些数据间找不到一点逻辑关系,异常可以出现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甚至不需要刺激。
我找来小赵:“上周,实验体有没有出现什么情况?”
“有。”小赵说,“前天的下午,出现过狂躁症状。实验体持续击打墙壁,手部受伤严重。大约半小时后,又似乎进入了幻想的状态,表现出野外生存的特性。”
“你是说持续击打墙壁?”
“是的,这也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实验体持续击打墙壁至手部受伤,可它似乎完全感觉不到疼痛。而它停止击打后,又立刻进入了新的状态,似乎对击打墙壁的事情完全没有记忆。”
“有恢复正常过吗?”
“有,那天晚上就恢复正常了。恢复后可以观察到他对受伤疼痛还是有正常疼痛反应,并且我们实验人员,饲养员及兽医可以再次接近它并替它包扎。在下午时,它对我们有明显的攻击行为。”
“你是说,连对饲养员都有攻击行为?”
“是的。它似乎完全不认识饲养员了,以往饲养员对它的声音命令完全不起作用。”
“现在饲养员对我们的实验非常反感。毕竟是一手带大的,还是很有感情的。现在,我们的实验把实验体变得疯疯癫癫,产生了攻击行为,所以,院士们要求停止实验。”
“科学实验哪有不失败的,疯癫了就要停止,那怎么进步。为了科学牺牲的动物成百上千,之前也没听这帮老古董有意见。”
小赵看着我气急败坏的模样,缩了缩脖子,溜了出去。
下午的会议上,我不停向院士们强调实验项目不能停,我一直都认为自己并不擅长言语,却有些惊讶于今天自己的雄辩能力。从一些院士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他们情绪和态度的转变,从拒绝到犹豫到赞同。看着他们的转变,我很有信心能够将实验推动下去。
“你的诉求我们完全明白了,我们再讨论一下,明天给你书面回复。”院长朝我挥挥手。至始至终,院长除了这句话没有再多说一句,我看着他的眼睛,除了看到一潭深不可见,毫无涟漪的水外,看不见任何情绪。
离开会议,我转头来到实验体的饲养基地。
饲养员看见我,脸一下子拉了下来。他一转身,背对着我,手里还在整理给实验体的食物。
“我知道圆圆是你们买走的,我是没有立场说什么。既然卖给你们了,我也只能对圆圆尽照顾的责任。”
“实验失败,实验体受损伤,再正常不过了。现在我在这个实验体身上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难道你要让我停下?你也知道你把这只猿卖给了我,那你还有什么立场去和院里反映情况。”
“你不要满口实验体实验体,它有名字,叫圆圆。没错,圆圆在你们眼里就是个实验体,是冰冷的实验体。但是在我眼里,圆圆和我的孩子一样,我从它生出来就照顾它。你们现在把它弄得疯疯癫癫,你还好意思来见我。”
“你也说了,我们实验室买了这个实验体,那么我带走它也是天经地义的。而且合同里也写了,实验中可能产生一些意外情况。这是不可控的,而且实验体也不会被退回。”
饲养员猛然站了起来,转身走到我身边,怒视着我:“没错,我是签了那个合同。但是我还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这个实验不会有什么危害,只是通过对大脑做刺激,看看大脑的反应,而且你们会善待它。就是信了你们的鬼话,我才把圆圆给了你们,可是现在呢。我不想再看见你。”
我毫不客气地说:“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个实验还是要进行下去。实验体我们会带回。”
“是你们的院长同意我带回我的圆圆,你要带走,那你拿着院长的意见来。”饲养员抬起手,用手指指着门,“不送!”
碰了这跟硬钉子,我悻悻地回到实验室。别的院士老头我不担心,但院长那老头模棱两可的态度,让我不免有点心慌。
院长心里到底有什么小算盘,谁也不知道。
还有,他到底在顾虑什么?
我突然感觉我的头和撕裂一般疼痛。这种痛就仿佛有人硬生生地把工具插入我头骨缝隙中,然后用手用力地扳开一样。瞬间我觉得天旋地转,我判断不了平衡,撞翻了凳子,也装翻了电脑。我平躺在地上,眼前的一切扭曲成一个漩涡,又展平成一片波动的平面。我的四肢没有力气地摊在地面上,我的喉咙发不出一丝声音,大脑里除了痛只有混沌,连眼睛都不听使唤。
我就这么躺着。我感觉自己吐了,呕吐物从胃中泛出,流出口中。但有些流入了鼻子,流进了气管。我感觉窒息,但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任由着意识一点一点消失。
我看到门被推开。
几个穿着白褂的人似乎在喊着什么。有人把我挪动,反而引起了我更剧烈的呕吐,有人清理着我的呕吐物。他们的脸好像万花筒里的景象一样,撕裂,重组,有时候混乱,有时候完整。他们的身体就好像在哈哈镜里一样,一会被拉长成细条,一会被压缩成团状。他们在我面前奔跑着,让我更加眩晕,我想让他们停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终于,几个人抬来担架,把已经意识不清的我抬离了实验室。
这是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