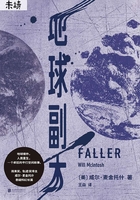大青沟的夜晚是冰凉的。我不大懂地理,反正就是沙漠吸热散热的作用。然而我确实懂得这温差的改变足够让我嗽个不住了。这一嗽八成又是一夜,于是在每一声的咳中我都痛恨自己这个冲动的决定,痛恨自己不肯服输的倔脾气--明明是牵挂着的却偏要静若止水。手握着电话,看星空。没有城里的聒燥,这里的夜分外清朗,于清朗中又透着安祥。在这样的夜里我渴望一双倾听的耳朵,似乎我这一生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忍不住诉说时他会放下一切,轻轻地说好。我拨通了谢超的电话:"喂,在干嘛?"对方悄声道:"在等你回家,那边冷吧?"一阵咳袭来,喘了半天方回:"还好。""胡扯!"他抗议,"这样也叫还好?吃药没?"好久了,没有人这样关心我。心头一热眼圈就红了:"谢超,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关心我。很少有人关心我的,所以每一个我都牢牢的记着。""还有谁关心过你?""丝子。别看她小,体贴着呢。
可如今却不想见我了--"禁不住哽咽,"白天我去了沙漠,翻了好久,什么都没有找到--""回来,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对一个习惯了说"我"的人,"我们"听起来如此新鲜。"对,我们。总会有办法的,相信我。"我点头,知道他看不见可还是点个不休。回屋后立刻着手打理行装,然后坐等长夜散去。我想回家了。真的。坐的是火车,出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谢超抢上前用一件外套把我裹住:"变天了,一会儿还有暴雨。你还咳么?"男人的体贴是陷阱,真怕自己一个跟头就栽下去。遂扬着脸调侃:"你大可不必如此上心,再献芹我也不会给你发薪。"谢超笑道:"呵,只求女主人大发慈悲留我住宿就可以了。"正说着,外面一道闪电掠过,飞沙走石,雷声轰呜--好大的阵势!我拍手笑道:"霍霍霍,老天爷要来人间清帐喽。你若有案在身就留在这躲雨,千万不要逞强袄!"谢超也笑道:"看在我为你送衣服的份儿上,它也不会为难我的,对不?"我晃头道:"那可说不定。兴许我是坏人呢,你帮我就是助纠为虐。
罪恶深重呀!"说完径直朝门口走去,他几步跟上道:"那你还敢出去?"我立定,神秘地"嘘"他:"我和老天爷是一伙的,我是卧底。"谢超夸张地大笑:"沈沉渔,谁的玩笑你都敢开么?"我也笑,有什么不敢的?它给了我如许的悲哀和苦难,而我所做的不过是用笑书写悲哀,用幽默化解苦难。赶到家楼口的时候雨已渐歇,阳台下面的空地上一片狼藉--这是风雨的杰作。我瞥了一眼一破碎的花盆道:"这若砸到头上,不出人命才怪呢!"忽地若有所思,忙朝自家阳台望去,丝子的那盆花已不知去向。我奔向花并没忘了回头冲谢超狞笑:"回家再同你算帐!你死定了!"果不其然,找到了丝子的龙舌兰。花盆破碎,泥土散落,喜在主干并未折断。谢超找来了袋子,面露惭色:"别生气了,一会儿买个花盆再把它种起来。"我不言语,一把一把地往袋子里运土。于黑土中忽地现出一角白纸,我与谢超四目相望双双醒悟:丝子把我骗了,什么埋在了沙漠中的绿洲,她的秘密就在家中。是夜对着谢超我絮絮叨叨地讲起了丝子种花的经由。
龙舌兰本是一株丑陋的植物,它的出名恐怕得归功于一部法兰西式的浪漫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片中的杀手里昂无论走到哪里,在沾满人血的双手中总捧着一盆龙舌兰花。对这株植物的爱最终演变成了对他救出的一个小女孩的爱。杀手本该是冷的,一旦动了感情肯定死的很惨。影片最后的一个镜头是小女孩进了收留所,她把花种在了大地上轻语:在这,你会长得更好。丝子大受感动,不理我的冷语相嘲不远万里买来了龙舌兰朝夕相伴。这种疯狂行为正应了它的花语:为爱不顾一切。谢超默默地听着,忽道:"我们把它埋在楼下的花坛里吧,在那,它会长得更好。"于是我们拿着小铁铲,花,纸条一起来到了花坛。谢超负责种花,而我则深深地挖洞,让那纸条在永不见天日的泥土里快快腐掉,然后丝子就会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恋爱,结婚,生子,远离痛苦,幸福的过一生。不是所有的爱都是被祝福的。有的时候相嘘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纸条上的六个字早已熟烂于心,可是丝子,让我们来一起练习遗忘吧,不论多久都得忘记:丝子爱沈沉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