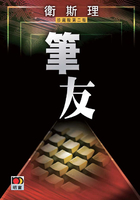周五早上,我到晨星餐厅吃早饭,饭后直接去了西五十三街的唐奈尔图书馆。前一晚我们用餐时,简单谈论过“斯洛克姆将军号”沉船事件,但我并不清楚确切的事发时间和伤亡人数。我找到一本书,它提供了许多问题的答案,有些甚至是我开始阅读后才想到的。与该事件相关的,从船主到各级负责人,几乎所有人都有重大过失,却只有船长被关进大牢。而且,以他犯下的弥天大错来看,他的刑罚实在轻得不可思议。
据我所知,那时无人提起民事诉讼。世界在这四分之三个世纪里的改变实在太大。换成现在,要是有谁动了别人哪怕一根寒毛,就难逃法律诉讼——就算那根寒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就算那事发生在一百公里以外。这种没完没了大大小小的诉讼对这个国家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仔细思量,但也不急于得出结论。我读到的一些东西,又让我转而关注另一个话题,打开另一本书。
早晨就这么过去了。我从唐奈尔的阅览室直接去了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刚好赶上十二点半的聚会。一点半散会后,我在披萨铺上买了披萨和可乐。午饭这样解决也挺好,但被营养师看到了肯定不答应。到家大概是两点一刻,语音信箱里有两条留言。前一个是十点四十五打来的,后一个我早回来十分钟就可以接到。两个电话都是杰克打的,两次都说他稍后会再打。
我上楼给他回了电话,想着他可能在家,或者那边有了答录机。可他不在家,那边也没答录机。
我在屋里一直待到晚饭时分。我没有出门的理由,手头又有本书要读。所以我也不是特意在等他的电话,不过也有这个考虑吧。电话只响了一次,是简打来的,确定我们周六晚上还要见面。她问我昨晚是否真的一路走回到家,我回答之前深吸了一口气。“走了两条街以后,”我说,“我说了声‘去他妈的’,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约好碰面的时间和地点,便挂了电话。我琢磨自己是怎么了,差点就说,没错,我从约克维尔一路走到了家。还有呢?说我的脚酸腿疼?说我在路上被人抢劫、持枪威胁,而这都是她的错?
我没那么说,当然。我先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回神,然后告诉她平淡无奇的真相。而她也没逮着机会念叨,说我原本可以搭她的便车,能省几块钱。看来我们都在进步。
周五晚上我去了圣保罗教堂,在那儿我见到了吉姆。不过,他正为头痛烦怨,场间休息时就先回家了。结束后我与几个人去喝咖啡,聊到最近戒酒会里有人坦诚自己是蕾丝边[10]。“我早知道佩吉是,”一个叫马蒂的家伙说,“刚认识她十分钟我就意识到了。我只是想在她自己反应过来之前碰碰运气。”
“脑子里还想着‘三人行’吧?”有人说。
“没有,我没想那么复杂。我只想在她明白过来之前上她几次。”
“可是上帝有别的想法。”
“上帝,”马蒂说,“他无知无能。上帝在他妈的调控台前睡着了。”
回到旅馆,前台有我的一条留言,同样的留言:杰克来过电话,稍后还会再打来。他没说让我打回去。太晚了,我也不想打。可我又改了主意,还是打了,不过没人接。
星期六,天气又冷又潮,雨下个不停。我没吃早饭,从街区尽头的熟食店订了早午饭。送餐的小伙子被淋透了,像一只快被淹死的老鼠。于是我多给了些小费。
整个下午我都在看电视,不停地换台,在几场大学橄榄球比赛之间换来换去。我并不在意看什么,这总比到外头淋雨好。而且我想,如果我一直待在屋子里,杰克找到我的几率也会高些。
可电话一直没响。我拿起话筒,给他打了几次电话。无人应答。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不是我真的着急与他联系,我只是不想继续被这没完没了的留言缠住了。
所以我一直待在屋里,要么看电视,要么看窗外的雨。
我和简约好在“小意大利”碰头,马尔伯里街和赫斯特街交界处的一家餐厅。我们去过那里几次,都挺喜欢那儿的食物和气氛。我提前几分钟到了,服务员没查到我们的预约,但仍为我们找了一张空桌。简迟到十分钟。食物不错,服务也不错。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吧台上一个健硕的男人是我十几年前抓过的犯人。我本想指给简看,给我们的闲聊添点料。想想还是作罢。
饭后我们打算在附近散散步,不过天还下着毛毛雨,还挺冷的,所以我们便直接回到里斯伯纳德街。她泡了壶咖啡,放了几张唱片——莎拉·沃恩、埃拉、伊迪·戈尔梅。这是个阴雨的十月夜晚,温馨浪漫的情调飘荡在空气里,正适合你侬我侬,但用餐时盘旋不去的冷淡和距离感,一直没有散去。
我想,就这样了吗?难道我余生的每一个周六夜晚都要这样度过吗?
到了午夜,我们上床睡觉,收音机调在全天候播放爵士乐的频道上,我俩躺在黑暗里温存了一会儿。我感觉到脑海边缘暗藏了什么东西。我不想看它,睡眠便如舞台的幕布般急速落下。
几个月前,我开始在简的住处留下一些衣物。她已经腾出几个衣柜的抽屉给我使用,也给了我衣橱里的几个衣架使用,这样早上冲完澡后,我就可以换上干净的袜子和内衣裤——还有干净衬衫。通常我会把换下的衣物留给她洗。
“你戒酒快满一年了吧,”早餐时她开口道,“还有多久?一个月吗?”
“差不多还有五六周吧。”
我觉得她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
当晚我在第九大道的一家中餐厅和吉姆·费伯碰面。我俩都是头一次去那里,两人都觉得食物还可以,但不会特意向人推荐。我跟他说了前一晚与简的互动,他仔细聆听,细细想了一想,然后提醒我我戒酒快满一年了。
“她也是这么说的,”我回道,“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耸了耸肩,等着我回答自己的问题。
“‘头一年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我知道这句金玉良言。”
“没错。”
“换句话说,我还有五六周来决定我和简的关系要往哪个方向走。”
“错。”
“错?”
“你还有五六周,”他说,“不用做决定。”
“哦。”
“理解两者的差别吗?”
“大概吧。”
“满一年的时候,你无须改变现状。你无须做任何决定。你没有义务采取任何行动。最重要的是,在那天到来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明白了。”
“不过话说回来,”他道,“我们现在谈的是你的规划。她也许有她自己的规划。你满了一年没碰酒,再接下来你要么拉坨屎,要么离开粪坑,懂吧?”
“大概明白。”
“你知道,”他说,“说什么满一年才能做决定之类的,只是一般情况。对有些人来说,前五年最好都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
“你开玩笑的吧?”
“甚至十年。”他说。
我们参加了圣克莱尔医院的聚会。参加的人大半都是戒毒所的病人,这是强制要求的。让他们保持清醒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发言了。吉姆和我来过几次,在这里你基本上听不到什么有深度的发言,不过倒是挺好的观察机会。
会后我陪他走回家,他突然说:“有句话你要记着。是佛陀说的,说得挺对。‘对现状的不满是苦恼的根源。’”
我说:“佛陀说了这话?”
“我是这么听说啦,不过我得承认我没亲耳听见。你好像很惊讶?”
“嗯,”我说,“我没想到他还这么有深度。”
“佛陀吗?”
“别人都这么叫他,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这名字就这么传开了。他应该有六英尺六英寸吧,大块头大肚腩,光头。这人定期参加莫拉维亚教堂的午夜聚会,不过偶尔也会到其他的地方。我猜他以前是机车党,而且八成坐过牢——”
他脸上的表情让我说到一半停住了。他摇摇头说:“我说的是在菩提树下打坐,等着觉悟的佛陀。”
“我以为是苹果树呢,而且我以为是他发现了地心引力。”
“那是艾萨克·牛顿吧。”
“如果是牛顿的话,那应该是无花果树才对。总之你说的是另一个佛陀,这种误会很正常。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叫佛陀的就是莫拉维亚教堂那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在西街一家粗野的酒馆看守大门。那句话你再跟我说一遍好吗?苦恼的根源是什么?”
把他送回家之后我也回了旅馆。之前我在旅馆前台停留过,惊讶地发现居然没有留言。回来之后发现仍然没有电话记录。我问了前台的服务员,他说是有一个人打了几次电话,但没说名字,也没留言。他能告诉我的是,打电话的人是个男的。
是杰克,我想,他已经放弃给我留言了,因为留了也没用。我上了楼。正在挂衣服时,电话响了。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马修吗?我是格雷格·斯迪尔曼。”
“我好像不认识——”
“我们前几天在‘每日清醒’戒酒会里打过照面。杰克·艾勒里介绍我们认识。”
“想起来了。”杰克的辅导员,珠宝设计师,耳朵上还戴着自己的作品。“当时你好像只说了名字,没说姓氏。”
“是,”他说,然后大声吸了口气,“马修,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