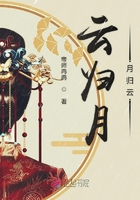我知道这虚无里头至少有三件东西:一个终结的王朝,一枚钤在江山边沿的皇室徽记,一段海浪传唱不休的挽歌。
石浦的皇城沙人称铁板沙,细如练绢,结实无比。就单个沙滩来说,它是象山半岛里最大的,长1800多米,宽200多米。潮水全线退却的时候,整个沙滩尤其平坦、宽广。从岸上望下去,一色浑黄,面朝大海铺陈,缓缓呈现的过程,恢弘、苍茫,就像帝国的中原版图一样壮观。
秋末到初春是旅游淡季,傍晚时分去海滩,往往游人绝迹,空旷的沙滩铺满寂寥。夕阳绯红色的光芒从西边斜扫过来,擦着远处瘦削的屋脊和不远处结实的海堤,宛如一声发自天边的叹息长途飘临,带着空泛的抚慰。供游人娱乐的马,枣红色的和白色的,高大,强壮,抖着一身缎子般闪光的皮毛。平时被驭者拘束着,看上去性子温软得像团棉花,此时可能被夕阳点燃了潜在的野性,躁动不安起来,马蹄不断踢腾着。驭者跟着兴奋,翻身,策马扬鞭,在空旷里一路狂奔。
马原本属于自由,看它们高贵的头颅在空中高高纵落,碗大的蹄子在坚实的沙地上敲击出了重浊的声响,低沉却震撼人心。
海边的晚风起了,带着推波助澜的威力,一阵阵吹送,安置在草地深处的音响所传出的乐声由此变得宏大鲜明,顺着宽阔光滑的广场流淌过来,从台阶跌落,倾泻在海滩。上面,新鲜的马蹄印迹与潮头的水线并行,蜿蜒向前。目光被牵引至奔驰的马,看见它们飘扬的鬛鬃以及驭者的头发,浴在烈焰似的霞光中,熊熊燃烧。
漫天彤云,黄沙遍地,烈马,长风,从地腹传出的旋律,白练狂舞的浪花,是在那一刻,激奋甚至悲怆涌上心头,非常陌生的感觉,古老凝重,像皇城沙滩的最初历史篇章。
这要追溯到南宋王朝。据县志记载,时人见浮尸海岩,乃绣龙黄袍,疑为帝昺,遂葬焉,外围以墙,因名宋皇城。至今此地仍有宋皇城村,一旁习称沙头的沙滩从此有了皇城沙滩的大名。
几百年过去,曾经的目光都已消散,只有皇城这个地名,记住了历史上某个王朝的最后归宿,也记住了这位身着鲜明袍服的幼年天子,茫茫苦海里一路飘零。不管他孤独的灵魂是否还抛掷浪尖,他的肉身终于选择在此靠岸。
在皇城沙滩的南端,留下了一座关于他的庙宇——宋王庙。
这座建筑物仅一进一间,一览无余,史料记载是丞相陆秀夫以白绫负幼帝投海,时间为公元1279年3月19日。这纵身一跃,一个王朝跟着轰然倒塌,留在历史天空里的背影,为这优柔积弱的朝代画上了不无悲壮的句号。
眼前的宋王塑像果然容颜稚嫩(赵昺七岁为帝,八岁投海)。除了陪伴两侧的土地夫妇,善良的村民还自作主张塑了宋王娘娘与他并肩,共度风雨长年。庙建在礁石上,背依高坡,面临大海,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不知为什么,总让人想起当年崖山的南宋残部被元兵赶尽杀绝,军民死伤十余万的场景。尤其站在局促的前院,一堵围墙挡住了视线,却挡不住轰然的涛声,静听之,一阵比一阵狂暴,是涨潮了,摧枯拉朽,惊心动魄,仿佛千军万马掩杀过来。转出门去迎接,扑面的是苍茫动荡的海面,而身后的宋王庙,小小的,宛如遗漏在海边的一枚贝壳,凝结着生命已逝的忧伤,但看上去很宁静,近乎虚无。
我知道这虚无里头至少有三件东西:一个终结的王朝,一枚钤在江山边沿的皇室徽记,一段海浪传唱不休的挽歌。
夕阳终于收拾起最后一缕光芒,好似旅人收拢他的行囊,离别或消逝,最后的深情一瞥,使皇城陡然金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