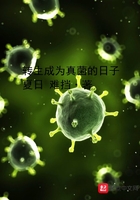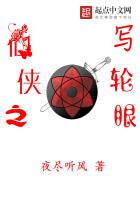“歇一会儿,先喝点参汤。”
他疑惑千万重地眨眨眼睛,盯着紫珍问:
“哪来的人参?”
“是南后派人送来的,”紫珍夫人道,“娘娘说你为大王分忧,为楚国操劳,要保养身体。大王也传话过来说,宁可失去半壁江山也不可累坏一个屈原。”
“南后啊,南后!”他立起身走到窗前,心潮起伏怎么也不能平静。证据确凿,完全是南后耍阴谋诡计,煽惑大王在误会加醉得一塌糊涂的情况下,对心上人山鬼细腰施以惨无人道的劓刑。按说,大王一怒之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是不应该去救的。无论废了她的王后,还是割了她的鼻子,都是罪有应得,自食其果。
然而,那是在满怀希望的六国合纵御秦取得绝对胜利的前夕,他为国家为君王大局着想,违心地做了那么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现在悔之晚矣!
不过,大王这次接受屈子诤诤谏言,同意变法,缔造宪令,冒吴起变法前车之鉴的风险,乃真心实意!得来实属不易。他对着王宫方向深施一礼呐呐道:
“大王,屈原呕心沥血也要造好宪令,为国君累死,死得其所。为民解忧,不惜粉身碎骨!”
说罢,他回到书桌边,喝了一口参汤,又伏案挥毫疾书起来。这时,紫珍夫人善意地说:
“郑袖品貌端庄,只是心肠太窄,嫉妒柳贵妃。她能差人送来人参,也就不错了。”
“是啊,她毕竟是王后,不能脱俗。坏就坏在他那老父亲、小弟弟身上。郑家父子跟腐臣朽贵狼狈为奸,在封地鱼肉百姓。这次法令一出,制裁的就是他们。”
“南后家人最坏,你也该笔下留情。”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
“她毕竟是一国之母。”
“此言差矣!”屈原头也不抬地说,“宪令是关系楚国千秋万代的大事,不能因郑詹之流而动摇王室的根基。也不能因王亲国戚就姑息养奸。”
“先生啊!我,真替你担心。”紫珍的双重身份躁动不安,沉默了许久还是如是说。
“担心什么?”
“法令一出,该得罪多少人!”
“哎,只要大王相信我,得罪那班庸人算什么!”
紫珍夫人几声咳嗽,赶忙以袖掩鼻。
“你是怎么啦?”屈原一愣,连忙起身扶住夫人欲将她送回卧房,“身体不适就该早些歇息。”
“不要紧,”紫珍从衣架上取下一件长袍,“只是变幻不定,千里迢迢不服水土而已。”
“噢,南国气候潮湿,阴冷,你要随时注意加衣。”
“不要为我担心,”紫珍夫人把长袍披在丈夫肩上,深情地望着屈原,情意缠绵地道,“你是楚国的栋梁,又是前所未有的大诗人,你的身体比我要紧。”
“多谢夫人!”屈原欣慰地转过身去,刚一坐下,又埋头于草拟宪令。他这一转身,就像所有干大事的工作狂一样,早已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身边还有身体不适的夫人紫珍的存在。而细腰精魄呢,坐在屈原背后临时为夫子设置的卧榻上,一直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凝望着他。直到沉重的眼皮合上去,歪在卧榻上进入梦境。
她和他重又回到了故乡......巫山的绿水青山,飞泉流瀑,响鼓溪边的洞辟书堂。那是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多么令人难忘的****。她和他在挂满藤萝的山崖上奔跑,追逐,疯笑,呐喊……她这阵却怎么也跑不动。身子不是自己的,而是羸弱的猫鬼妹妹的。山鬼精魄和猫鬼身躯,白花猫生前惨遭南后郑袖蹂躏,两条伤腿被藤萝缠住,朝天鼻拉着风箱……她远远地落在了后面,眼睁睁看着他从一座危峰上掉下去,掉下去……下面是无底的万丈深渊。
她哭呀,喊呀,叫呀!她喊不出,叫不出,胸脯仿佛是一炉灶火。是闭了气的炼锡炉就要爆炸。通身发热发烧,口里,鼻腔像烟囱冒着烟与火。舌头,嘴唇像开裂的灶土!啊啊,为了他,她的恋人,楚国的希望,人世间从未有过的诗人,她拼尽最后一丝儿力气呼喊:
“灵钧......!”
屈原茫然地抬起头往外张望,糊着素帛的花格窗户,早已经泛白,远远的雄鸡“喔喔”地打鸣。他站起身揉揉酸胀的两眼,舒展一下胳膊。他莫名地车转身在寻找着什么--是寻找午夜令人疑惑难解的夔柳与紫珍的转换?也许是疲乏至极的精神恍惚吧。
然而,这不是第一次。
他曾经在紫珍房间的窗户纸上,清晰地看到山鬼细腰夔柳的身影。夔柳被割去鼻子的那一晚,紫珍的鼻子曾经产生剧痛,而后鼻翼两边留下细细的白痕。这说明紫珍与夔柳之间有某种神秘联系。是心灵感应?血缘之亲?不可能!她们远隔数千里,出生在不同国度……
刚才恍惚又听到夔柳的呼唤,是她吗?一当看到歪在卧榻上的夫人紫珍,他急了。三步并两步奔了过去,把自己披的长袍裹在她的身上。
“这怎么行呢?怎么行呢?紫珍!你怎么能躺在这里过夜?”他将她紧紧抱了起来,不住地抱怨说,“郢都深夜寒气太重,你要病倒了可怎么办?”
紫珍夫人惊醒过来,原来是南柯一梦。她欣喜地看到丈夫并没有从危峰上掉下去,却紧紧地搂抱着她。瞅着他的一脸倦容,她心痛不已地说:
“你看,你都干了一个通宵。我去吩咐婵娟,快给你准备早点。”紫珍夫人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叮嘱,“你吃了早点,好好补睡一个觉。”
屈原在书房吃了“寒具”(早点),在卧榻上马马虎虎打了个盹,景差进来禀报:
“先生,上官大夫求见。”
“朝堂不见家里见,非正人君子。不见。”屈原对俗不可耐的上官大夫早就没有好感,他不想见靳尚。站起身不往外走,却又来到书案前。
“同朝为官,哪能这样!”紫珍夫人把一碗热汤搁到书案上,转过身朝外走着,“我去看看。”
“去把他轰走!”他又坐下去埋头修改宪令。
紫珍夫人来到客室,上官大夫靳尚恭敬行礼。随即他的家臣献上一份非比寻常的厚礼。
屈夫人连连推辞道:“这,这……”
“左徒大夫为国操劳,”靳尚言辞恳切地说,“他殚精竭力,夜不能寐。我靳尚无能,办不了大事,只能献上一些山珍补品,聊表心意。”
“不行,不行……”
“屈夫人,靳尚不好走动,很少串门子。”靳尚虚情假意地说道,“这不,屈大夫担任左徒有年了,我还是头一次登门,真不好意思。”
“您是贵人,国事烦忙。”
“都是老家领地送来的一点土特产品。”
“上官大夫,”屈夫人执意不受,“我家先生是从来不准接受礼物的,您这叫我太为难了。”
靳尚和家臣正束手无策,屈须大大方方走来,接过礼物交给婵娟道:“人家带来了,收了就收了。”又满脸朗笑地说,“上官大夫,不是外人。”
靳尚这才环顾左右,落落心在垫席上入坐。屈夫人仍有微辞:“姐姐,屈原可订的有规矩。”
“这位是?”靳尚把话题岔开。
屈须自我介绍说:“我是屈原姐姐,乡下粗人。”转对婵娟,“还愣着干什么?快拿一些归州的柑桔来。”
靳尚笑道:“屈大姐真是个豪爽人,其实我靳尚也讨厌这一套。不过,同朝为官,没有一点人情总不好意思。您从老家来了不少日子吧。”
“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屈须说话跟做事一样利利索索,“小弟公务忙,回不了家。总让我到乡下去看看,了解一下那里的民情民怨。”
“你们老家是楚国发祥之地,”靳尚说,“前些年,我还陪驾大王去那里围猎呢,那里收成还好吗?”
屈须拍着巴掌道:
“收成倒还可以,就是领主的苛捐杂税太重。如今地要交土地税,人要交人头税,杀猪要交杀猪税,宰牛要交宰牛税,走路、过河、坐车、驾船都要交税。只有两脚一抻......两脚一抻还要交棺材板子税。”
“是呀,是呀,那税是太重了些。”靳尚附和。
婵娟拿来一筐柑桔放在食案上,立在屈夫人之右。屈须指了指桔子,继续她的数说:
“上官大人,尝尝我们归州的桔子。桔子好吃,税不好吃。除了税还有捐,如今针屁眼大一个官,只要手里有点权,求他办点事就得交门坎捐。”
靳尚拿了个桔子在手上慢慢剥着,眼睛滴溜溜四处逡巡着说:“哎,屈大夫呢?”
“先生在书房里。”婵娟搭话。
靳尚欲起身,被婵娟拦住:
“先生正在修改宪令,吩咐不让打扰。”
靳尚重新坐下。屈夫人一旁咳嗽,越咳越厉害,立起身来对靳尚歉意地道:
“对不起,我就少陪您了。”
屈须去搀扶弟妹,紫珍的山鬼性格又显露了。她不让大姐帮扶,要自己走,两人在那儿纠缠。
靳尚巴不得屈夫人走。他重新打量着貌美而端庄的婵娟,“你是屈先生收养的姑娘?”
婵娟不悦地说:
“什么收养的姑娘?我叫婵娟,地地道道的齐国临淄人。我出国随夫人一起来到屈府,夫人最近身体一直不大好,先生也忙不过来。”
靳尚奉承地说:
“啊,你就是婵娟姑娘!听说婵娟姑娘是屈先生的高足弟子,文思敏捷,辞章锦绣。南后早想物色一个女才子给她做女官。婵娟姑娘,我给南后保荐,进得宫去可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啰。”
“我不能离开先生。”婵娟坚决地表示。
“你不想进宫?”靳尚不可理谕地,“这可是楚国女孩子做梦都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