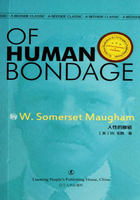夜深,窗外的月光凌乱地洒在破旧的走廊里,投射出一片片诡异的斑驳。
徐环在走廊上小心翼翼地行走。即便他的脚步已经迈得很轻,但陈旧的木板仍然不时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在一片死寂中显得格外惊心动魄。不仅是地板,整个楼都已经老旧不堪:发黄的墙面已经褪色,墙体上现出道道裂缝,狭窄的窗台上积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在月光的照射下,走廊里散发出一股陈腐的气息。
每一片斑驳,每一片阴影之中,仿佛都隐藏着一些令人恐惧的东西。它们似乎在阴影中冷笑着,监视着徐环的一举一动。
徐环浑身冰凉,额头却布满了汗珠,他感到一股发自内心的恐惧。在这种极度的恐惧中,他来到了走廊尽头,一扇更加斑驳的木门立在面前。他抬手轻轻推开木门,一阵刺耳的嘎吱声随之响起。
徐环悄无声息地踏入门后的黑暗之中。这是个狭窄的房间,一片漆黑,只有位于屋子中间的一件东西散发着,确切地说是反射着幽暗的光。
那是一面宽大的镜子,就这么突兀地摆放在房间中央,十分诡异。徐环愣愣地看着这面镜子,莫名恐惧。镜中的身影,清晰明了,仿佛是另一个徐环在隔着镜子看他。突然间,一个荒唐的念头贯穿脑际:那是自己,还是一个长得像自己的人?
他眨了眨眼睛,镜中的“自己”也眨了眨眼睛;他抬了抬手,镜中的“自己”也抬了抬手。这下他才松了口气,甚至对自己刚才的担心感到好笑。突然,镜中的“自己”幽幽地咧起嘴,冲徐环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徐环惊恐万分地看着镜中的“自己”,他想跑,可两腿却像被冻住一般,动弹不得。而镜中的人似乎想离镜外的世界更近一些,于是使劲往镜子外挤,以至于脸贴在镜面上,鼻子和嘴唇被挤得变了形,像一头丑陋的怪物。
徐环这才意识到,这哪是什么镜像,根本就是镜中还有一个人,一个长得像自己的人。
就在这时,徐环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镜面后这张扭曲的脸的旁边,竟然又出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脸,同样露出诡异的微笑,贴在镜面上,拼命挤压自己的五官!
徐环心中一颤,全身剧烈地抽动起来。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闭上眼睛喃喃地对自己说,“都是幻觉。”
许久,徐环鼓起勇气睁开了眼,期待幻象消失,可眼前的场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诡异:镜面后,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一张张同自己模样相同的脸,他们把鼻子和嘴唇挤在镜面上,仿佛一个个扭曲怪诞的面具……
徐环大叫一声,猛地坐了起来。他头脑发晕,心脏狂跳,浑身颤抖不止。缓了一会儿,他才发现,自己正坐在床上,刚才的恐怖经历,只是一个噩梦而已。但这个梦又如此真实,让他一时沉浸在那种彻骨的恐惧中,不能自拔。
坐了几分钟,徐环才逐渐镇定下来。他费力地起身下床,打开冰箱,给自己灌下了一瓶冰水,然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抬头看了看表:妈的,又是凌晨四点。
徐环浑身发软地走到客厅宽大的落地窗前,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大雨。听着雨滴打在树叶上的啪啪声,他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
最近几个月来,徐环几乎天天做这种奇怪的噩梦,而且每次都会在梦中惊醒。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了,再这样下去,真要神经衰弱了。想到这里,徐环掏出手机,拨打了于东青的电话。
农业重金属风格的彩铃响了好一会儿,于东青才接了起来:“你妹的徐环,给我打电话之前,你能不能先看一下时间?现在才四点半啊!”
徐环这才意识到自己把睡梦中的于东青吵醒了,心中略感抱歉,但是仍以若无其事的语气说:“四点半,这要是搁夏天,天都亮了,我这不也起来了吗?”
于东青语气中充满了疲惫:“我刚出现场回来,才睡了两个小时就被你弄醒了,你再这样我把你拉黑名单了啊……有什么事,赶紧说!”
徐环嘿嘿笑了笑:“是这样,上次你不是给我提过,市局技术部门有个学心理学的心理医生吗,你还让她给你做过心理治疗,对吧?”
“你说的是吴婷婷吧,没错,她是公安大学心理学系的高材生。不过她不是心理医生,而是在我们局技术部门供职。她也不是给我做心理治疗,就是有时工作压力大了,让她给做做心理疏导。找她干吗?”于东青顿了顿,狐疑地说,“该不会是你看上人家小姑娘了吧?告诉你,你别打歪主意,人家才刚大学毕业……”
“你少把自己的龌龊想法放在我身上。”徐环打断于东青,“是这样,我想让她也帮我做做心理疏导,行不行?你能不能跟她说说?”
“你?”电话那头,于东青沉默了一会儿,“自从上次你帮我查完那件案子之后,就一直不对劲。我早就让你去看看正规的心理医生,可是你讳疾忌医,偏不去。现在怎么又想起做心理疏导来了?我劝你,还是找个正规的心理医院去做下检查,这才靠谱。”
“我才不去医院,我又没病。”徐环烦躁地说,“我就是心理压力大,让你那个小姑娘给我疏导疏导就行了。”
于东青叹了口气:“真不懂你们这些人,去趟医院都扭扭捏捏的,又不是看男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得,随你便吧,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是私事,虽然我跟她是上下级,但也不能强令人家,我跟她打个招呼,把她的电话给你,你自己联系吧,行不行就看人家的意思了。对了,最近有案子,她可能会很忙,如果不着急就过两天再找她吧。”
徐环笑了笑:“行,有你这个顶头上司出面,人家还能不答应?”
“我一会儿给你发个短信……对了,我问你,昨天晚上十点左右,你有没有听到枪声?”于东青突然话锋一转,问道。
“枪声?”徐环一怔,“没有啊,十点……那个点我好像在听着音乐洗澡,有声音也听不见。怎么了?”
于东青压低声音:“你们小区昨晚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死了一个。你最近也注意安全。没事我先挂了,我还得补补觉,天亮了有我忙活的。”
挂掉电话后,一阵困意袭来,徐环躺在沙发上,又睡了过去。当他迷迷糊糊再睁开眼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徐环抬头一看表,立刻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今天是父亲出发去南美洲旅行的日子,虽然他与父亲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但作为唯一的儿子,去机场送别还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基本的礼节,即便是徐环这种不善交际的人也懂。
他迅速洗漱完毕,然后换上了几乎从没穿过的高级西装。在衣帽间宽大的试衣镜前面,徐环笨拙地整理着脖间的领带。身为祁东市最大的企业——远景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徐环虽不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但他也从来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镜子面前,只是父亲一向看重这些罢了。
定制的西装十分合体,镜中的徐环身材挺拔,衣冠楚楚,对于自己的形象,徐环非常满意,直到他看到那个奇怪的东西。在他的颈部,有一个小小的红色印记。他靠近镜子,仔细看了一下,竟然是个伤口,确切地说,是一个细微的划伤,血已经凝固,在皮肤上形成了一个不起眼的血痕。血痕呈现出小小的菱形形状,菱形里面有一个红点,乍一看像一只眼睛,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徐环搞了个无厘头的文身。
徐环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自己最近没受过什么伤啊,这玩意儿,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用手指使劲摁了摁,却感觉不到疼痛,可能是哪天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刮破的吧。只是这个血痕,似乎带着些邪气,看上去让人极其不舒服。再说了,自己打扮得人模狗样的,单单脖子上有这么个恶心的东西,确实有点不合适。父亲又是个疑心病那么重的人,万一再误以为这是跟哪个女人乱搞的时候弄上的,那就尴尬了。
于是他撩起水,使劲擦洗起来。只是用清水擦洗并不管用,擦了半天,血痕似乎像文在他身上一样,仍然清晰可见。徐环叹了口气,打算晚上回来洗澡的时候再仔细将它洗掉。他拿毛巾擦干自己的脖颈,竖起大衣的领子,尽量遮住那个菱形标记。
徐环挺直腰板,最后扫了镜中的自己一眼,然后满意地转身离去。只是,在最后匆匆的一瞥中,他似乎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嘴角幽幽上扬,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徐环的后背顿时渗出了冷汗。不过他并没有回头,而是快步走出了房间。
当接到于东青电话的时候,吴婷婷已经上床睡觉了。对一名刑警来说,深夜被叫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此,吴婷婷在选择这份职业的时候,就有了这种觉悟。不过,让她感到郁闷的是,于队长又是让她承担案件的监控录像清查工作,要知道,在别的局里,这种工作往往都是由警校实习生或者协警来负责的,而她一个堂堂公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却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一直从事这项工作。虽然她每次都完成得很出色,但是并不代表她喜欢,她一直期待着在某一起案子中,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谁都是从这些基础性工作开始干的。”于东青曾经郑重其事地告诉她,“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队长也不让我办案子,他交给我的工作只有一个:装订卷宗。当时我也有情绪,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应该到办案一线岗位上,整天订卷,那是小姑娘的活儿。不过等到我真正办案子之后,才意识到我们队长的良苦用心。订卷是为了让我了解整个办案过程,熟悉办案方法,积累经验,这样我才能在办案时有的放矢。”
吴婷婷点了点头,虽然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但是工作既然分到自己手中了,那就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
“就目前这起案子来说,你可别小看这些监控录像,这件案子,很有可能通过筛查录像破案。”于东青告诉她,“你的任务很重,我需要你连夜工作,最好能在天亮前查清凶手的外貌特征。”
分配完任务之后,吴婷婷就被于东青发配到了海西区分局的技术室。这里非常狭小,只有十几平方米。狭窄的空间内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计算机显示器、主机以及其他设备,显得异常拥挤;加上没有窗户,无法充分通风,整个房间充斥着烟味、体臭味和计算机那种电子设备所独有的味道,这几种味道掺杂在一起,实在称不上好闻。
吴婷婷虽然也是个爱干净的女生,但她并没有抱怨,仅仅皱了皱眉头,便集中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
这并非吴婷婷第一次承担监控视频的清查工作,只是这次需要查看的监控视频,无论是从时间长度,还是从精细程度来说,都要超出以往很多。仅仅是观海园小区内的监控,就刻录了三十多张光盘,这还不算小区周围道路的监控。
还好海西区分局给她配备了两个帮手,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干活的好手,而且吸烟吸得很凶,但总胜过没有。吴婷婷将整个监控视频分为三组,由他们三人分头清查。
清查监控视频,看上去非常轻松,实则不然,要想从监控视频中查出蛛丝马迹,不仅需要清查者具有相当的耐心,更需要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和敏锐性。用于东青的话说,能做好监控视频清查工作的警察,从事别的任何工作都没有问题。
当吴婷婷把监控视频仔细看了一遍之后,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她已然非常疲惫,一个劲地打哈欠。不过比起疲惫来,更让她感到郁闷的是没有收获。这一遍看下来,她竟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甚至连一些可疑的迹象都没有。
不过当她告诉她的帮手——两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警察——需要把监控视频再查一遍的时候,他们两人以一种“你算老几”的神情看着吴婷婷。这也难怪,作为一个二十多岁刚入职的女警,命令两个年龄和自己父亲相当的老警察,感觉总是怪怪的。
其中一位脸色阴郁地看着吴婷婷,口气里丝毫没有商量的意思:“吴警官,我心脏不是很好,再熬下去真的受不了了,我先歇一会儿,歇过来再继续查。”说完他便爬到了旁边的沙发床上,呼呼大睡起来。而另一位老哥则似乎觉得跟她讲话都是多余,连声招呼也没打,便径直推门走出了技术室。
吴婷婷很沮丧,不仅仅是因为两位中年警察的态度,更多的是因为没有发现线索。前几次清查监控录像,她做得非常不错,每次都从中发现了重要线索。吴婷婷定了定神,强迫自己喝了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然后又把精力集中到了手头的工作上。
监控画面大部分时间都是静止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走神。要想在其中发现线索,必须一直盯着看,哪怕只是分神几秒钟,都可能错过重要线索。吴婷婷努力睁大双眼,强迫自己集中精力,但是凌晨四点是困意最浓的时候,因此,虽然吴婷婷的眼睛还盯着屏幕,但头脑早已一片混沌,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
突然,技术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了,一个瘦削的身影走了进来。吴婷婷顿时打了个激灵,她凝神一看,来人竟然是法医卫毅平。
“卫毅平,你不赶紧去检查你的尸体,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吴婷婷睁大眼睛,瞪了卫毅平一眼,没好气地说,“告诉你,姐姐我忙着呢,没工夫搭理你。”
“忙什么,忙着睡觉?”卫毅平一脸的坏笑,“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可是看到你的鼻子都快贴到桌面上了。”
吴婷婷冷哼一声:“我忙着干什么不用给你汇报吧?说吧,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喂,干吗这么一脸嫌弃的表情。”卫毅平环顾了下四周,压低嗓门说,“其实我是来帮你的。我问你,想不想立功?”
“立功?”吴婷婷狐疑地看着他,“立什么功?”
“当然是周远这起案子了。”他抬头看了眼吴婷婷眼前的监控屏幕,不屑地哼了一声,“嘿,别查了,这玩意儿,一点用也没有。”
一听自己的工作被看低,吴婷婷心生不悦,冷冰冰地说:“不试过怎么知道,再没用,也比你在这儿无所事事地闲逛强。”
“真的,”卫毅平一脸的认真,“我把话放在这儿,这个案子要是能通过监控找到凶手,我下个月就光着膀子上班!”
吴婷婷嫌弃地瞪了他一眼:“得了吧,你还是别污染大伙儿的眼睛了,就跟大家多稀罕看你光膀子似的。于队说了,这个案子监控很重要,凶手的行踪,一定会被监控拍到。”
卫毅平弯腰把脸贴近吴婷婷:“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极其隐秘的线索。”看吴婷婷斜着脸不搭理他,语气又增加了几分神秘,“不瞒你说,我在死者尸体上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他瞥了眼吴婷婷,“怎么样,感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吴婷婷白了她一眼,然后扭过头又看起了屏幕,不再搭理卫毅平。在吴婷婷眼中,卫毅平是一个油腔滑调、没有正形的主,尽管现在很多小女孩都喜欢这种坏坏的贫嘴男生,但是吴婷婷却非常反感这种满嘴跑火车的人。
卫毅平有些尴尬,他愣了一下,随即又嬉皮笑脸地贴上来,神秘兮兮地说:“我在死者的尸体上发现了一个很隐秘的痕迹,看来这起案子,没那么简单,搞不好……搞不好牵扯什么大的阴谋。”
吴婷婷转身看着卫毅平,不耐烦地说道:“卫毅平,你电影看多了吧,你要真有事就正儿八经说,没事赶紧走,我这儿忙着呢。”
卫毅平啧了一声,一脸的无辜:“嘿,你这人,我是看在咱俩同年参加工作的分儿上,想帮你一把,没想到你不领情。我告诉你,死者身上,真的有个很奇怪的痕迹。”他眼珠子一转,又说道,“这可是非常隐秘的线索,顺着这个线索调查,或许会发现什么呢……”
吴婷婷揉了揉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那死者身上到底有什么痕迹?文身吗?”
卫毅平压低声音说:“No,No,不是文身,应该是……用锐器在身上划的标记。”他扶了扶眼镜框,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我感觉这个标记不像是意外划的,肯定有它的特殊意义。”卫毅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吴婷婷,“我拍了一张特写照片,你看看。”
吴婷婷接过照片,当她看到照片里那个类似菱形的血痕时,她感到后背一阵发凉,心里极其不舒服,仿佛那是一只血红色的眼睛在盯着自己。她略微颤抖地放下照片,一阵寒意席卷了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