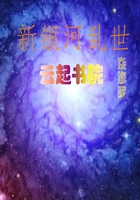年夜饭上好多人醉了,包括姜九生和常凭亦。陈步长是想醉没法醉,毕竟这位祖宗得管,现在还多了一位要处理的常客。
众人散去,有醉的女眷携回家,半醉未醉的尽了兴皆满面春风回家,嘴里絮絮叨冒着酒泡,姜九生看起来是属于半醉未醉的,可能是姜九生即使喝大了也不犯浑不撒酒疯,人喝醉酒的表现有很多,譬如常凭亦那种喝大就睡的,姜九生这种越喝越沉默的,还有其他人喝完话不尽的。陈步长先把姜九生扶进房间,姜九生还有些意识,自己脱掉脏衣鞋履一屁股坐上床塌,感觉脑袋昏昏沉沉似有千万斤重,他晃了晃头只感觉漫天繁星,疼痛感袭来,只是仍旧一声不吭猝然起身走向屋里的大长桌,桌上有一灯台,台面上摆着一个吹笛儿童,姜九生一把拿过拽在手里盯着,陈步长看着姜九生迟疑一会,觉得他自己应该能行,就连忙梢门出去清理外面的一团乱。
常凭亦仍旧未清醒,倒在餐桌面上大睡。下人自然小酌半杯不敢喝的,现在吃完饭都得忙于收拾,期间直接避开熟睡的常凭亦小心收拾桌面,仿佛给他划了一道圈,圆圈里的他不可触碰般。陈步长搞定姜九生从别院绕回来,看一眼残局然后径直走向脸贴在桌上的常凭亦,喝大了睡着还能这么潇洒的模样,英姿飒爽的人当真让人羡慕,陈步长把常凭亦右手抬起扶到自己肩上,从左侧一个用劲把常凭亦撑起,还是一副昏迷的样子,眼皮都未曾睁开看一眼,陈步长纳闷了,这两人到底是被灌了多少,当时自己不就坐在旁边看着的么,居然忘了!
好在先前就让人把客卧收拾出来,否则这会常凭亦真是个烫手山芋,总不能任由他不管吧,可也没个同路的把他带回家,陈步长暗叹一声,老大不小是该娶个贤惠的回来了,他这条件也不差,大把姑娘肯定追着上门,怎么就不好好挑挑?现在也不至于落的别人家手里,好在还是姜九生家。陈步长把他驼进客卧,直愣愣地放到在床上,“咚”一声险些磕到床头板,不比姜九生,这个完全没意识,陈步长耐心弯下腰替他脱鞋,连同外衣一同扒了扔在椅子上,也不管什么四仰八叉的姿势了,直接推门就走了,这要是其他人保准直接随之去,倒哪躺哪,陈步长哪还会管?懒的。
第二日常凭亦早起,站在客卧外面一动不动,险些吓到从隔壁自己房间出来的陈步长。
“常馆主怎么起这么早?”只是醉酒的表现吗?陈步长惊愕。
“头疼的睡不着。”
“感觉不好?”
“晕。”
“这一般醉酒都是蒙头大睡直到第二天正午,你这是睡够了?”
“我不会睡懒觉,喝醉也不会。”
“昨天可是特意换的蚕丝被,您可别怪是姜家的床不好睡啊!”
“哪里,步长,昨晚九生......”
“还不一样是醉了,就是醉态稍微好点。”
常凭亦扶额,还是觉得五分痛三分晕,看着蓝天直刺眼。
“走,吃个早饭就不痛了。”陈步长拍拍常凭亦的肩,拉着他一起朝前院走去,“昨晚吩咐过厨娘今早起来就煮上醒酒汤,待会喝点。”
果然,前院大桌上已经摆好早饭,种类繁多数量倒是正常两个人的量。
常凭亦随意刮一眼低声开口道,“这是做少了吧?”
“不少,我们两个应该够吃,您不会是个大胃吧?看不出来呀。”
“我的意思是,其他人不一起?”
“他们都吃过了,姜九生的份是单独送进别院的,所以除了我们两个不做事的还有谁敢陪我们坐在这慢慢吃早饭?”陈步长笑笑顺手拿起一根油条放在嘴里叼着,说自己不做事其实是自嘲,他待会就要赶去码头监工,先填饱肚子重要。
“他的单独送?”常凭亦坐下没急着拿筷。
陈步长自然知道他指的是谁,“当然,估计这会还不行,太早估计还没醒,毕竟好久没看他喝这么多酒。”
“没问题吗?”
“什么?”
“一下子喝这么多。”
“没办法,昨晚他不让我管,我等会连着醒酒汤和胃药一起送进去,早上厨娘也给生爷煮的清粥,养养胃喝粥舒服点。”陈步长半截油条下肚,还有半截捏在手里开始低头大口喝上热乎的豆浆。
“你急着去码头开工吗?”常凭亦先喝的热豆浆暖暖胃,说话间仍在挖勺喝,其实这样不好,得先吃点东西垫垫胃。
“还好。”
“等会你先走吧,我帮你送进去。”
陈步长挠挠头,踌躇片刻偏过头看一眼常凭亦,“也行。”
姜九生不比常凭亦,醉后无法早起但也醒的不晚,陈步长已经离开一个时辰多姜九生才睡眼惺忪的模样打开房门,一开门就看见坐在庭院里发愣的常凭亦左右晃着脑袋,听到动静指指面前的托盘示意姜九生。
“怎么是你?”
“陈步长去码头了。”
“你起的挺早。”
“头痛睡不着。”
“吃过了?”
常凭亦点点头,眼皮上略微泛红,像蚊子行过之处,“先把醒酒汤喝了再喝些米粥,陈步长交代的胃药要我看着你吃下去。”
姜九生不多言,拿起瓷碗一口闷下,难喝的东西先解决,放下碗后停住片刻又拿起粥里的瓷勺,感觉没什么胃口,可对面常凭亦闲情逸致地坐着不动,姜九生还是没有多犹豫直接咽下一大口。
“昨晚你说再约时间聊聊,择日不如撞日吧,看你今天也没什么事情的样子。”
“我是没事,可今天可是大年初一,你好歹收拾一下要见人吧,陈步长说他中午回来,另外刚刚你家亲戚来过,昨天年夜饭上没瞧见过,东西我带你收下了,就跟他们说你还没起他们喝两口茶就不多留了。”
姜九生听着显得无所谓,单用鼻音“嗯”一声,全然没把常凭亦当外人。
“我今个空手在这不好吧?”
“那你出去。”
姜九生换身行头,又一条新衣。只是刚换好衣服大堂就络绎不绝来人,压根没有空隙时间跟常凭亦坐下好谈,常凭亦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姜九生只是没在人群中找到那抹鹅黄色影子。
常凭亦闲走在大街,街上今日人少,店铺大都歇业,谁这么拼大年初一还在外忙碌,那可真是劳碌命了,也就长胜码头这一类的支柱产业不能完全走开放掉,所以大过年的长胜的门还大敞着,陈步长就在其中。
脑袋不晕了,常凭亦还记着昨晚饺子的事情,正好这几日有空,就是菜难买得靠抢,不过他就买点馅的菜还是简单的,想罢常凭亦直直朝菜市场去,也就这几日菜最好卖也卖得最好。
正午时分,陈步长准时归来,厨娘给他留饭他就在后院的石桌上将就干掉三大盘饺子,蘸着家乡的辣子酱别提多有味儿,“刷刷刷”盘子光速见底,把嘴角的辣油一抹就往姜九生的别院赶去,还好中午家里没有客人留着吃饭,不若然他早就被招回来了。
姜九生倚靠在木椅上,庭院的凉风阵阵,吹得人心痒痒,桌上是一些散落的礼盒,大都相似的糕点油米陈步长昨日收到时看一眼就甩到后院里摆着,其他看似正儿八经的东西都放到庭院桌上,就是现在姜九生面前的一团乱。
“下回你拆吧。”陈步长听出姜九生话里的无奈,应该都是些姜九生眼里的垃圾,对他没有用的都能被随意丢弃,管他是黄金百两还是上古收藏品玩件儿。
“我给您收拾掉吧。”陈步长讪讪开口,也没辙。
“你过来看这个。”
陈步长走过去仔细一看,原是一副水墨画,寥寥大山直插入皑皑白天,飞禽走兽围困在半山腰间,旁边特别提笔著明画的是溪滑山,当地有名的景山,以出珍奇异宝闻名天下,揽来不少游客驻足攀登,最左下的名字写的是张大千。
“这幅画......还行。”陈步长看不懂水墨画,之所以是还行只因为三个字“张大千”,张大千是溢城曾经数一数二有名的画家,与其他一个并非溢城的合称为无独有偶,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人们对他们的赞誉度很高,陈步长以前跟姜九生去拍卖会有幸遇过一次,当时张大千的一副画拍出的价格惊为天人,想来尺寸还没这幅的一半大。
姜九生忽的笑出声,“你觉得还行?”开口就是一句反问,问的陈步长措手不及。
陈步长踌躇一会还是觉得没有问题呀,水墨画不都是这样吗?
“你觉得行那就送你吧。”姜九生麻利卷起画轴递到陈步长面前。
“不用生爷,万一是副名画我可不敢要,这可是人家给您的。”
“不用客气,这画在你那才能被叫上名画。”姜九生仍旧笑意浓厚,陈步长知道这句话有打趣的意味,可不清楚生爷为什么对一副好端端的水墨画打趣?
“别说张大千是以画纸不过一米闻名,就算是单看这幅画也全是纰漏,要是张大千在世八成还得气死。”姜九生这样一提醒,陈步长倒是觉得不对劲起来,开始重新审视这幅水墨画,“且不说溪滑山并不巍峨,但画家都知道,尤其是作水墨画的,溪滑山以山之层次分明,色拢四季种八方的树开四海的艳花名誉天下,水墨画是做不出它最重要的色如四季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就还没有见过有人画水墨溪滑山的,何况这山顶入云还飞鸥鸟,岂不笑话。”
姜九生虽从不收藏这些艺术品古董名画一类的,可也并非毫不知情,稍微一眼就知道这是副赝品,还次得很。
“谁拿来的东西,真是让您看笑话来的。”陈步长摸摸自己的木鱼脑袋,姜九生一讲还真是这么回事,假的不能再假一点。“我记着好像是邵越吧,他来的时候有拿个类似这种板的东西,打包好还是看得出来。”
“邵越?他什么时候对这种水墨画感兴趣了?”
“不一定,说不定也就是奉承您一时买的,估计也是遭人骗的。”
姜九生沉默不言,示意陈步长把桌上的东西都收干净,自己则进房准备午间小憩一会,真是越睡越想睡,睡多反而困,一把懒骨头的感觉,酒劲还没缓过来也罢,又听人絮絮叨叨一上午,简直耳朵生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