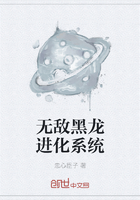软玉人长得出挑,玲珑剔透,办起事儿来麻利周全,最讨喜的是稳而不闷的性子,什么都拿手,却偏是个不喜张扬的女子,谦虚谨慎,横竖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丫鬟。
她的笛声配上药王的马头琴,让我意外的有一种置身大草原的错觉。那种如临其境的震撼,让我不禁感叹,一个江南水乡的奴仆,是如何将大草原的豪放苍凉表现的如此的淋漓尽致。
“软玉姐姐可去过大草原?”待二人合奏完毕,我好奇的问道。
“不曾去过,年幼时,在父亲的书房有幸读过郦道元先生的《水经注》,心向往之。”她笑了笑,继续道,“后来听游方的先生提起过科尔沁草原,他说那里牛羊成群,白昼分明,骑上一匹快马,便可追赶星辰,若是有机会,我也很想在蓝天白云下自由的纵马驰骋。”
当提到科尔沁草原的时候,她整个人完全不同了,两只眼睛烁烁放光,感觉整个世界都被点亮了,让旁人都能立刻沉浸入她的喜悦,体会到她发自肺腑的热爱和向往之情。
“一定会有机会的。”我鼓励道,“不过,是九爷让姐姐来照顾我的吗?他的伤怎么样了?”
我还记得他舍命救我受了重伤的样子,也同样忘不了他抛下垂死挣扎的我的样子,软玉会离开济南来照顾我,说明他早已无碍,不过我还是想要“明知故问”。
“三个月前,就是九爷救下姑娘的那天,爷的家了出了很大的变故,家里主事的哥哥暴毙,重伤的他连夜遣散了小竹居众人,赶回老家治丧。爷临走前将我送给了姑娘,特意叮嘱我今后务必好好照顾姑娘。”
说到此处,她蹙眉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九爷的伤势怎么样了,自上次一别后,九爷他全无音信。”
“不过……”
吐出一个转折词后的软玉眉心舒展,瞬间恢复了笑容,“九爷他是个好人,好人一定会逢凶化吉的。”
原来,是家逢巨变,怪不得那天走的那么匆忙。连济南别院的下人都遣散了,看样子,是不会再回来了吧。
原来上次一面,真就成了永别。
“留下软玉姐姐,凭白又让我欠他一次,他舍命救我,我却连一句谢谢都没和他说过……”听罢,我失落的说到。
软玉握住我的手,劝解道,“姑娘和咱们九爷的缘分深着呢,定还有相见之日。若是姑娘有什么感谢话,就留在心里,等到下次再见,当面告诉九爷吧。”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这天,马上就变了……”
我倒不是故意说出这样丧气的话来,时代的更迭近在咫尺,今后我该何去何从尚不可知。大明不亡,我这个公主都要逃出皇城才能保命,若是清军入关后,身为前朝欲孽的我还能活吗?
不知为何,我说出这句话来,软玉和药王的脸色齐刷刷的暗淡下来,似乎是各怀心思。
“变什么天?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嘴里,眼里,心里都挂着一个二十多岁的老男人,你害不害臊?”药王不高兴的怼道。
“您胡说什么呢!九爷是我的救命恩人,前前后后救了我四次了,我感念他的救命之恩,在师叔的眼里,怎么就成了龌龊的事?”
“呵……我说明明就是你这个丫头思春了。”药王喝了一大口酒,笑道,“你昏迷这三个月,每天都在梦里重复的叫着一个名字。”
我像一个有故事的女人,提起酒壶,也喝了一大口,浅浅笑道,“是冷寒竹吧。”
“嘶,这个名字倒是出现过几次,不过不是。”软玉捂嘴笑道,“姑娘一直在梦里唤着九爷。”
我的脸腾地一下烧了起来,耳根子都烧的滚烫,“胡……胡说!”
胡说!
就算我变心了,不再爱齐悦,午夜梦回时喊的,也应该是私定终身的冷寒竹才对,为什么有了心上人不叫,反而叫九爷,那个只有数面之缘的人?
“姑娘不必不好意思,我跟着九爷也有十年了,从来没见过爷对哪一位姑娘这么上心过……”
“听软玉姐姐的意思,九爷身边有很多姑娘?”不知为何,听到这里我竟有些反感,于是打断道。
“九爷今年二十有八,大夫人进门已有十三年,除大夫人外府上还有三个夫人,嗯……还有不少的红颜知己。不过,爷对姑娘,真的特别……”
软玉掰起指头细细的计算着,看着她觉得理所应当的样子,我不禁觉得有些悲哀。
穿越这么久,我倒是第一次想起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在这个时代,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不过是一个随时可被替代的物件儿罢了。
想到这里,我第一次将冷寒竹和九爷做了一次对比。既然我不愿在这里孤独终老,那我究竟愿意和什么样的男人共度余生?
是像冷寒竹这样有可能接受一夫一妻制的人,还是九爷这样妻妾成群的“普通男人”?
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我与齐悦的过往,我所经历的一切,我的本心,都不能接受一夫多妻制,我根本想象不出和别人分享爱人的痛苦。
可是在小三横行的现代都不易做到的事,在封建迂腐的古代,我有可能遇见那个愿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他吗?
我一定要坚信,冷寒竹就是这个人!若是我已在动摇,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
“九爷艳福不浅,真是让人佩服不已。”我笑道,“夫人们也是好福气,能够遇见九爷这样义薄云天的好人,不像我福薄。”
闻听此言,软玉连忙道,“姑娘……”
“我与冷公子……”我假装害羞的低下了头,“九爷他为了救我受了重伤,我心里自然是非常感激的。”
“是我僭越了,姑娘和冷公子郎才女貌,十分般配。”软玉道,“可是公子现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一定会来这里找我……”
药王一直默不啃声看着我俩,“冷寒竹?莫不是师兄的那个傻徒弟?”
“师叔您认识他?”
“哼,那块儿榆木脑袋,和我师兄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老夫可是亲自领教过,一根筋!我劝你啊,还是乘早死了这条心,不然日后有你吃不尽的苦头。”说罢,他仰面躺了下去,抓起一旁的蒲扇,悠哉悠哉的扇起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