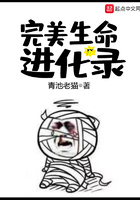半年前,哥舒翰提议在湖心岛修筑应龙城,极言此城军事价值,可堪刺入吐蕃身体之匕首。圣人重视河西防务,首肯。于是鄯州刺史调集人马火速修城,并担当着为应龙城供给物资的职责。
“我阿兄岑况正是建城者之一。”岑参道:“半月前哥舒翰带队返回应龙城,途经鄯州便歇息一日。那时我阿兄正在鄯州,他知晓我要去应龙城,便拉着我讲述了该城城防要塞、营区布局以及守备重点。我自觉是小卒,并不需要听这些事,正不耐烦,他却正色向我诉说了这夹城的秘密。”
“应龙城建在湖心龙驹岛,与别处不同,其夹城本意用做排水防洪,所以才这般地狭窄也并无人迹。工匠们修筑好内墙,留了一方出口。本准备修补妥当,却想到应龙城四下被青海湖所围,日积月累盐湖浸泡,恐怕少不了修补。”
“几名工匠经过商议,决定在城墙内留下一方暗口。他们加固了周围承重,砌上易于拆除的轻砖。既不会影响防御,也方便日后维护。”
王维奇道:“那便是我们进入的暗口吗?你兄长难道早知此劫,所以才将此告知你?”
岑参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答道:“阿兄素来疼爱我,他说龙驹岛四面无援又深入吐蕃,若是有朝一日敌人将应龙城围死,城内唐军恐怕只能死战。他将这暗口的方位告诉我,说若真的有那么一日,要我定要藏入其中,保住性命。”
“真是好兄长。”王维感慨。颜真卿也附和道:“若是不知这夹城的秘密,我们恐怕都得殒命于此。”
岑参笑道:“我曾在往返鄯州的粮车上留下诗文,只有兄长能解其意。适才出去核查,发觉已有回音——明日鄯州运送补给的货船将比平日更晚到,也会借故在此多停留半个时辰。那时,便是我们逃出生天的良机。”
王维沉吟片刻,问道:“你救走清臣,哥舒翰竟未搜查追踪吗?”
“当然不会。老贼怕歹计泄露,昼夜搜捕了两个日夜,大雪里火光耀地半边天都亮堂!我们亦未能饮食。到了第三日…”岑参的声音中多了些许讶异。
“第三日,搜查的人突然收紧,城内竟然安定下来。我担心是计,可饥渴难忍,只得深夜溜出夹道寻些吃食,也须择机在粮车上传信。后半夜寒风难耐,巡夜人也多在浑水摸鱼。我捧着汤和胡饼,抹黑潜入粮车附近。拿出匕首正欲刻字,却问到不远一架盖着帆布的粮车里传出丝缕腥臭。我看四下无人,便壮起胆子借着月光掀起那帆布,竟是两人尸首!”
“上天眷佑我二人。”岑参的声音颤抖,仍在为那夜的发现而恐惧。“那两具尸首被湖水浸泡地浮肿不堪,衣着残破皮肤溃烂,竟也看不出面目。我写罢诗文,惊魂未定地逃回夹道。回过神来才想到,这两具尸骨恐怕是守军自青海湖中打捞出的。正因这尸骨,哥舒翰那日之后才未对我们继续追捕…”
王维惊讶道:“你是说,哥舒翰将那两具尸骨当成你二人。”
岑参叹息道:“是的。那两具尸骨与我们形体相仿,其中一具左肋亦有贯穿刀伤。他们被放置在运粮车上,想必是准备经鄯州,被送回长安的。”
“许是两个鄯州人或私逃的军士?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王维咋舌道。“简直如有神助!”
岑参苦笑道:“我只当是吉人天相。幸而尸首随粮车送往鄯州,兄长也看到了我在车上的题诗。那日过后,哥舒翰便率众出城去了。”
众人安静了良晌,忽听王维道。
“岑参,清臣,明日我不能随你们回去。”
“啊?”岑参惊讶道。“王御史!你已重伤至此,还留在此地作甚?”
王维捏紧几枚今夜寻得的小木罐,黯然道:“实不相瞒,我来应龙城是为寻找哥舒翰与祆教暗中交通的证据。他位高权重,即便我们回到长安,若无证据也伤不动他。”
颜真卿也劝道:“摩诘,你说得没错。我也想过这一层,可一来,这物证并非能轻易得到。再者…”他顿了顿,努力压抑住咳声。“现在并不是弹劾哥舒翰的好时机。”
王维愣了,他确实没想这些。问道:“怎么讲?”
颜真卿将他几日的思虑筹谋娓娓道来:“如今河西、陇右名将,除大将军王忠嗣外,只有哥舒翰一人能够与之比肩。可谈及政治手腕的老辣精明,后者却更胜一筹。”
“即便找到证据,就能弹劾哥舒翰吗?我看未必。于公,圣人还需要哥舒翰这员大将统领河西,抵御吐蕃。于私,即便视王将军为假子,圣人也不情愿见到节度使一人独大。”
王维听得惊讶,生出万分敬佩,他自觉思虑远不及颜真卿之缜密。他虽不情愿,但忽然想到未来的石堡城一战王忠嗣恐怕命途多舛,大唐西侧防务终究要交到哥舒翰手中。于国于民,现在都不是扳倒这员大将的好时机。
可“大圆满”已害了无数边民,这祸乱绝不能再拖延下去。王维拧起眉,思虑片刻道:“既然哥舒翰动不得,想必只能自祆教入手了。”
颜真卿赞同道:“不错。哥舒翰虽已暴露,但祆教还藏在暗处,亦须提防。我一路行来,也在边民口中得到了些许线索。”
“传教者通常一行四人,身披银线绣成火纹的皂色长袍,戴着獠牙长角的面具。在传教时,为首那人会摘下面具。而据我在几个村子收集的消息再三推敲,那名为首的传教者,是个女人。”
既诱人,也危险。王维心里一怔,女人的厉害他早在玉真那里领教过了,问道:“可有什么特征?”
“有,不过也可笑。问到那人特征,好多村民只说了一个字…”颜真卿道。“白。”
王维的心如巨石投入静水,“哐”地一声摇曳起巨大的层层波澜。他的脑中如同鸣起锣鼓,心中似琢磨岩石,完全慌了神思。
王维狠掐自己掌背一把,强行定住心神,声音却仍打颤道:“白,这算什么特征?”
岑参接话道:“若说在中原,女子肤白确实算不得特征。可在这安西高原,边民整日经受日晒风吹。能够用‘白’来形容女子,却实在是十分难得。”
“而我确实也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王维急问“是谁”。即便他心中暗自祈祷岑参不会说出那个名字,可最终还是令他失望了。
“哥舒翰的女参军,念奴。”
“不可能!”王维咆哮着,这声音来自他身体每一寸的力量,他想用尽自己的力量为念奴辩护。“今夜正是她舍命将我送至应龙城,半月前亦是她在番禾那场大火中救下我!她怎会是哥舒翰的爪牙?我不信!”
“可…”岑参低声嘀咕了一声,也不再说了。
众人沉默了许久
“咳,咳咳。”颜真卿咳了几声,打破沉寂道。“摩诘莫要生气,我没见过那念奴,想必岑参也只是胡乱猜测。单凭这一项特征,实在是难以揣度的。”
岑参却赌气抢道:“我可不是乱猜!要是不信我,你便自去看看,这高原之上有多少肤白女子?念奴是哥舒翰手下参军,为何不能怀疑她?”
几次被念奴出手相助的人,毕竟是他自己。王维自知不可强加于人,也不愿念奴被污为祆教恶徒。他藏在黑暗中,不再答话。
岑参怒火渐消。想到自己毕竟不知王维经历,若那念奴果真是他的恩人,自己这样唐突指责,只怕会让王维心寒。
岑参想到此处自觉失言,又碍于情面不愿道歉。他站起身别上横刀,接过颜真卿手中的火折子轻轻吹燃,在火光里向二人道:“已近四更了,我去军营里寻些吃食,再看看有无药草。”
他向暗口出走出几步,突然停下,又转回身子,低声道:
“抱歉啊,王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