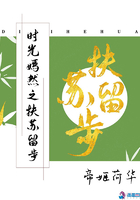江羽臣把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仍在桌子上,坐在宽大的转椅里,把两只手枕在脑后,轻轻得闭上眼睛。
“这个王总到底耍得什么花样?” Seven在江羽臣对面的椅子坐下。
“那个人查得怎么样了?”
“就是建筑公司的,姓王的要拿点回扣,我们手里虽然有录像,可是没有他们交易的确凿证据,账面上一点都查不出来。”
“他这次联合董事会催促这个项目开工,应该不会只是着急拿到提成那么简单。”江羽臣清淡得说。
“江总难道认为他还有别的事情?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开工是早晚的事情,我们僵持在这里,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几位股东恐怕又要生事,我们不能还见不到老虎,自己就先乱起来。”
“好,那我去安排。” Seven起身。
“该来的总会要来。”江羽臣喃喃得低语,仿佛在自语。
Seven转过身来看着他,江羽臣抬起眼帘,摆了摆手。
一周以后,这个占据京城瞩目地段的被规划为智能、减排、绿色的高端楼盘——紫澜花园在万众瞩目下开工了,听说这里的每幢楼都装有德国进口的中央空气净化系统。在布满铅尘动不动就雾霾的北京,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卖点啊。
江羽臣拿起绑着大红花的土锹在无数闪光灯和镜头下装模作样得铲起第一捧土。他身后长长的舞台上,徐澜微笑着像看着一件艺术品一样欣赏着她同样万众瞩目的儿子。就像我们小学开家长会一样,从家长的就能看出谁的小孩考了第一名,而江羽臣让徐澜把这种自豪的微笑保持了二十年。她大概就是因为常年都挂着这样的笑容,所以才不会老吧。
我在舞台下的角落里,看着台上皮肤光滑没有一丝皱纹的徐总,那只陪着我做白日梦的小兔子跳出来,“要不要和江羽臣生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一定会继承他优秀的基因,到时候自己也这样牛气掰掰的嚣张无极限,会不会也长生不老啊。”
“是啊,是啊,一定会的。”
“可是如果孩子不像爸爸,像妈妈可怎么办?”
我头上瞬间无数条黑线,“不会,不会,越优秀的基因,遗传力也会越强。”
“好吧,就算你说得是对的,可是你要怎么生孩子呢?你不是偷偷得在小气球上扎窟窿的事情,是江大少爷根本就不会碰你。”小兔子龇着牙露出一脸邪恶的嘲笑,我美丽的白日梦像玻璃一样咔嚓咔嚓得碎了一地。
我沮丧得陪着江羽臣折腾了一天,如果你想说林菲,江大少都带着你出席如此重要的活动了,你都公开亮相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么。那我可以如实得告诉你,现场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把我误会成江大少的女朋友、未婚妻、情妇甚至是贴身助理一切能和他扯上任何关系的女性。因为我穿着一身黑西服,怎么看都像是Seven的助理,不跟班更贴切一些。而且我还不能提出丝毫反抗,因为是我软磨硬泡得磨了一个小时,他才同意我到现场看他头戴安全帽、举着土锹的样子。结果我发现穿着Givenchy的江羽臣戴不戴安全帽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那天我们住在紫澜花园对面的酒店里,从12层的落地窗看下去那还只是一大片诱人的空地。在北京三环以内,一间空着的门脸房都让人流哈喇子,何况这么一大片空地。我和江羽臣并排站在窗前,我们畅想着两年或者一年以后,我们的眼前就是北京城最高端、最让人想往的住宅,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在那里的落地窗前,看我们今天留在这里的倒映。我偷偷得看向江羽臣,他漆黑的眸子闪着亮光,像期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期待着从脚下拔地而起的高楼。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过,不久之后这里散落着建筑垃圾,盖到一半的楼房荒芜在这里像一个流产的孩子。
江羽臣伸手揽过我,他的下颌垫在我的头顶,我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真丝衬衫,隐隐得可以感受到他胸膛的温度。我的头发摩挲着他的衬衫,他全身的温热变成一股涓涓暖流流进我的心里,我转身抱住他窄紧的腰身,我明显能感到他的身体微微僵硬起来,因为我是从来不会主动和他的身体接触的。我的耳朵紧紧得贴在他的胸膛,我听到胸腔里混乱的心跳一点一点得变得沉静有序,江羽臣轻轻得拍了拍我的背,然后柔声问到:“你怎么了?”
我在心里冷笑,我怎么了?我是你的女朋友,我抱一抱你还要问我怎么了?但是此刻我不想生气、不想吵架,我只想抱着他,可是重温那种久别的温暖的同时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在无底的悬崖越坠越深。
我轻轻得摇了摇头,“我只想抱抱。”
他笑一笑,双手扶着我的肩膀,在我的额头落下一个轻轻的吻,然后揉揉我的头发,“早点睡吧。”他松开手,转身走进卫生间,所有的动作都那么沉稳有序,可是我依旧能感到他脚下明显加快的步伐。
我站在原地,身后是深夜里璀璨的霓虹,为什么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流转的温柔和最深沉的依恋,可是从却无法得到他的温情。
忽然我的下腹传来一阵阵绞痛,我痛得蹲下身子,眼眶里莫名其妙渗出来的泪水,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难过。
江羽臣走出来看我蹲在地上,一把抱起我,“林菲,你怎么了?”
我打开手机看了看日历,应该是我的大姨妈要来光顾了,平日里我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即便有喝一点热红糖水也就没什么了,可能今天外面冷又穿着高跟鞋站得久了些。
“没什么的,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我顺手揪起身下的被子。
江羽臣一声不吭得翻着手机,他不断的再百度的搜索栏里打下“女生来例假肚子疼”的关键搜索词。十几分钟后,他好像出师了一样,跑到卫生间里转了一圈,然后我就听到哗哗的水流,他跑过来拽起我,“我找不到脸盆,你就再澡盆里泡泡脚,这样会好很多。”
我看着洗手间半洗澡盆的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我刚要坐下,他又马上制止我,然后拿了一块浴巾垫到澡盆边上的大理石上,“石头凉,这样会好些。”然后他又跑进来再我手里塞了一杯热水,“没有红糖,你先凑乎喝着。”
我欲哭无泪得把脚伸进热水里,真的很舒服,想到白天他是万人拥戴的江总,却再这里倒洗脚水,我不禁笑起来。
我泡脚的功夫,他又跑到外面,客房服务打了无数次,不是要红糖水就是要暖水袋,连阿胶都要了。折腾了几分钟,他终于放弃了客房服务,我见外面没了动静,开始喊他,我想告诉他不用这么大惊小怪。
他走进洗手间,对着电话另一边的Seven说,让他赶紧送红糖水和暖水袋过来,Seven迷迷糊糊得声音忽然变得尖利起来,“不是吧,老大!林菲要分娩了?”
我一口水喷出来,剧烈得咳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