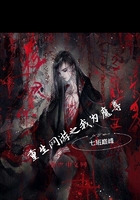“这里可是扶先生的铺子?”见玩闹的少女和一脸墨迹的蒙眼男子,他似乎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
扶朝低头轻咳了声,对秦夕喊道:“秦夕,招待客人坐下,我去去就来。”
秦夕只害怕那些面目狰狞地鬼魂,这位先生长得好看,她倒也无所谓了。
她拉开扶朝对面的座椅,先生坐下,转而去茶桌上沏茶。她把茶杯放到那位先生桌前,却被婉拒了:“贺某早已不是这世上的人了,这茶,怕是无福消受。”
秦夕温婉地笑笑:“先生放心,铺子里的茶是给客人准备的,天地万物,均可享用。”
他听了,接过茶:“那多谢夫人了。”
被误认成扶朝夫人,秦夕摆摆手:“我不是……我只是……”她找到合适的词,说:“只是这儿的女工。”
扶朝再出来的时候,脸色的墨渍已经清洗干净。在那位先生对面坐了下来,他问道:“不知先生怎么称呼?”
“鄙姓贺,名锦书。”
扶朝又摆出了那副商人的姿态:“贺先生今日光临,要买卖什么?”
“我听闻,扶先生这里可以寻人……”贺锦书停顿了一下,又改成:“寻魂。所以,想请先生帮忙探一个人百年后的去向。”
扶朝笑笑:“小事。贺先生有要寻之人的贴身物件吗?要那人的去向,少不了她的气息。”
贺锦书打开了皮箱,里面原是一套大红戏服,看得出有些年头了。
“这身戏服是我母亲的遗物,但后来我赠与她了,她曾穿过,不知道算不算……”
“算。”扶朝一口应了下来,随后又道:“可寻人之后,这身戏服作为交易要留在我铺子里。”
秦夕白了扶朝一大眼,他不缺吃不缺喝的,找个人还要人家母亲的遗物!奸商!绝对是奸商!
贺锦书抿着唇,犹犹豫豫的样子。过了许久,他覆在皮箱上的手总算松开了:“好。只要扶先生找到她的音讯,戏服就归先生。”
扶朝满意的点点头,他冲贺锦书面前的茶杯抬了抬手,说道:“那贺先生请饮茶吧。”
贺锦书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正伏在一张方桌上,四周都是闲聊声,叽叽呀呀的戏曲涌入耳底。
他一望,是苏州梨园。自己莫不是在做梦?
“唉,这新角唱地就是没有梁浅姑娘好。”旁边桌上的男子向同伴说道。
听到梁浅的名字,贺锦书蓦地回过头。只听男子的同伴有些惋惜地说:“可不是嘛。唉……嫁了张家公子,怕是以后都听不到咯……”
贺锦书闻言,猛然站起身来:“你方才说,梁浅姑娘嫁了谁?”
“嫁了谁?整个苏州都知道,张家大少爷娶了昆曲名伶梁浅。”
“张茂生?不……这绝不可能……她怎么会嫁他……”贺锦书不信,连连摇头。
男人不耐烦极了:“我说你这少年郎,这人尽皆知的事,我骗你做什么?”
少年郎?贺锦书望向茶盏里,里面俨然是个十四五岁的陌生面孔。
他一惊,明了这一切皆是那位扶老板所为。他沉下心来,问道:“不知贺家三少爷如今何在?”
“三少爷……”男人思索了一会儿:“你说贺锦书?他一年前失足掉下护城河里,死了。”
失足?好啊,好啊。他那好面子的好父亲啊,好一个落水而亡。
光绪三十一年,贺锦书时年九岁,贺家派人来到郴州,递了一封贺家大少爷贺志生的信。信上说,贺家老爷子病危,盼多年未谋面的孙子回贺家认祖归宗。
母亲捏着那纸轻薄地书信,喜极而涕。她嘱咐儿子,一定要把箱子里的东西,亲手交到父亲贺志生手里。
就这样,贺锦书提着一只装着母亲戏服的皮箱,跟着贺家的人踏上了去苏州的船只。
贺家在苏州是颇有名望的苏绣世家,皇宫中所用的苏绣用品居多出自苏家所领的绣娘之手。十年前,贺老爷子让长子贺志生去湖南郴州赴王家儿子的婚宴。
宴席上,王家请了当地的湘昆班子来唱戏。当天唱了一曲《风筝误》,贺志生向来喜昆曲,望着台上扮演詹淑娟的闺门旦含蓄蕴藉,眉眼动人,一时留心。
那花旦便是贺锦云的母亲,名唤婉娘。郴州地方小,少有风度不凡之人。贺志生出自大家,一身锦衣,举手投足间气宇轩昂,在人群中的确扎眼。新郎是位眼尖的聪明人,见台下翩翩公子有心,台上二八娇娥有意,从中搭桥牵线,二人时常在王家厢房相会。贺志生教婉娘认字读书,婉娘回以千娇柔媚的曲声,郎情妾意,白云仙乡。
家中写信来,催着贺志生回苏州,贺志生一再推脱,妻子姚氏察觉不妥,更是催促地紧了。贺志生无奈,只好启程。走之前,婉娘已有身孕。他托王家少爷帮婉娘安排好府舍,承诺回苏州后立马告知父亲,接婉娘回去。
婉娘苦苦地等着,却只有钱票寄来。初始还有贺志生长长的书信,写他的诸多无奈和思念无边。婉娘也信,带着儿子等着。这一等,就是十年。
贺锦书从记事起,便见母亲夜夜垂泪,他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始终不提不问。他也不恨父亲背信弃义,母亲都不恨他,自己恨了又有何用呢?
贺府管家到渡口接他,开口就喊他少爷。他有些怯,轻声应了应。
到了贺府,那位从未谋面的父亲在厅前等他,身旁站着贺夫人和贺家的四位少爷小姐。
贺志生见到儿子已经长成了仪表不凡的模样,难免喜从中来。他上前握了握贺锦书的手,给他介绍贺夫人和他的孩子。
贺夫人倒没给他脸色看,让两个女儿喊他三哥。贺锦书艰涩地应下来,心中只挂念着母亲的话。
他抬起箱子,说道:“我娘说,要我把这个亲手交给你。”
贺志生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提起他母亲,面露为难。他接过箱子,潦草地带过话端,只让贺锦书快去见见爷爷。
对贺锦书来说,他迢迢千里来到苏州,只是为了替母亲送一样东西。他还是要回去的,母亲还在郴州。
可母亲没能等到他,贺老爷子半月后西逝,葬礼刚完,府中就来了郴州的信,告知贺锦书母亲落水的死讯。贺家管家带他回家奔丧,母亲的遗物里有张泛黄地宣纸,上面临摹了一首易安居士的词,贺锦书读了后,郑重收好。
一月后,贺锦书回到苏州,入了贺家祠堂,成了贺家三少爷。
转眼就是七年后,清朝覆灭,改天换地。社会动荡间,苏绣产业一度低迷,多家绣坊接连关闭。贺志生作为长子接过了家中家业,不甘落后,潜心研究苏绣技艺,贺家以此为契机,更是成了苏绣家族的佼佼者。
贺家人丁兴旺,奈何头上两个嫡出哥哥都不成器,倒是贺锦书,做事端正沉稳,得父亲器重。
夜里,他出了书房,踱步到院内,一个瘦小地黑影闪身进来,刚想问是谁,就见一张稚嫩俏丽地脸庞,接着家丁和丫鬟便追了进来。
“你们找什么呢?”
“回三少爷,厨房里进了小贼,我们正逮贼呢。”
假山后地的小孩子拉拉他的衣角,一脸恳求的模样。
贺锦书问道:“府中可丢了什么东西?”
“并无,就是少了些吃的……”
他摆摆手:“既然没少东西,让人仔细巡视下就好,这样四处逮人,像什么样子?”
打发走下人,他低头望望暗中的女孩,问:“你是何人?”
女孩一身破破烂烂地,捏着糕点不敢望他。
贺锦书吓唬她道:“你不说我可就把他们喊回来了?”
“我只是太饿了……”
女孩把怀中的点心和鸡腿摊了出来,她望望手中咬了一口的糕点,怯生生地说道:“这个我吃过了……”
贺锦书愣了愣,一时心软。
“吃完就往后门离开吧。”他想着,又多说了句:“世道艰难,别人的施舍只能解一时之困,你若不想再饿肚子,那就得学一手本事。”
话毕,他回了屋子,只留下一地的月光。
贺夫人前几年重病过世,贺老爷陆陆续续的纳了新的姨太太,民国四年,贺家四姨太为他生了个儿子,府中摆满月酒,请了梁家班来唱戏。
四姨太瞥了瞥一旁的贺锦书,刻意取笑,说道:“听说三少爷的娘也是个昆曲名角儿呢……”
贺锦书垂下眸子,不急不恼地回道:“我娘亲会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不像四姨太,端茶送水,擦地洗脚,样样都是实事。”
四姨太听了,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她原本是伺候贺夫人的丫鬟,可心思不纯,找准机会翻身成了四姨太。
“好了,听曲就听曲,叽叽喳喳地像什么样子。”贺老爷发声止住了想要回嘴的四姨太。
四姨太受了气,认准了要还回来。再点曲的时候,她指定要听《风筝误》。
贺老爷望了儿子一眼,见他脸色虽变了变,但也没说什么,于是应了下来。
贺锦书一开始还端坐着,扮演詹淑娟的五旦一出场,他望着那身熟悉的戏服,再也坐不住了。借口身体不适,离开了戏台子。
他进了院子,中秋快到了,夜里的月亮又圆又亮,他一时发觉,这二十一年的人生,从未团圆过。小时候陪着母亲等父亲,后来母亲走了,更无团圆可想了。
穿着戏服的小姑娘就在这时靠了过来,他回过头,认出是刚刚台上的五旦。
他语气难免不善了几分:“谁准你进来这里的?”
小姑娘一脸浓妆,伸手想抹掉,却又想到后面还要上台,只能焦急地道:“是我呀……大哥哥…唉……”见面前的人仍紧锁着眉头,她觉得自己说不清了,唉声叹气的。
望见假山,她眼睛又亮了起来,立马指着说:“五年前,石头后面,点心、鸡腿……你和我说要想不饿肚子,就要学一手本事……”
贺锦书眉头舒展开来,似乎的确有那么回事儿。
“你是那个小贼?”
小姑娘高兴的点了点头:“我听大哥哥的话,进了戏班子学唱戏,现在不会饿肚子了!”
贺锦书倒没想到,自己当初随口一句话,让一个小孩记了这么久。
她又问道:“大哥哥是不喜欢我唱的曲儿吗?为何我刚开口,你就走了?”
这时戏曲声又停了,她忙着要赶回去,走之前不忘说道:“我现在有名字了,我叫梁浅,深浅的浅。”
梁浅瘦弱的身子拖着长长地戏服,影子映到了廊上,贺锦书望着,不由地念道:“梁浅……”
再见到梁浅,是在苏州梨园里,她卸了戏装,圆圆地脸庞,一双杏眸仿佛会说话般地。身着水蓝色地布衣,一股乌黑地麻花辫垂在脑后。贺锦书仍没认出她来,只听后面有人脆生生的喊道:“大哥哥!”
他觉得声音耳熟,回头才想到,好像是有那么个叫姑娘,叫梁浅。
刚刚和一位老板谈完订单,贺锦书打算要走的,硬是被梁浅留了下来。
“师傅说我唱地可好了,大哥哥你听了就知道了!”她说着便跑上台,作势唱起来。
贺锦书望着那双水汪汪地眼眸入了神,他摇摇头,脸突然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