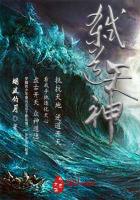不同于往日的肃清,此时的议政殿内针锋相对,气氛紧张,本该立于两旁的众仙官各执其说,商议着一件大事。
如何处置夜羽。
话说收复魔族已有一段时日,众仙怎么如今才突然想起还剩个夜羽?全是这么回事。
在魔族灭族之后,游散于外的魔族余孽贼心不死,妄想东山再起,便联合了飞云殿内的一众美男,要拥护夜羽为王,重建魔族。
此事败露,凌决当即下令,被捕的一众美男就地处决,而未参与此事,却深陷其中的夜羽,就成了众矢之的。
觉得应该放过夜羽的一派认为,他两次谋反都未参与,可见其心性清明,并非大恶之人,且夜羽此翻确实是被牵连,看在相君的份上,便饶他一命罢。而另一派却认为,夜羽虽未有谋反之心,却不可避免地处于漩涡中心,他身份特殊,只要活着一日,魔族余孽就会心存幻想,且他现下没有此心,谁能保证他一直没有,万一他只是善于隐藏,等待时机呢?总之夜羽长住飞云殿,与相君安全甚是不妥,留着总是个祸患。
一时间,殿上七嘴八舌,争执不下,吵地热火朝天。主张处置夜羽的一党略占上风,他身份摆在那里,身为魔族王子,确实难辞其咎。一众仙家字字玑珠,将魔族百条罪名一一陈列,要将夜羽处以天界最高极刑。凌决撑着下颚不语。
突然殿中一声清冷地声音响起,压平了纷扰。
“夜羽是我飞云殿的人,要如何处置,也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
只见凌霄霸气地走进来,气场全开,她凛冽地扫了一圈,在场的各路神仙全部噤声,低着头退到两侧,夜羽跪在殿中,面色凄凄,反手被铐,不由自主地看着凌霄,神色复杂,一双动人的桃花眼低掩住心中的情绪,又别过头不去看她。
众仙面面相觑,其中一位胆子大的迟疑了一下,出列道:“小仙并非有意冒犯相君,只是夜羽身份特殊,为永绝后患,还是…还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好。此次他不反,怎知以后如何?这谁人做保?”
“本君保他,谁有异意!”
凌霄气息冷冷,立在殿中,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她看了看众仙,悠悠开口,“既然众位仙家都没有异意,那本君便在此谢过。”
她朝凌决一拜,领着夜羽离开。
白芷王城外,浅色的小花成片摇曳,像风中舞动的精灵,收集着世间的喜怒哀乐,化为一朵洁白无瑕,照入人心。
她说,他可以选择留在飞云殿,或者离开,夜羽选择了离开。
“为什么救我?”他无法下手杀自己,却很希望别人能给他一个了断,可救他的人是凌霄,他又觉得自己该要珍惜的,毕竟是她救来的命。
“我确实曾想过要杀你,甚至想过与你同归于尽。”他父王作恶多端,魔族俱毁,他早想到会有这一日,可实现这一切的偏偏是她。他不是没有想过,与她一同下地狱,可他终究做不到,即使自己再痛,也没有想过要拉她一起。“我不过兵败之人,阖族灭亡,我本就苟活,多我一个也不多,你如此,让我…”他有些艰难地说完。
“我并非中意于你,你我虽算不得朋友,毕竟相识一场,你离开吧。”夜羽的心思,她还是从钟离元玉那儿听来,他“无意”说到魔族,又“无意”提到夜羽,然后酸溜溜地说夜羽也许是对她有意思的,虽然不知道他是从何时开始,但自己注定与他没有交集,她做事向来干净利索,直截了当最好不过。
“我自然是明白你不会倾心于我,想来你喜欢之人,也必定是如东华的储君那般,但你有你的心思,我亦有我的心志,我只是不明白,当初为何愿意留我在飞云殿。”
曦和与魔族大战在即,凌霄不将他扣押做为人质或者遣送回魔族,反而将他留下来,现在又允许他离开。夜羽是很清楚的,两族一旦开战,魔族必亡,他以那样的名义留在飞云殿,看似作为人质,但实际她从未为难过他。若他回了魔宫,在这一战中便免不了一死。可她是出于什么原因救他一命呢?可怜?还是一时兴起?
“九万年前,西州白云山。”凌霄道,
他的眉眼,是极致的美,透露出淡淡忧愁的阴柔婉约,大概比这世间所有女子都让人怜惜。
夜羽看着她,模糊忆起来。
九万年前,父王在白云山捕捉一只巨兽,带了年少的他左右随行,他在白云山下曾发现一位身负重伤的少女,因担心父王发现她是神族而痛下杀手,于是将她藏进深草堆处,给了她一颗护心丸便匆匆离去。
夜羽生平救过许多性命,总是默默为父王积善,他努力回想,却始终记不得那时她的模样,只记得那躺在荒野中身受重伤的少女,即使浑身是血,身上布满了刀口,却有着不同于她这个年纪的沉着冷静,一声不吭,紧咬着牙,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他无奈地笑笑,也许这就是缘分,他有幸遇到,可还是错过。
“你不必感谢我,我不过做了个顺水人情,若你不来王城,沙场相见,我也必定不会手下留情。”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三危山的时候,她受了重伤,奄奄一息时,有一头灵鹿为她舔伤口,那鹿的眼睛灵动清澈,干净洁白,周身的灵气让她的伤口得到进化,她杀了那头鹿,饮了他的血,才有力气撑到白芷城。
她不在乎生死荣败,无畏世人对她的褒贬指责,但她若死了,无数的希望就会破灭。三危山一战后,她名动四方,她活下来,就能让很多人拥有希望,可即使这样,她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代表正义的,那些叛军也并不一定就是邪恶,相反,他们中很多人,毕生都没有杀过一个人。
在这个蛮荒的年代,善恶便是输赢,或者说,输赢便是善恶。
“如果当时没有我,你会死吗?”他轻轻地问,
凌霄只是看了他一眼,又转过去看远处茂盛的白芷花海,答了一声,不知道。
“谢谢。”他顿了顿,“我方才在想,自己是希望你说会,还是不会。”他望了一眼凌霄,包含太多深意,“我很希望你说会,这样我会很开心,在你的一生中能够真正影响你一次,可我又希望你说不会,让我更加看得清楚,于你,我始终都是可有可无的。也许这个答案更好,缘分本就是说不清道不明,你我这一遭,没有绝对的毫无瓜葛,也没有纠缠不清,这样很好。”他顿了顿,抬头望望天,眨了眨干涩的眼,又低下头来继续道,“君上…我,能唤你的名字吗?”还未等凌霄开口,他又否道,“罢了罢了,都要离开了,唤什么都一样。”
凌霄看了他许久,未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他笑了,如三千桃花争相夺艳,突然释然了很多。
他们缘长,所以兜兜转转了一圈还是能遇上,可他们又缘浅,只能那样的开始,又这样的结束。
夜羽走了,他至始至终都没有叫出那个名字,他们之间太多太多的纠葛,让他连她的名都叫不出口,他不知道自己该带有什么样的感情,是愤恨地,还是爱惜地。他在想,她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有些怅意,还是轻松了些?又或者,她心无波动,就如同救了个不相干的人,还了个不相干的情。那个名字,也许他以后只能在心里默念,只能唤给自己听,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忘记,或者慢慢痊愈,他会去西天,找到他的心该放的位置。找到他能解决这些痛苦的办法。等到有一日他能逃出心魔,便是此生最大的希望。
殷珂曾问过他,他是否恨凌霄?
他说,他不恨她,他恨自己。
而如今,他也试着开始原谅自己。
凌霄送完夜羽,回城的时候发现了被凑地伤痕累累的有奇一族的王子。这个王子叫什么她都不记得了,当时他正被几个鲛坚族人殴打,凌霄向来是不会放过任何敢在白芷王城附近闹事的人,她三两下解决了那些鲛坚族小兵,一群小兵被打散,露出中间围着的鼻青脸肿地有奇族王子,她看了他一会,王子也正好看过来,一双闪烁着泪光的小眼睛惹人怜爱,凌霄将他拎回了白芷王城,从头到尾,站在不远处的虬海一言不发,凌霄也只是撇了他一眼,自顾自地离开。身后的男子突然露出诡异一笑。
自从昨日在王城外见了虬海,他在凌霄脑海中便挥之不去。
沉族一族虽为四大神族,却位于深海,控制着除了四海之外的所有深海水域。数万年前,沉族老王君蓄意开荒阔土,领十万沉兵与相临的曦和一战,将曦和族大军逼退至白芷王城。此战持续了数千年,所涉之地生灵涂炭,曦和万里山川饱受战火煎熬,沉族深海的鲛毒腐蚀土地气云,使这片土地上连续数千年未能有一个仙胎顺利降生。
沉族战败后,退守深海,数万年不在有动静,却从未放弃过他的野心。近些年,女君即位,沉族的野心愈发明显,在西海上的那个幽州岛,表面上似一处族外行宫,实际上却暗藏不为人知的秘密。钟离元玉毁了幽州岛后,曾派人前去调查,他告诉凌霄,幽州岛上的沉族修的皆为阴险逆天的禁术,除了嗜血阵,还有一些险恶阴毒的邪法。
那日虬海身着沉族崇尚的一身黑色,领口印有金粉花纹,是沉族的图腾,他是女君的异兄,母亲是深海蛟龙族的女子,年轻时不知犯了何错被逐出蛟龙族,到沉族王宫中做了个侍女,后来被老王君看中,生下了虬海,他母亲地位低下,即便是沉族老王君唯一的儿子,也无法继承大业。
这是她第二次见到虬海,除了第一眼觉得他有些面熟,此次却有说不上的情绪,那个男子阴险的笑在凌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心情莫名沉重,好几次在梦中惊醒,浑身大汗,却始终不记得自己梦到了什么。
她知道,是那日落在梦界中的一缕发丝的缘故。
那日她的发丝被钟离元玉的箭削落,被留在了梦界,当时钟离元玉就深感不妙,并试图找回,但始终没有办法。那个神庙,就是梦魔天姬编制的梦界中破解之处。
不论法力高低,只要步入神庙,就如同一个凡人,暴露出他的破绽,梦界会根据这个人心中的破绽而幻化出相应的场景,若是能走出自己的心魔,便可再也不用受心魔控制,恢复法力离开梦界,若是无法破解,便只能永远留在这梦界中。
当初的凌霄心中未能有何破绽,梦界也没有办法幻化出相应之景,才让她阴差阳错帮钟离元玉破了心魔,可她一缕发丝留在了梦界,只要她心生破绽,梦魔天姬便可察觉,即使无法再次轻易将凌霄放入梦界,也能通过她的梦境去影响她。
陌吟近日心情不怎么好,他觉得自己情路坎坷,蟠桃会之后,他先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女子,东华的大殿下,和住在荆海的海神。他郁郁寡欢,找到云中君喝酒,云中君对他不分男女的事情很是汗颜,不过出于好心,还是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云中君道,荆海的女神可能同他比较般配…
于是陌吟上了一趟天宫,又下了一趟荆海,回来与云中君道,荆海的女神确实比较般配于他,因他去天宫见了钟离慕白,没想到他有磨境之好,竟然喜欢女子!陌吟感叹自己与他无缘,又去了荆海,不料荆海的女神同样思慕于他,还表示能接受他有儿子这个事实,于是陌吟喜滋滋地跑回来准备了一石白果充做礼数,连夜背去了荆海,可第二日,他又垂头丧气跑了回来,满脸的胡渣,红着眼说自己只有千弛,这辈子要与千弛相依为命。
不论云中君如何劝解,他也不说究竟出了何事,直到一次喝多了酒,在飞云殿中走丢了,千弛去寻他时,他抱着千弛瘦小的身板痛哭流涕,不停地问他知不知道扶桑若木的故事。
千弛是不知道的,可云中君知道,那是个悲伤的故事。
传说,盘古大神开天后,左右手的食指皆变成了一颗银杏树,生长于东西两极,东为扶桑,西为若木。若干年后,这两颗树化为仙身,结成夫妻。上古大炎时期,六界多为混沌之处,战乱不止,若木在一次战乱中死去,扶桑为了救她,与她的原体元神融为一体。
他原本以为年代久远,这些都是以讹传讹,不想…
这就是陌吟为何总是浑浑噩噩,且分不出男女的原因。他就是扶桑,与若木合为一体后,他元神混乱,虽然表面上看不太出,但大多数时候,他是神情不清的,记忆也丢了很多。
那日他搬着白果到荆海女神住处,见她的水晶宫中有一面大镜子,那镜子能照出元神本尊,三魂六魄,他在镜子中看到了若木,才顿时清明起来。
原来他叫扶桑,不叫陌吟,是那时才改了名。
陌吟,
陌上人不现,
吟是不相缘。
陌吟到飞云殿看望千弛时遇见凌霄受梦魇所惑,他沉默了许久,说凌决可能知道。
她去了明华殿,凌决在吩咐司礼处理曦和北边一个部族的事,司礼恭敬地告了退,转身将门关上。
凌决对于她遇见虬海的反应没多惊讶,只是点点头,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凌决拿起手中的笔,又将笔放下,“有些事,你也应该知道”,随后便带她去了白芷王城一隅的月庭。
她来长平殿的时候,钟离元玉在刻木。他为凌霄做了一床软榻,放在书房,这块上等的沉香木,质感极佳,木质上等,是做榻的好料子,背榻上的图案已经差不多做成,是并蒂莲花印双鱼戏水。
这是个细致活,他拿着挫刀细细端量了一会,缓缓削去薄薄一层,将那莲花的姿态矫地抚风摇曳。
“你边上坐会儿,我这个马上成了。”
没听到她的回答,钟离元玉直起身子看她一眼,“怎么了?嗯?”
她面色无异,只是坐在那安安静静地说了句没什么,
过了一会,她又说道,“这榻别做了,我不能拿天氏壁来镶在上头了。”
钟离元玉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又转过身去修那只鱼眼。
莲叶青青,双鱼戏水
“无碍,回头去山水洞,那儿也有极佳的。”
“夜羽走了,我把天氏壁给了他。”
挫刀脱力一偏,血滴滴答答流下来,他望着地上血迹,发了一会愣,转过身去把手伸到她面前,委屈道,“霄霄,我受伤了。”
这伤口略深,凌霄拿了绷带和药给他弄上,边埋怨他如此不当心。
他把手指伸到她面前,“吹吹,很疼的,十指连心。”
凌霄将他手丢开,道了句活该,转过身不去看他。
天氏壁是凌霄的一块贴身佩件,虽无什么用处,但跟了她多年,沾满了她的气息。
她不是那种会因为感情上给不了别人回应就感到愧疚而去补偿的人,有奇族王子和北海寂并就是例子,且她先前说过要将那玉嵌在软榻上,以她的性子,说过的话,即便是夜羽主动提出要,她也会直接拒绝。但她现在,却把玉给了他,把带着自己气息的玉,主动给了他。
“霄霄,对我,你是有什么不确定的吗?”
“我能感觉的到,你是有所保留的,告诉我,为什么?”
他将她转过身来,“霄霄,与你在一起,我等了很多年,我不会因为别人如何评价你而动摇,也不会因为你做的这些事情而不相信你,或者我现在做的还不够,但我在尽力学着如何对你好,我从来不掩饰自己有多爱你,你也不准掩饰。”
“我不想逼你,所以一直没有再提,凌霄,我想知道,你愿意嫁与我吗?”
久久的沉默,静止的空气像一把利剑,不知伤了谁。
“我没想过要与你成婚。”
钟离元玉缓缓吸气,觉得心口有些闷痛,他将刀口撰在手里,手上的血滴滴答答落了满地,无知无觉。
“就这样不好吗?”
“就这样?”他一把扣住凌霄的双手,将她按在床上,突然有些生气,“你说,我们这样是哪样?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我是你千万玩乐对象中的一个吗?还是,这一切全是假象,你在玩弄我?你是在报复我吗?”他说到最后,自己都笑了起来,却满是苦涩的味道,凌霄动了动手,却发现无法挣脱。他紧紧地扣着她,逼她对视,
“我不傻,我知道你也爱我,告诉我,为什么?”
他手上的力气加大,死死地盯着她要回答。
凌霄冷冷开口,“放开!”
“回答我!你知道的,我比你更执着。”
凌霄直视他,“好,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钟离元玉凉凉看了她一眼,松开她的双手,她一挥袖,身边的景色骤然变化,高低不平的墓碑浮现在眼前,漫山遍野,辽无边际,伴随着坟边的青青飘草,几只鸿雁天边南飞,血红血红的杜鹃将云霞染红,夕阳下更是一番凄美壮阔。
钟离元玉凝视着这一切,站在一旁未动,凌霄只顾往前走,指尖抚过一座座碑头,“这片是在鹤水江中战死的曦和将士。这片,是5万多年前的空栈之战牺牲的几千将士,这片,是收复魔界之战…”
这是她一个人的秘密,连云中君都不晓得,在凌霄帮那些人轮回后,还为他们立了碑。这些都是她亲手所埋。
神仙没有轮回,死了,便是死了,元神融入山川河海,永远消散。即便云中君取了这些人的一魄送去轮回,但终究是死魂,就如顾尽帆那般,仅一世便会消亡。
“你说过,这些事,不该是我来,我告诉你,这些事,只能是我来。钟离元玉,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王兄此生,无法走出白芷王城。”
凌决在数万年前与沉族那一战中,身负重伤,双腿残废,伤及根本,只能终日呆在白芷王城,靠这一方仙泽维护。这就是她为何小小年纪,就开始独自一人,东征西战,安布四方。除了她,没人能守护曦和,一将终成万骨枯,她这举世威名与曦和的万世太平,正是用这些千万将士和她这一身伤换来的。但她不后悔,比起她,王兄只有那冰冷的王座,连亲自去寻找自己的心上人都做不到,她又有什么理由,抛下他。曦和为了今日的太平牺牲了太多人,如今的沉族蠢蠢欲动,曦和上古战将皆在那场战争中命尽归天,王兄无法出战,曦和无用兵之将,她放不下曦和,她不会离开…届时与沉族一战,她必定亲自挂帅领兵,将前世之债一并算清!
“钟离元玉,这就是我的牵挂,而你,”她上前猛地撕开他的前襟,露出一块青黑色的印记,古老盘复的图腾印刻在他的左肩,“这就是你的牵挂。”
钟离元玉自从到了沽山,就没出过声,这是他没见过的凌霄,她难掩的哀伤深深刺痛了他,
他走了,留下她一人跌坐在千万英雄冢中伥然失神。
是夜,凌霄派人送来一张信筏,上面寥寥几句,说的很清楚。
他们各自担着责任,注定不会在一起,她已让云中君重新拟好了命薄,在凡界了了这段缘,从此不再有瓜葛。
钟离慕白端着一盅羹汤坐到他旁边。别看他这个二弟平日笑起来温柔而雅,其实心眼多着呢,发起威来毫无征兆,他有一百种办法将你收拾地服服帖帖,还要对他感恩戴德。钟离慕白很失落,他无所不能的二弟,怎么变成这幅模样,道法中所说的果真精妙绝伦,“世间万物生生相克”,诚不欺他。“喝吧我的储君大人,都一天了,失恋了?又让你的相好气着了?”
钟离元玉接过碗,放在桌上。
“这位相君还真是神通广大,怎地把你弄得成日魂不守舍。”
“于她,我确实一败涂地。”他苦笑,钟离慕白不高兴了,怎么说小二也是我大东华的储君,怎么能为一个女子如此,说出去东华颜面何在?钟离一族颜面何在呀?
他拍拍钟离元玉的肩膀以示鼓励,“小二,你是未来的王君,要以大局为重。”,钟离元玉低眼道,“东华历届储君并未皆有帝王印,若王君所生的孩子中并未有此印,即为贤能者即位,我心中有所求,不是一位好王君。”,钟离慕白宽慰他,他代政以来的表现六界皆有见晓,他家小二是当之无愧的帝王之才,所说美中不足即是那位曦和的相君,但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既然是道关卡,那解决了它就是,“不过…小二,你那位美人有些难解决。”
他看钟离元玉还是有些低落,便神色严肃了些,“小二,你身上有着东华的帝王之印,有些责任也是难以推脱的。”,他叹了口气“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第二日,钟离慕白还未上朝,朝晖宫里的小仙娥便匆匆赶来,掌事的仙娥蓝心听了消息,立马泪眼汪汪赶去禀告钟离慕白。
储君剜下了帝王之印。
钟离慕白大惊,忙穿了衣服赶去钟离元玉宫里,又折回来吩咐蓝心不要将此事泄漏出去,特别是别传到父君那头。蓝若边掉眼泪边点着头。
朝晖宫内外与平日并无两样,长平殿里钟离慕白却踱步难停。
钟离元玉转醒,面色有些苍白,左肩上阵阵作痛,体内气息大乱。
钟离慕白赶紧按住他,剜了帝王印,难免遭到反噬,此事他气息不稳切不可乱动。
“王兄…”
“你怎可如此糊涂!”钟离慕白气急败坏地打断他,“帝王印乃命定,怎么可能任意串改,小二,你这般…你这般成何体统?”
钟离元玉不在意,“现如今我没有了帝王印,这东华的王君,也可以是你。”
钟离慕白颓败地坐在他床榻边,“小二,我从未想过要当王君,东华的王君只能是你。”,钟离慕白看他执迷不悟,一甩袖子,“这印不在了疤还在,你别以为剜了它就能赖掉。哎,小二你要去哪?”
钟离元玉不顾他的反对起身,穿了衣服匆匆离去。
钟离慕白拦不住他,气的又甩袖子大骂成何体统。
黑暗,一望无际的黑暗,周身的空气温度渐渐下降,渗入骨髓的冷气将凌霄呡了呡冻地发白的嘴唇,一路摸黑走,耳边隐隐约约有无数声呼救,伴随着刀剑相撞的声音。忽然,有什么热热的东西滴到她脸上,又马上变得冰凉,她伸出五指一片黑暗,看不清那是什么,滴滴答答,越来越多的液体砸在她身上,如同下雨一般,地上积累的液体蔓延过她的脚踝,她嗅到了血腥的味道。
对,是血,是她最熟悉的气味,这里满天下着血雨。
脚下被什么东西拌到,她摔倒在血水中,摸到一具冷冰的尸体,旁边的刀剑划伤了她的手。
这是梦,也是她的心魔,这就是她一直以来做的那个梦,现在,她在自己的梦中,她在这里游荡寻找,不知何时是尽头,她记起来,自己到了极乐天,有些心魔她必须要面对,所以她找到了梦魔天姬,入了梦界,若是找不到出口,便只能困死在这。
她终于知道,自己一直以来梦到的都是什么,是战争。在战场上,她杀伐果断,但内心深处,凌霄对死亡并不是毫无感觉的,神仙不似凡人,虽能长生不老,一但死了,便真是死了,骨血消失,元神化入山川江河,不复存在。世人只道相君骁勇好战,却不未有人想过,她也会害怕战争。
可有些时候,只有战争,才能避免战争。
她该如何突破这心中之魔?
血水已经蔓过她的腰身,向头顶蔓延,突然,前方轰隆巨响,缓缓升起一座巨大的铜台,铜台上一个巨大的雕塑,轮廓像是一名高大伟岸的男子,手持巨剑指天,脚踏巨莽,似乎在砍杀世间所有的邪恶,但周围太过黑暗,她看不清雕塑的脸。她双手紧握,拼命想往铜台去,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
突然一道白光迷了她的眼,积蓄已久的血水像洪涛搬涌出那个洞口,远处传来石头破裂的声音,铜台上的雕像开始土崩瓦解,裂成大块大块的巨石掉入血水中被冲出去,一只大手揽过她的腰身,带她一跃,站上了铜台。
铜台下泛滥的血水呼啸而过,耳边风声不绝,白衣暗银纹的男子松开抱着她的手,屈膝微微倾身,牵起她一片衣角吻上,和润平稳的嗓音虽不大,却好似压过洪涛泛滥之声,让她莫名地安心,“瑾以吾生,护你周全。”
倾刻间,四周皆穿来破裂声,他们所处在的梦境似乎像一个正在破裂的壳子,开始有了裂痕,透入道道白光,最后四分五裂。
落地后,她顾不得自己身处冰火两重天之地,猛地抓住钟离元玉的手,他也紧紧地抓住她,将凌霄抱在怀里,久久不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