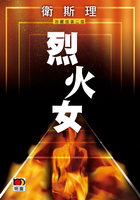易、潇二人入得关来。一路风餐露宿,饱尝辛苦,所幸二人相伴,不感烦闷,行了月余,这一日方至建康。二人这一路之上甚是平静不曾遇半人截拦,显然二人复出之事尚未传开,但易水寒已觉奇怪,街面之上江湖样人日多,且偶有交手摩擦,气氛略显不同。
“易大哥,太师父的望云轩所设分号当是不少,为何我们独到建康来?”潇潇边观街景边道。
“师父曾道,这望云轩向来认箫不认人,凭我是易水寒,无箫也是枉然。建康这家是总号,师父无事便在此执掌,我的寒箫、虺剑都在师父手里,不到此来,还有何办法?”
这般说着,易水寒点指前方,潇潇踮脚观望,只见一店座于街心,上悬大匾书:“望云轩”三字。雕梁画栋,极显富贵之气,令人只敢远观,难近其身,非官宦而不敢登门。易水寒也不管,拴了马便拉着潇潇大步走人,亦不论身上布衣寒酸,头上帽破,如出入自家门庭,进门便坐。吓得门处侍童一跳。
侍童定睛看了易水寒,便冷了脸,走过来,喝道:“喂,这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可不是脚夫歇脚的地方!您看,对面有茶摊,走吧,我们这还有贵客,别有碍观瞻,影响我们生意,走走走!”说罢,便欲往外赶二人。
易水寒理也不理,将帽一掀,放于桌上,潇潇只觉好笑,也未动分毫。
那侍童见二人不理,反而火冒三丈,上前抓住易水寒手腕,生往外拉,口中道:“还不走……”
易水寒岂容他这般放肆,翻手扣住其腕处脉门发力,那人半段胳膊立时软了,气也弱了,疼得只有嘘嘘人气,再不能出一言。
“易大哥……”
“若不是看你是望云轩的人,阎罗殿你是去定了。”易水寒松手,对潇潇道:“我们进去看看什么贵客。”说罢二人便入里间,那侍童张了半日口,却未敢喊出。
见屋正中两椅一桌,桌上一盏茶,左手边坐一花甲老人,红面短须,衣着不俗,手中举一对玉镯,仔细观看。右手边坐一贵妇,珠翠满头,身着百鸟朝凤团花锦裙,眼望老者。身旁有丫环轻摇羽扇,四名壮汉列于一旁,显是家丁。
易水寒见那玉镯,忽而来了兴致。上前两步道:“老先生,可否借在下玉镯一观。”
老者先前只顾端详玉镯,并未留意易水寒,听其之言,顿觉唐突,皱眉抬眼见易水寒之容,眉间略展道:“公子说什么?”
“玉镯借在下一看。”
“怎么,公子也懂这鉴赏之道?’’
“略知一二。,,
老者初见易水寒临风玉树之貌,虽不知他是谁,心中已有几分喜欢,便问那贵妇是否应允,那贵妇点头,老者便将镯递于易水寒。
易水寒观镯,见其色浓绿,手触极润,便知一二。对光而看,晶莹透彻,便道:“果是好翠。”举镯轻碰,清越之声。又道:“依在下所见,这对镯乃是采取山底深处或溪涧边之玉所制。此等玉石色浓而艳,透而纯,且硬于平常之类,这玉镯可称得上价值连城了。”说罢便将其递回。
老者捋须笑道:“不假,不假。”
贵妇命人收回玉镯,又道:“可不知如何分清这翠之高下,还请公子明示。”
易水寒道:“翠之颜色颇多,有红、绿、紫、青、蓝、灰、黄、褐、白、黑十色。中以绿为最上,紫色次之。绿之色又分数种,有冰透,白、泥皮、金丝,墨夹绿等种。上上之翠色可以五字来括,为浓、阳、俏、正、和。浓为色厚,阳为色亮,俏为色艳,正为色纯,和为色匀,此五条皆全之石已臻极品,但还须其雕工精湛方才完美。”
老者大叹,贵妇盈盈点头。
老者仿佛颇是惊异,道:“‘六瑞’为何?”
“玉雕圭、璧。圭分‘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璧分‘谷璧’‘浦璧’。”
“何为‘六器’?”
“苍、黄、青、赤、白、玄六色玉所雕成之礼器。”
老者连连称赞,又道:“何为玉环,玉璧,玉瑷?”
“中孔小者为璧,较大为环,再大为瑷。”
“‘顿牟掇芥’何为顿牟?’’
“这……莫非,莫非是琥珀。”
老者立时起身,拱手道:“今日老夫可是开了眼了,公子如此年轻居然有这等见识真是了得!公子,坐,碧玺,上好茶。”门外有人应了一声,奉茶而人。易水寒携潇潇坐于一旁。
待那贵妇走后,老者方才落座,对易水寒道:“老夫乃是本店店主,姓石名独山,不知公子大名,仙乡何处?”
“在下……石掌柜,非是晚辈不愿相告,怕是告诉您,您也不会相信。晚辈来此是有一事相求,不知你家大掌柜在否,晚辈请见。”
“这……”石独山皱眉道:“公子似与望云轩颇有渊源,你怎知我家先生。不过……”
“怎么,贵店接笔重要生意,先生他闭关亲制?”
“公子到底是谁?”
“大掌柜几日出关?”
石独山低眉一算,道:“巧了,似在今日。”
太好了,石前辈,烦您引路后园琢玉室,我二人可等候。”石独山更为惊讶,这琢玉室非近人不知,而此人却知晓,看来是自家人,便道一声“请”。引二人穿曲廊,过林径,至琢玉室外五十步之地。易水寒停住,道:“此处便可以了,怕我二人碍了先生之事。”石独山相陪,三人一候便至掌灯。
易水寒与潇潇低语:“师父常道,这琢玉与练功极类,琢玉时需心无杂念,若止水一般,这玉石贯以心力方才会有灵性。而师父之法更与旁人不同,师父以内力断玉,玉自然较硬圆润,所以师父一般不亲自动手,因为完成一件玉器耗内力太大,凡亲制不是贡品,便是朝中三公所求。”
潇潇点头。
石独山忽道:“门开了,先生出来了。”便迎将过去。易水寒顿时激动亦大步上前。
“累煞老夫了!如今年岁大了,这便是老夫封刀之作。石头啊,这几日辛苦你了,家里可好?”
“好,好,老爷,只是今日来了位贵客,已在门外候了一日了。”
不消石独山说完,易水寒已至银子近前,双膝跪倒。
银子不看则可,一见愣了半日,方道:“我这是眼花了吗?还是做梦呢?儿子?”
“师父,让您替弟子担心了。”易水寒强忍泪水道。
银子已然老泪纵横,走上前去,拉起易水寒,泣道:“真是儿子,儿子你的记忆恢复了,儿子……”便抱住易水寒,似孩子般呜呜而哭。
此时石独山方才明白,对潇潇道:“原来这是少爷,难怪如此了得。因为少爷得病之事,老爷好歹病了一场,整日闷在屋中,这下好了!”
潇潇感动得不能出一言。
当晚银子在花园大排宴席与潇潇、易水寒接风洗尘,银子只乐得皱纹堆砌成花,与易水寒畅饮。二人向银子述了前些日之事,银子对鹿死我手之事颇为好奇,对易水寒道:“儿子,老天真是疼你,连遭难时都有高人助你,好啊,把跟那鹿死我手学得招式打给爹看看。”
易水寒见师父高兴,借酒兴起身,躬身道:“是。”便走出几步,抬掌之时便觉前后百步煞气,看其双臂齐动,时快似闪电,时缓如太极,风随掌声动,掌随气行,身旁花树微微而动,有飒飒之声。银子持须而笑,微微颔首。忽然端起手中酒杯,向易水寒泼去。易水寒一见这酒来,右掌迎其画圆,将酒尽揽于掌中,左手伸出二指向水球一楼,其便化为水线向银子射回。银子举杯一接,大笑道:“好,好!来,儿子快回来坐了,别累坏了。”易水寒方才收招撤式归座。
“看来这鹿死我手也是高手归隐山林,他,老夫还真不认识。”
“这老人家行为怪异,却曾和欧阳无语交过手,而败于欧阳无语,至今耿耿于怀。当日还错认我为林子风前辈,险些与我拼命,他老人家的记忆至今还留在二十年前,实在可怜。”
银子拍拍潇潇肩膀,笑道:“这有何错,林子风的女婿替岳父迎敌,也是天经地义之事。”此言一出,潇潇脸顿时红了,道:“太师父,您喝得太多了。”
“哟!笑我这是醉话,怎么?潇潇没意思嫁给我们易水寒?”
“我……”潇潇着实窘得手足无措。
“师父,倒有一事忘了,弟子得了块小石头给师父过目。”易水寒插了一句,从怀中取出当日自黑衣人身上得到的石头递与银子。
银子口中道:“傻小子,我这方处理你的终身大事,又来捣乱,这么好的儿媳,凭你那木头似的脑瓜可得不到。”便接过石头,反复看了看,道:“不过是一块普通石头罢了。”
易水寒道:“若一人戴了,没什么稀奇,可若是千百人都戴,那便怪了。师父,你可曾见过有以此为记的江湖门派?”
银子闭目想了一时,道:“还真不曾听说。”
“师父可知一派,名曰‘烟云十六部’?”
“独山叔没告诉你吗?因你小子出事,爹我心灰意冷,哪还有闲心管旁的。再者师父为制玉闭关已有月余,这近日江湖之事,师父还真不知,明日,我便派人外头打探。”
易水寒点头,遂与潇潇将一路所见所闻都告于银子。
银子长叹一声,道:“怪就怪潇潇他爹,这林子风为后辈惹来这许多事,这前人种因凭什么总让后人来承担后果。现下外面这么危险,你们还敢回来,有胆量!不过,最近你们先别抛头露面,容我想想办法。你们也累了,回去歇吧。”潇潇、易水寒起身告退,银子看二人走后,自斟自饮起来。
当晚,潇潇沐浴更衣,觉身心俱累,倒下便睡。
次日无事,银子有意让二人好生休息,也不来看望,只派人送来寒箫、虺剑。易水寒大喜,便箫不离口,大吹一日《青溟散》。潇潇也只坐于房中,听箫喝茶,望天出神,觉自出流霜竹林后,今日才是最清闲一天,忆往昔生生死死,便若昨夜一梦,不知今后身又在何处,不禁叹气。忽听门处有声响,跑过去,自门缝取出一纸条,看罢之后,潇潇头一偏,暗笑。
当晚,潇潇手持灯盏,轻轻出门,左顾右盼,口中道:“有什么话不白天讲,偏偏夜里来说,这又不是见不得人。”话音未落,潇潇手中蜡烛“扑”地灭了。一人站于潇潇面前,道:“大侠迟到了,走,上屋顶。”。便一拉潇潇二人上房。
待坐好之后,潇潇怪道:“易水寒,有什么事不白天讲,搞什么鬼,说罢。”
易水寒微微一笑,指天道:“看星星。”
潇潇抬眼一望,果见满天星斗,闪闪烁烁。
“好好看看罢,恐怕今后没这般闲心观星了。师父已知数月之后,将召开武林大会,届时江湖各大门派齐会灵鹫山风堂雷宇,目前已知几门派遭灭门之灾尽是烟云十六部所为,丐帮便召此大会,以商对策。”
潇潇道:“真有此事,那我们也去?”
“师父命我前去。看来此番武林必起轩然大波。”
“那‘烟云十六部’真有那般厉害?” “如今不过捕风捉影罢了,这江湖门派间自相残杀还少了?就算不是烟云十六部所为,只要推到其头上便罢了,谁又知这什么烟的是不是谁凭空捏造的呢?”
潇潇半晌不语,良久方道:“我觉得哪里不对,极端不对。”
易水寒亦道:“没错,所有人都在说‘颠覆武林’,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原因,所有的人都在暗示那最后一个人危险至极,在我们找那六人夺剑谱时,他一直没有出现。按道理,凭其所说实力,不会对付不了咱们两人。”
“如果,那六个人都死了……”
“武林之中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可以以另一身份于武林呼风唤雨。”
“他利用我们,坐收渔翁之利。”
易水寒躺倒屋瓦之上,长叹一声:“我易水寒居然成为那人手里一颗棋子,真奇耻大辱,气煞我也。”
“易大哥……”
“不过”,易水寒复又起身,道:“我会让他出现,敢拿我当棋子是他最大的错误。我会让他满盘皆输,到那时,大仇得报,便回冷海湖,再不过问江湖之事。”
潇潇不能自己轻轻而泣,易水寒慢慢抱住潇潇。
二日晨,潇潇、易水寒被叫于银子近前。银子道:“这几日也休息得好了,没几日便是武林大会,你们俩替父出征,这路途遥遥,可得早些动身才是。我料想此次大会不过为了推个盟主对付‘烟云十六部’。潇潇,你放心,有风雷二圣在,他们都是你爹的亲师兄,你爹之事,一定会于武林大会上提起,自会有人为你做主。易水寒,旁的不嘱你了,只有一则,附耳过来。”
易水寒走过去,听银子道:“小子,给江湖上的朋友些面子,少赢些沽名钓誉之辈,人家创了大侠大剑之名,守了一世,不易呀!”易水寒听罢,想笑也不敢,点头称“是”。
当日银子为二人亲选良马,打点盘缠,将应用之物收拾停当。转日,易水寒、潇潇启程,往灵鹫山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