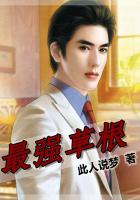感觉一整个早上,班里都特别的压抑。
没有人说话的时候,感觉想有个声音才不会忘了自己在哪里;而真的等到有人说话的时候,又觉得自己不说话会被别人遗忘。
然而要说些什么也逃不开那个彼此可能见都没见过的那个人——
“早上寝室大爷发现尸体的时候学校就拉了警戒线。现在去那里看还能看到草地上有一些清洗不掉的血迹,不过有人说,早上的时候那个血啊,那么一大滩,啧啧——”
“你说他也真的脑子有坑,还一个月就高考了,熬都熬到头了,还真就跳了——”
“你说会不会是他梦游啊?”
“不会吧,好像有遗书。不过我觉得和他一个寝室的人真的惨,估计得去去晦气。”
“学校里说是他从初中开始精神上就有轻微的抑郁症,最近家里出问题了就受不了了。反正这锅是甩的一个妙——”
“抑郁?还剖尸过了?”
“鬼知道啊。你说这么他爸妈也挺不容易的,这样一走,不是要了老人家的命吗?”
“……”
星语听着,觉得有些讽刺。
世人都说,生者节哀。可是,死者是不是孑然一身,身边连个安慰的人都没有呢?
挨到音乐课,也许是大家都觉得教室里的气氛憋得慌,都一股脑地往外跑。
“你怎么样了?”星语看着许安还是有点魂不守舍,走过去摸了摸她的脑袋。
“没事。我和他也就打了几次球,不熟。”许安勉强地咧开嘴,挤出一点点的笑,可是眼睛里都还是惊惶。
“走吧,去上音乐课了。别想太多。”星语不知道说些什么,就拿着许安桌上的音乐课本往外头走。
“等等我啦——”许安抹了一把脸,蹭蹭蹭地跟了上去。
星语看到许安不断地揉搓手指,知道她是有话想说。可是两个人谁都没有先开口,最后,许安看着就快到艺术楼了,下了决心一样,这才开口。
“星语,我第一次觉得,生死太突然了。”许安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姥姥去世的那段时间,她在医院里白血病都治了五年了,什么美国德国进口的特效药都是不要钱地往嘴里送。到后面她快不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一种解脱,感觉是排练了五年的戏终于演完了。”
许安的声音有一点干涩,她起头,也许是眼角有一点眼泪。她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又恢复了正常——
“火化的时候,全家人都在哭,可我不知道要哭什么。”
“可能我印象更深的,是那五年里,全家人都勒紧裤腰带攒钱买药。那个时候,我舅舅卖了一栋洋房,我妈妈卖了嫁妆,日子很苦。”
许安清了清嗓子,声音又有些哽咽。
“那个时候我才十岁,可连我都知道这东西治不好,尤其到后面各种并发症你猜都猜不到,可是,每一天,我妈他们还是托朋友找关系买了一盒又一盒的药。”
“你说我不懂事也好,没良心也好,总之,我就巴望着哪一天,姥姥能早点去。这样对她对大家都是解脱。你说我在灵堂看着周围一圈人都鬼哭狼嚎的,我能哭什么啊?我记得当我看到最后医院的心电图抽风了一样,我甚至还有点高兴。”
许安自嘲地笑了,看着面无表情的星语,“是不是人越长大就越伤感了?”
星语没有说话,也看向许安。
“你知道,我是那种呆不住的人,就想着全球各地浪,如果哪一天,我在外头遭枪子儿了,或者空难车祸什么的,然后突然死掉了,可我家这一个辈分的,就我一个人,你说,我爸妈怎么办啊?”
许安苦笑着,没等星语回答,接着说:“这几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老了很多,生意不好做了,可开销还和前几年一样的大,其实这些我都明白,我舍不得他们为我操心。”
说着,她看了一眼盯着她看的星语,摇了摇头,“你肯定说我是成天没正形,说话也净是挑晦气的说,可是我许安也是人啊,也有软肋啊。”
“呵,不说了,我开玩笑的,姐可是惜命的很——”许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语调又变得轻快起来。
星语一路上都没有搭话,有些时候看着神情变幻莫测的许安,有些时候看向云层垛叠的天空,有些时候啊,眼泪就流了三两行……
“星语,我们都会长大,然后就什么都不怕了,对吗?”
“嗯。”星语不知道是在对自己说,还是在对许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