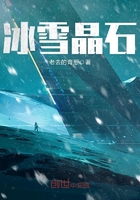所谓入乡随俗,便是这般随俗?
南宫轶端着身子看向身侧的简兮公子,一脸询问之色。
简兮公子倒是大方地摇着风流扇,道:“风流才子,佳人成话。难道此行不妥?”
南宫轶仰望着高悬的玉憬苑横匾,纸醉金迷的胭脂色里铺就的层层诱利之中,夹杂着声色的高酣。原来这就是随俗?
只是若这是随俗,那顾谙被放在何地?
简兮公子似看出南宫轶的难色,道:“玉憬苑是谙儿母亲的陪嫁,如今是谙儿的产业。”
南宫轶依旧站定未动。他想起那则照夜公子与简兮公子一掷千金的故事,想起简兮公子为讨佳人欢心学跳回风舞的故事。他心爱之人也是他人心慕之人,简兮公子与顾谙才子佳人的故事里,南宫轶是姗姗来迟的人。
南宫轶突然意识到得失心原来也很重要,哪怕一步、一件事、一句话,对他都影响至深。可若这些都重要,那么自己所承的帝业呢?
丘照夜所扮的简兮公子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南宫轶。顾谙说是招待,实则是行保护之实。这位太子的心机可不是外表看的这么简单,当初,自己的几个得力手下悄无声息地折在他的手上。这个天下,从来不缺掩饰自己的人。丘照夜面色沉静地看向南宫轶,礼貌地一笑,笑里掩过三分警惕、三分敌意:一个人过分地掩饰自己,为了什么?今日自己所扮的简兮该如何试探,如何出招?
简兮潇洒入室,南宫轶只得随后。
“太子殿下对相师堂了解多少?”
甫一落座,南宫轶被简兮突如其来的一问问的稍稍愣了下神,颜色刚缓,还未答话。简兮又道:“相师堂立世不足百年,其势却令人不敢小觑,太子殿下可觉得这话对?”
“是!”
“殿下觉得相师堂能有如今成就靠的是什么?”
南宫轶认真地看向简兮公子,开口道:“公子满足于今日相师堂之境吗?或者公子满足于如今在相师堂中的地位吗?”
简兮眉梢微挑,反问道:“为什么不满足?”
南宫轶笑道:“咱们回到方才的话题上来,我对相师堂了解多少。我对其了解的再多,也不如公子。所以我的一番见解在公子眼中会不会有班门弄斧之嫌?”
简兮抬眼正视而待。
“相师堂于天女河遇明主相侍的故事天下流传已久,可我不信。”南宫轶微微一笑,“当年北芷国主或许真的救了相师堂主,但因一命而偿百年,未免代价太大了。要说海家与相师堂的联手是基于利益最大化更让人相信。便如东盛与北芷的交易,只要找到一个共点,敌人都可以做朋友,何况有恩有德的两个人?”
简兮示意继续。
“这世间有个有趣的现象,野史往往比正史读来有趣,真实性更高一些。我曾拜读过一本《相师之始》的书,据说是北芷一位不得志史官所撰,这位史官穷其一生,跋山涉水,于坊间搜集了不少轶事传闻,我且讲一讲,简兮公子为我辨一辨真假可好?”
“早先听闻有这么一位先生,晚年居于南杞,被王族奉为上宾,讲述民间流传的一些荒诞趣事,以讨生计。在下便期与这位先生见上一面,才知原来他是南杞国人,这不得志便有了出处。”
“在这位先生的书中,北芷国主与相师堂的相遇缔约乃是七空大师一力促成。至于大师促成此事的原因,书中未述。北芷国主许诺相师堂的是相师十八堂子弟身不受死之权,当然如今相师一脉只余八堂,不知是自然凋败还是有故旧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相师堂承诺北芷国主,保海家百年无忧,诛一切对海家有扰有碍的对手,所以光鲜明亮的相师堂,一开始不过是君主家的一介杀手罢了,只是令海家没有想到的是相师堂真成了气候。”
简兮看向南宫轶,冷冷道:“当年搜家的时候未找到的那本原来在太子手中。”
南宫轶看向踩着馨香踏歌而舞的舞姬一步一步趋向自己,执杯慢慢抿酒,降低声音,尽量平复心情,道:“眼前此景似与今日话题不符。”
简兮淡然道:“无妨,这些舞姬知道规矩。”
果然,简兮话音刚落,这些舞姬顺着乐声轻盈转身,不再靠近南宫轶。
“成了气候的相师堂是顾家的野心还是始料未及?”南宫轶放下酒杯,将疑问与胸中所蕴的压抑之气一并缓缓吁出。
简兮感受着空气中凝而渐失的沉重,也学南宫轶方才之样,执杯轻轻摇晃,漫不经心地道:“成了气候不好吗?”
南宫轶失笑道:“好吗?以江湖之势却功盖国主,这个气候好在哪里?”
“原来相师堂之势,连远在南杞的太子也怕了。所以太子欲求顾谙,乃是早有预谋?”
不出南宫轶所料,话题终于引到顾谙身上。
“那么公子所求,求的哪般?”
屋内瞬时弥漫开一股硝烟之味。
简兮俊颜之中显出宠溺之色,口气中多了一丝霸道,道:“世间的缘分其实就是这样奇妙,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所以但有所求,也是求这缘分的长久,而旁人以为抓住的那丝情愫,其实不过是不懂江湖儿女相处之道的一种错觉。”
简兮所答狠狠地刺痛了南宫轶的心。简兮看着南宫轶眼中显现的黯然,心中直觉又好笑又痛快,将杯中酒中一饮而尽。
恰此际,一曲毕,舞姬低首而退,门口处站定一位风韵娘子。宽袖长裙,隐隐透出菡萏花底纹,不着风尘的脸上,恬淡怡然,朝着两人行了一礼:“两位公子有礼了。”
简兮抬眼,嘴角含笑,道“小姨!”
“贵客至,当有雅乐佳肴,是玉憬苑怠慢了。”
“久闻玉憬苑回风舞最讨心上人欢喜,非千金不可得。不知今日可有缘睹上一睹?”南宫轶插言道。
荻娘仍立在门口,不卑不亢道:“公子这话若几年前相问,荻娘只怕还会惊到,可自从简兮公子为佳人掷金学舞始,这回风舞便非千金可得了。”
南宫轶心情又沉郁了一番,瞧着简兮面上得意之色,又开口道:“难道要得佳人欢心,只一曲回风舞吗?”
荻娘看着屋内一副争风吃醋的模样,不由一笑道:“不知公子要讨哪家小姐欢心?这照邺城里的大家小姐,咱们玉憬苑还是耳闻了一些,也有一些了解,不知可要咱们为公子出谋划策?”
南宫轶愣了一下,自是不敢报顾谙之名,有些吃吃道:“不必。”
“世有解语花,当有解语者。世有公子,当有懂公子者。”荻娘冲南宫轶福了一福,道:“公子不是此间人,不该入此苑。”
简兮公子闻言,双眼轻垂,再抬眼时,面色复了自然。
荻娘退后两步,做出“请”势。
简兮公子将手中折扇在手心处轻轻敲了敲,道了句“告辞”,如来时般潇洒而出。南宫轶直觉自己似个跟班仆从,带着颓然之气紧随其后。
身处豪华大街,简兮指着来往行人忽道:“倘有一日,顾谙离你而去,你怎么办?”
南宫轶今日言语虽一直处于下风,但颜色形状并未有多少变化,听言道:“简兮公子以为我如今行事作派,担不起您这一问吗?”
丘照夜仰头望天,叹道:“天晴久会有雨至,久雨也有晴日出,天下之势如此,男女之情亦如是,总有一天谜底会解开的。”
南宫轶不解。
“谙儿说你真诚不假,南宫太子可担得起这一赞?若担不起,你如今行事作派,如何担我一问?若两者你都担不起,佳人在你侧,你可会忐忑?”
丘照夜将折扇收紧,指向前方,道:“请吧!这时辰,大小姐应该与南地胜师碰面了。”
南宫轶却未前行,而是一脸诚挚地回道:“世人皆传公子对谙谙之情深,这世间仰慕谙谙者众,公子不过比在下早遇她而已。”
丘照夜回身,一副愿闻其详之状。
南宫轶拱手,继续道:“我不懂男女之情,于其上也不懂变通,但我愿意学,愿意改,为谙谙学,为谙谙改,我对谙谙之心,之情深,并不比公子少。”
“如此甚好,请太子殿下谨记今日之言,莫待他日空成碌碌者。”丘照夜道:“碌碌者,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