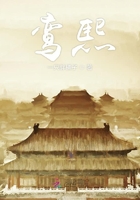日落矣。
有月升。
深峡有谷,名“君山谷”,谷前平川有商铺林立,亦有人流攒动,好不热闹。
“君山谷的夜市,我最喜欢逛的集市。”顾谙笑对南宫轶,“带你逛一逛?”
南宫轶牵起顾谙的小手,宠溺一笑,问道:“与明峡镇的集市有何区别?”
顾谙甩着手中的树枝,一副女儿家的小姿态,贴着南宫轶嘟着嘴撒娇道:“你给我买吃的,好不好?”
南宫轶一愣:“谙谙想吃什么?”
顾谙并不言语,只一味地拖着南宫轶七拐八拐,拐到一个小摊前,欢喜地指道:“它!”
南宫轶只觉一股臭味冲鼻而来,忙得掩鼻道:“谙谙,臭豆干?”
顾谙嘻嘻一笑,点头道:“我们叫它臭豆腐。家里所有人都不喜欢吃,也不喜欢闻,害得我只能偷偷来吃,吃完还得回去散味。”
南宫轶皱眉道:“谙谙,我也不喜这吃食。”
顾谙脸色一凉:“这可是你们南杞的吃食啊?”
南宫轶试图退后,却被顾谙扯住衣襟:“不许走!”
“谙谙,臭啊!”
摊主听到南宫轶说了“臭”字,双眉俱挑,道:“怎么是臭,明明是香,香的不得了。我学的外祖家手艺,冬天用缸收集雪,来年夏天在雪水里加稻草灰和佐料,用这卤水浸泡新鲜豆腐,隔日捞出,洇干后入锅油炸,也可配以各色小菜盐酱拌食。”
顾谙用手轻轻扫着小摊上臭豆腐的气味,表情舒适惬意,欢喜道:“小哥,先一样来一份。”
南宫轶再次试图逃离,顾谙右脚勾绊着南宫轶的左小腿,一边咬嚼着臭豆腐串,一边以眼狠狠地盯着南宫轶。南宫轶无奈道:“这东西,咳咳,这吃食,我真享受不起------”
顾谙故意贴近南宫轶,踮着脚,南宫轶被气味熏得难受,只得服软道:“谙谙,这美食有人享得,就得有人享不得------你容我退后两步,可好?”
顾谙慢悠悠地左右转着脖子,不肯答应,还一边回头道:“小哥,再一样来一份。”
“谙谙不是说最喜欢吃薄饼吗?”
顾谙举起臭豆腐道:“这是第二喜欢的。”
南宫轶深呼吸,忽又觉得这招甚糟,只得又捂上嘴道:“谙谙,咱们还是不要弄个什么一二的。”
顾谙嘟着嘴摇头,娇憨之色益盛,倒激起南宫轶一番宠溺爱怜之心,无奈地收回脚步,任顾谙一脸得意之色地大块朵颐。
虽是入夜,君山谷前却是灯火通明如白昼。顾谙拉着南宫轶,不停地给他介绍这里的特色,跳脱欢闹的样子,与一般少女无异,无丝毫往日里运筹精算模样。南宫轶平日里甚少逛集市,今日与心仪的女子行于闹市之中,生出许多欢乐情趣来,只觉从前光阴竟有虚度之嫌。少女心满意足地牵着他的手上了一家酒楼,找了处僻静的雅座,要了两壶烈酒及几色菜肴,凭栏望远近。
“谙谙今日心情很好。”南宫轶伸手将她垂于鬓角的一簇散发绾于耳后问道。
顾谙顺着他的手势轻抚耳垂,才发现今日忘记戴耳坠。顾谙改为半手托腮,打了个哈欠道:“你不说我竟没注意到今日忙碌了一天。”
南宫轶指着烈酒道:“烈酒伤身。”
“我待你是真酒友,你可别扫我的兴。”
南宫轶却道:“谙谙当真只为玩乐而来?”
顾谙白了他一眼。南宫轶笑道:“谙谙来君山谷,求人还是求事?”
“求人,这人我求了五年,每每不得。”顾谙并不瞒南宫轶道,“昝烈风,听说过吗?”
南宫轶思忖半天,方道:“听说他因错判冤案被流放,家人散尽家财保他一命,后便无讯出。”
“他被流放时你也不过将十五之龄,却能对他国之事了解地如此详细,还敢说自己性软不才吗?”
“我是说过自己性软,可没说过不才啊!”
顾谙抿嘴一笑,执壶倒过一杯烈酒,举杯道:“口误,权做赔礼。”
南宫轶伸手去拦,却没拦下,劝道:“谙谙这喝酒的习惯真是不好。”
“你也说习惯了,若好改就不是习惯了。”
“昝烈风好歹是名噪一时的按察使,怎会落魄至此地?”
顾谙又倒了杯烈酒,一饮而尽道:“名噪一时是真,落魄也不假,流落此地是因为君山谷是我娘的产业,他与我娘师出同门,在这里他才安全。”顾谙指着酒楼对面的一个书画摊道,“我还记得当年他雷厉办案的气势,扬风纪、澄吏治、核刑狱,何等威风,不过数载,便坠入尘埃,遭人碾压,被人欺凌。每日里涂抹字画无聊以过,性子越来越孤僻,少与人言。”
“他得罪了谁?”
“京北七门。”
南宫轶听到“京北七门”,眼中突迸出一丝精光,问道:“谙谙曾至南杞查一桩旧案,事涉七门里,如今这昝烈风亦因七门里被流放,谙谙是想为他翻案?”
“他自己的案子,我为他费什么神?”顾谙不屑道,“我娘师出陶朱门,门中有令可嫁可娶官家人,唯身不做官家徒。昝烈风违师规弃师转拜官家,所以陶朱门上下皆以为耻。只因我外祖家与昝家有旧,才将他接到此处,允他栖身。”
“所以传言其家人散尽家财救他,其实是你外祖家所为?”
“他性狠心辣,一心醉迷刑狱,他既无心成家,亦无女儿家心仪他,哪里有什么家人?”
“谙谙如此评他,却为何年年求他?”
顾谙一笑:“我不喜他并不妨碍他成为一枚有用的棋子。”
“谙谙这次要何条件打动他?”
“我只以一个理由请他,往年他不动是觉时机未到,今年恰好。”
南宫轶不解。
顾谙又一杯烈酒入腹,脸上微微泛起酒红,道:“我所查旧案,无功而返,他的仇只能自己报了。”
顾谙看南宫轶不解的神色,继续道:“他是酷史,我不喜,但刑狱之案,有时非得他这样的人不可。他不喜相师堂的人,与我爹素少来往,不过他待我还是和善,许是念了我外祖的情面。皇帝手中有几桩难案,按察使司无人能处理,皇帝查阅旧案看到昝烈风,有意复用他,此举与我不谋而合,这才有今日之行。”
“他功名被革,有罪之身,如何起用?”
“北芷有制,但有权贵推荐保举,可以复用,不入官职,持特使令做事。”
南宫轶似有所悟:“此举虽有弊,但善加利用,倒是不小的助力。”
“每个特使令身边都会跟着一个暗卫,但有不臣或反逆之心,格杀勿论。”
“又是小皇帝的手笔?”
顾谙点头道:“特使令身边跟着暗卫,是沿袭之制,只这格杀勿论之规是皇帝之笔。”
“这位北芷小皇帝,当真是劲敌。”南宫轶感慨道。
“皇帝自小亲近我,耳濡目染地学了一些我的性子,所以海一芊曾言倘被有心人利用我的性子而伤害皇帝,恐不及防。我不防你,便是那孩子不防你,希望你也不要做出伤害那孩子的事来。”
南宫轶不语。
“秋日南师胜聪会来北芷,我会请求师父与她相见,相信两位天女峰掌门的晤谈,会令两国有一个崭新的局面。”
南宫轶看着顾谙透着醉红的脸颊,轻轻抚之,指尖传来温润的感觉,顾谙眨着眼睛,忽又笑道:“以为我喝醉了?不会,我酒量很好的。”
“我是在想,我的谙谙到底是怎样的女子?”南宫轶眼中,似水美样的顾谙;顾谙眼中,年华正好的南宫轶,都在相视里一笑。
将爱意尽付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