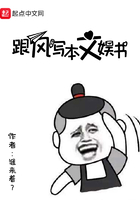阴雨绵绵的天气还在持续,热烘烘的空气散发着糜烂的气味,在屋里或者屋外都让人不经意间打着哈欠。奶奶还是忙忙碌碌的,不是在灶台上收拾就是在堂屋里剁猪草,爷爷则戴着眼镜一脸严肃的样子,可他的手里却是拿着一把弯刀,初看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后来才发现新鲜竹片被他砍成一根根细丝的状态,然后一起捆起来成了刷锅的刷子。
突然的人声和犬吠声传来,我们都跨过门槛去到檐坎上看,只见来的有三个人,他们一边说笑一边给爷爷奶奶打着招呼,爷爷奶奶也迎了上去,而一直在周围看似凶猛的狗渐渐走开了。来的人爷爷奶奶让我称呼他们为姑婆和姑爷,而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孙女,小孙女同样被要求叫人,听她把我爷爷奶奶叫做表爷和表婆。大人们还在继续说着话,而小孩往往只要叫过人就自然变得边缘化,没人在意了。
阴雨天是无聊的也是安稳的,尤其是老人做不了的事太多了,一大早有一些小伙子披着塑料薄膜戴着帽子上山去了,听到他们议论说下雨天好去捡香菇。爷爷他们的活动就是打扑克牌,刚好人数够了,而姑婆他们的目的也就是来打牌的。一个小独凳就是打牌的桌子,几个人紧密的凑在一起开始了他们独有的小天地,还听到他们不时会说杀了、垫了之类的话,结束一局就开始计分,数到八十分有人高兴有人唏嘘。
外边是时而阴、时而又漂几颗雨的天气。如此天气在我的世界里还是适宜户外活动的,没人顾得上管我的时候我又来到院坝边上去看自然生长出来的喇叭花。鲜艳的红色花朵特别能刺激人的视觉神经,看得入迷又见一粒金色的光点映入眼帘,定睛一看居然在叶片上走出一只金色甲虫。这只甲虫像七星瓢虫一样大小,只是它是有点方形的形状,全身都是金黄色就像过年别人家的金粉对联一样,而且还要更亮一些。还是对新事物的老态度,我又抓起那个新奇的甲虫,想要拿去给大人们看,也想知道这是什么虫。再次伸开手指那只甲虫还在手心里,爷爷半倾着身子看一会才回答这是黄金壳壳虫,其他人没有格外探头探脑的来看,还是坐得好好的只是等着稍后的出牌。没想到这个虫子的名字这么直白和我想的一样,有一个人认可就足以,别人没看其实我也不想分享给别人看我的宝贵甲虫,这样反倒合乎我的心意。合乎心意的事情只让人觉得是快乐,没有任何不妥。
正要跨出门槛再去外边找一只,堂屋里的姑婆像是突然关心起我抓到的虫子了,她问我抓到的是不是瓢虫,我一听忙说不是,由于认得瓢虫,这个明显不是,我说这是黄金虫,还补充说过一会它就变成黄金了,说完得意的扬长而去。再走到喇叭花旁边,我想一定还能再见到一只,却感到身后有人,突然转身查看居然把身后的人吓得一跳,而身后来的正是姑婆的孙女,记得上一秒她还在姑婆的怀里稍微有些无精打采的样子,现在的她竟然跟在我的身后,还是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眼睛眨巴眨巴的一脸认真的模样。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也许是姑婆无心的问了那么一句,也许是我臆想出来的虫子可以变成黄金吧,没想到吸引得这个陌生的小女孩变成了我的跟班。用心去找甲虫却再也找不到,这个跟班还跟着我,和我一样的不知疲倦,那双无辜的大眼睛还是那样在那个茫然的脸上。走过很多菜地,终于她开口说话了,她想要看一看我手里的金甲虫,待我缓缓张开手指查看的时候,她也伺机凑了过来,无奈只是一瞬间的事甲虫飞起来逃走了,她慌张的感叹倒“哦豁!”而我追出几步奈何小虫子越飞越高了。
说哭就哭的本领与生俱来还能驾轻就熟这就是小孩子。我跑到爷爷身边拖着哭腔抱怨倒该别看甲虫的,还说我的黄金没有了,爷爷还是很平淡的打着牌,还反问倒要是真能变成黄金我们就不打牌了,都去抓甲虫去了。还是很执着的我,依然觉得丢失的甲虫是贵重的黄金而不是一只普通的虫子,也因为这种答案不是那种简单是与不是那样好理解,我认为大人们不抓是因为甲虫飞起来本就不好抓罢了。无论是与不是,其实我要的只是一个安慰,或者一句推脱搪塞的话也是好的。
像是一场表演,哭泣的无用功做下来没有结果,也就停了。我又看起了独凳上的牌,看着彩色的美人鱼和黑白的美人鱼是一样的模样,而他们都更喜欢那张大王。对面的姑婆抱着小女孩,她很安静,睁着眼睛没有在睡觉,守着她自己的一小块底盘。而我去了菜地又去了院坝,然后又到了堂屋,到处都是我的,却没有那种十足的安全感,我终于也凑在爷爷打的牌堆边还拿起牌观赏起来,一小会的肆无忌惮过后终究没有得到一点点的包容,被爷爷责怪过后我只好躲远了。
心想这是由于自己好动才得到的责怪,和安静的小女孩不一样。可是即便这样想也还是比较委屈。外边的喇叭花已经收了它绽放的花朵,而红色的花苞还是那么鲜艳,因为它在等待明天的重新开放。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感觉也是因为看到喇叭花而想到我的甲虫才越来越浓的,这不由得让人又走近喇叭花的旁边。
火烧云的霞光之下零零星星飞着好多蜻蜓和一些别的飞虫,我看得入迷又发现身后有人,这次回头看却是爷爷。爷爷一伸手就抓住一只金色甲虫递给我,不似嘲讽却胜似嘲讽,没想到下午会有这么多飞虫,伸开手看见姗姗来迟的金色甲虫再次飞走了,这次却没有那么多的不舍和遗憾。远处的三个人说说笑笑走远了,和来时一样只是四周没有犬吠,和来时一样只是小女孩的声音更大了。爷爷过了一把打牌的瘾像是变得不舍了,不自觉向那边走了几步。
中午的金色甲虫是不自由的,现在的金色甲虫是自由的。相反的,我现在是不自由的,爷爷拉着我的手随意走着,我的各种问题涌入脑门,我问了许多问题,只是最后关于那个甲虫的名字,其实他也不知道,哪是他现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