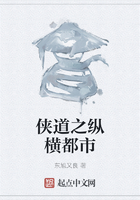事情一步步的似乎很顺利。清干净了傍晚跟踪的尾巴和客店的明哨暗哨,又赶走了马匹另其四处乱走捣乱,最后再赶来这西北的库房,打昏了看守后,一口气点燃了十间货栈。一切都按着计划在发展,但钟少候的右眼皮还是不断的在跳动。
看来安老魔定是跟在自己的身后。
他这么想着,打昏了路过的更夫,藏到了小巷子的转角后边。一旁的林义州也换上了岳州军的装束,并牵来了两匹马。
二人之一牵着马,另一人把换上了自己衣服的两名守卫推到马背上,再把守卫的双手绑在了马鞍上。一切准备就绪后,二人就在这巷子里等待,等待火势旺盛,等待人潮涌现,好浑水摸鱼。
过了许久,久到钟少候背完了两遍家训,终于火光大量,引起了城门处守卫们的注意。
“走水了!”
“调车过来!”
“起来灭火!”
人们从屋内走出,提着水桶水瓢,朝着城门处跑去。
成祖下令,凡诸州县,设潜火军一百人,归于夜巡警治下,城中每三百步建水缸一口;居民两万户以上者,设潜火军两百人。
按律,潜火军给饷略高于一般民壮,低于巡警司军士,每月得银二两,布一匹,粮四斗。不过看此刻救火的潜火军们兴奋的模样,似乎湘王给他们有额外的加响。
钟少候轻轻的抽打了一下马屁股,让两匹马驮着那昏睡中的军士朝着反向前进,等一队急着救火的军士匆匆走过后,偷摸着拿了两个过路的百姓的水瓢,混在救火的队伍里朝着城门处走去。
二人很顺利的就走到了城外,挤人群边缘,躲在了树林里。
“怎么不走?”林义州回头看着钟少候。
钟少候趴在树下,眯眼远望,“一定有哪里出了问题。让我再想想。”
“别等了,要是安幕纯追来了就走不了了。”
二人说了几句,发觉背后有人正从林子中靠近自己。
“什么人?”
“是林将军吗?杨百户让我们来接应将军的。”
二人与之交谈了片刻才知道杨青虹分了三伍人,各领了十匹马守在东、西、南三门接应。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钟少候灵机一动,问他道。
“我刚刚看见人群里有两个官兵没有救火,而是朝林子走过来,我就知道应该是将军。”
钟少候恍然大悟,“我们穿着军服,一路走来竟然没有被拦下,一定是其他门出了问题。你快报给杨百户,让他增援令两门。”
那军士不为所动,低头道:“杨百户让兄弟们砍树造车,现在应该在攻城了。”
“什么!”钟少候与林义州如遭雷劈。
“···我们去北门,让他停下来···”
“不!我们去南门。”林义州打断了钟少候,“一共不到一百人,还都是斥候。我们现在去也就不来几个了。”
林义州咬牙切齿,他只觉得自己现在心跳得飞快,血烫得要烧起来了,“我们去南门和东门,冲门,看看能不能救下几个。”他走到接应的军士身边,跨步上马,眼神无比的坚定。
——————————————————
湘王府,落石书房。
此前有天外陨石落在岳州城外,外貌好似一方砚台,湘王买下了陨石,并令人磨制成砚,置于书房中。此后书房就成了落石书房。
窗外人影绰绰,湘王停下公事,皱眉走到门边,问门外守卫道:“怎么回事,现在几更天了,外面怎么这么吵?”
“城里走水了,潜火军的人正在赶去灭火。”
湘王“哦”了一声,正要继续办公,一阵急匆匆的脚步从远处传来。声音的主人推开了书房的门,是一位甲胄全身的校尉。他抱拳躬身,对着屋内大声道:“殿下!城北门有贼人举火攻门,城里还有贼人的内应在到处放火。”
湘王取来虎符信令,分别在两张纸上按下签字,拿给那报信的校尉道:“我已知道此事。你找人去向岳州卫与岳州左卫求援。”湘王扶直那校尉,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告诉岳州卫指挥使张段和岳州左卫的杨再勇,让他们出骑兵,不许走脱了一个攻城的贼人。若是逃了一个,就拿他一个儿子来补。”
那校尉浑身僵硬,步履阑珊的离去后,湘王瞪了眼之前胡乱说话的那个仆役,又吩咐他道:“我还能让你办事吗?”
仆役嬉皮笑脸的跪地求饶:“小奴一定办事妥帖,绝不胡言乱语。”
湘王踢了他一脚,回到书房里继续办公:“让安公公回来,放过小家伙们吧。孤必让他如愿。”
仆役恭敬地关门离去,只留下湘王一个人在书房中长吁短叹。
“不知道要多死多少人啊。”
————————————
传说有人在岳州城外发现了黑白两只鼠王。鼠王毁坏耕地百姓一连数年颗粒无收苦不堪言。有道士请来了黑白二气,化成两条大蛇吃掉了鼠王,岳州这才丰收。为震慑鼠类,道士把双蛇画在了东门的门板上。于是到今天为止,每年春夏两种之时,全岳州的农户们都要赶来此地,在东门外设祭坛大肆祭拜二蛇。而平日里这黑白二蛇也香火不断。
此时,城西火光一片,人来人往呼喊声不绝;东门边,夜间祭祀的农户们岿然不动,神态自若的跪在门前。
“不是说东门人少的吗?”折琼对着耶律隆绪抱怨道。
“我也不知道啊,白日里来的时候,没有这些人的,”耶律隆绪也十分苦恼。
二人不再等待,把里衣外穿,又在地上打了几个滚,确定看不出破绽后,有对昏睡着的何闲同样操作了一番。等到平日里那张无论何时都一派自信满满的小白脸变得黑不溜秋了之后,折琼才满意的点头,才把耶律隆绪从不离身的酒壶拧开,洒了几滴在各自的脸上,和他一人一边架起何闲来,装作迟到的信徒,跪在人群的末尾。
“你们几个是谁家的?”有管事的祭祀看了过来。
“啊··哈哈,我们三兄弟是投奔叔父来的。他有伤病,这几日来不了,我们替他来的。”折琼露出他标志性的温暖笑容,手死死地把耶律隆绪的脑袋按在地上。耶律隆绪怕暴露不敢反抗,只得把气撒在不知情的何闲身上。
“哦,一定要心诚。”管事告诫了几句就走了。岳州城里外的有上万农户,他才记不住那么多人呢。
三人跪了许久,祭拜者们才慢慢散去。等人走的差不多了,三人偷偷溜到墙角,把何闲绑在耶律隆绪的背上,开始爬墙。三人的衣服里外都是灰黑,在地上打了滚后更是如此。远远的从地面上望去,根本发现不了还有人在爬墙。
门楼上的守卫大都被调到了别处,剩下的小猫两三只根本不是二人的对手。一位守门的军士发现了已经爬上墙的三人,正要呼喊,就被耶律隆绪一个健步拉近了距离,再抬手那么一劈,再也发不出声音。
折琼看着满地的鲜血升腾出雾气,有些不满的看向耶律隆绪。耶律隆绪对他露齿一笑,从另一面跳下城墙,单手挂在半空中。折琼半个身子挂在墙外,只剩一双手扒在墙沿,他双脚蹬强看准了位置,深吸一口气松手落下,正踩在耶律隆绪的肩上。
他吐出浊气,双手紧紧扣住墙缝,让耶律隆绪继续。
感谢岳州扩建,感谢湘王慈悲。岳州城的外墙并没有像边镇城墙一般凝成一体,使他还有缝隙可抓。
二人又反复了两次才落地。正当二人有说有笑准备进入远处的森林时,一道令二人不寒而栗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了过来。
“技术活,当赏。”
一阵破风声传来,折琼跪倒在地上往边上一滚动,他之前所在的位置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入土声。耶律隆绪小心的摸过去,那砸出的洞口似乎正好一铜钱大小。他挖出了那物件,正是一枚铜钱,只是铜钱上的阳文给他陌生的触感,似乎不是现下楚国流通的任何之一。
“二位杂耍够了就走吧。西北折家和辽国王子对殿下···呵,咱家都糊涂了。今夜之后,就是陛下了。东南何家的弃子还请二位留下,此人与陛下和咱家都有大用,二位莫要自误。”
折琼解下身上的系带,把何闲推到耶律隆绪怀中道:“四哥,你虽为辽人,但你我兄弟情义深厚。你快带着大哥逃吧,这里就交给小弟我吧。”
耶律隆绪哈哈笑着,握住折琼的胳膊,不让他逃了,“四哥我怎么能丢下你走呢,要走也是你带着大哥走,我留下。”
二人就这么边推让,边往林中退去。而安幕纯则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二人演习,没有被拉开半点距离。
“跑!”
眼见拖延无果,二人一人一半架起何闲掉头就跑,安幕纯故作无奈,轻叹道:“何苦呢。二位日后必定是我大楚的栋梁,就不能与咱家和和气气的吗。”
他双手甩出,数不清的暗器向不远处的三人射去。耶律隆绪接过何闲,与折琼对上一掌一脚,推开彼此,避开了这一击。耶律隆绪暗暗叫苦,为什么自己就慢了半拍,没有把何闲先推给对方呢,此时也不容他多想,活命最要紧。
安幕纯摇头,啧啧称奇,也不多想,朝着耶律隆绪飘去。
在他背后,折琼解开腰包,对安幕纯大声道:“安老公守湘王门户,想来是要门包的。不知五两银子够不够。”他取出一把碎银子,运功一一射向安幕纯。
安幕纯停身回头,袖子一荡就接下折琼射来的银子,下意识的掂量了一下,确实在五两左右。
他用力将碎银子压成一锭,丢向折琼。继续朝耶律隆绪追去。
折琼避开银锭暗器,但不敢靠近安幕纯,只得继续取向安幕纯投掷碎银。而安幕纯则是不断的回首抹掉折琼的攻击。
大概过了四十两的功夫,折琼的荷包已然见底,于是不得不想办法正面面敌。另一边的耶律隆绪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无奈之下只好回身对敌,希望安幕纯能说到做到,不会杀了自己。
安幕纯一掌拍出,耶律隆绪伸掌与他相对。安幕纯脸上带笑,眉眼讥讽,双脚正立着,云淡风轻。而另一边耶律隆绪心中凄苦,他已用上了全力抵抗,但依然感觉如渊如海的磅礴内力从安幕纯手中不断的传过来。耶律隆绪脸色发白,只觉得安幕纯的内力似游蛇般在钻透了自己的防御,在自己的经脉中游走。
折琼从安幕纯背后赶来,一掌就要打在他脊柱中段。安幕纯冷笑一声,回身一指点在折琼掌心。折琼转瞬间化不开内力,左臂肌肉炸裂,鲜血源源不断的渗出表皮。
折琼面目狰狞,右手取出一块泛着银光的金属,正是被安幕纯捏作一团的银锭。他用力抬手挥去,银锭锋利的边缘正插向安幕纯关节处。
安幕纯面色一变,正收手,却被折琼抓住了指头。他表情阴冷,忽然背后又有抽刀声传来。
耶律隆绪拔出腰刀,正向安幕纯挥来。他另一手无力的垂在地上,同样受了不轻的内伤。
安幕纯躲闪不及,被那一刀正正砍在肩头,划开了半边衣袖,还在身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痕。
他看着肩上逐渐涌出的血迹,发出阵阵冷笑,令折琼和耶律隆绪不寒而栗,靠向彼此。
“我本不想杀你们。”
安幕纯脱掉破损的袖子,把它系在腰上,又缓缓地把另一边的袖子用布条缠紧。折琼与耶律隆绪趁机向林中逃去。
“不过,陛下会原谅我的。”
安幕纯从怀中抽出一条细长的银白丝带,怀念的摩挲着,而不是把目光看向远处的逃跑的两人。
“希望你们的血不会太难洗。”
抬手放出,银白的丝带闪电般的向折琼等人飞去,丝带在空中灵活的摆动,就像一条银蛇,在月光下亮出了它尖锐的毒牙。